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的一纸诏令,将韩、赵、魏三家大夫正式封为诸侯。
这一事件,被司马光视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之笔。
寥寥数语,看似平淡,却暗藏千年治乱兴衰的密码。
为何司马光以此事为史鉴之始?
只因这一笔背后,不仅是对礼崩乐坏的痛惜,更是对后人“以史为镜”的殷切期待。
《资治通鉴》历经十九载编修,载尽十六朝更迭。
司马光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炼出这样一个真理:
人若读透历史,便能放下执念;国若参透兴亡,自可长治久安。
一、放下权谋之争,方显治国之智
《周易》有云:“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然观历代王朝,多少人困于权术算计,终致身死国灭。
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席卷长安。
太子刘据被江充构陷,含冤起兵,最终血染湖县。
武帝痛失爱子,方悟“术数之臣,祸国甚于虎狼”,遂下《轮台罪己诏》,罢兵休养。
可叹一代雄主,直至暮年才懂:
玩弄权谋者,终将被权谋反噬。
司马光在《通鉴》中特录霍光辅政之事,别有深意。
汉昭帝年幼登基,霍光总揽朝政,却始终恪守人臣本分。
当有人劝他效仿伊尹废帝自立时,霍光掷地有声:“伊尹处商汤盛世,我行于汉室危局,岂能因私欲毁社稷?”
他力排众议,迎立流落民间的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
宣帝初即位,霍光当即还政,退居幕后。
《通鉴》评曰:“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然其明察奸伪,严于律己,终未失人臣之节。”
可见真正的治国之智,不在争权夺势,而在知进退、守本心。
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道,更是将此理演绎到极致。
魏徵以直谏闻名,常令太宗当众难堪。
一次退朝后,太宗怒言:“必杀此田舍翁!”
长孙皇后却着朝服贺喜:“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
太宗闻言释然,从此将魏徵谏言书于屏风,日夜省察。
《通鉴》载此事时,特引太宗感慨:“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司马光借此告诫后世:
执念于权术者,如持利刃行独木桥,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
唯有放下争斗之心,以史为鉴,方能成就真正的大智慧。
二、淡看兴衰更替,方能洞察天时
《道德经》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王朝兴衰,亦如自然轮转。智者不惧鼎革,明者不困成败。
五代十国时,冯道历仕四朝十帝,被欧阳修斥为“无耻之尤”。
然司马光在《通鉴》中为其正名:“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此评看似贬斥,实则暗藏机锋。
在乱世之中,冯道赈济灾民、劝止屠城、保存典籍,使百姓免遭涂炭。
他曾在《长乐老自叙》中写道:“吾本书生,逢乱世而苟全,非求富贵,但为生民计耳。”
司马光以冯道为镜,照见一个更深层的真相:
执着于王朝正统者,往往陷于道德枷锁;
真正心怀苍生者,却能超越兴衰之相。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亦是参透此理。
他夜宴石守信等将领,坦言:“朕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众将惶恐请辞,次日皆交出兵符。
《通鉴》详录此事,并引太祖之言:“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富贵者,不过多积金帛,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
看似劝人贪图享乐,实则深谙“盛极必衰”之道。
司马光在评述中感叹:“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赵匡胤耳。”
此言非赞其武功,而叹其懂得:
真正的王者,不在开疆拓土,而在知何时放下刀兵。
三、修身以立德,方能安邦定国
《礼记·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资治通鉴》中无数帝王将相的命运沉浮,皆印证了一个道理:治国之基,不在权术,而在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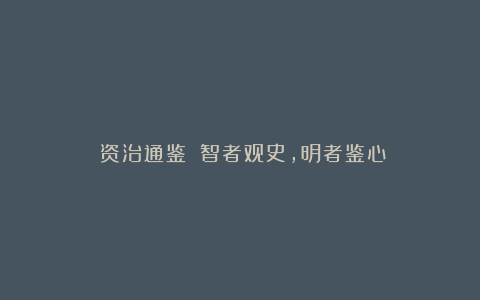
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天下分崩。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虽雄才大略,却因“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私欲,屠徐州、戮百姓,终成千古骂名。
司马光在《通鉴》中痛批:“操知人善任,然性忌刻,好诛戮,故虽强盛,人莫敢亲。”
反观刘备,出身织席贩履,却以仁德立身。
当阳长坂坡一役,他携民渡江,甘冒被曹军追击之险,百姓感泣相随。
《通鉴》特录其言:“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正是这份“不忍”,让诸葛亮、关羽、张飞等英才誓死效忠,终成三分天下之势。
司马光在评述楚汉之争时,更将修身之道剖析得淋漓尽致。
项羽力能扛鼎,却刚愎自用,火烧咸阳、弑杀义帝,最终众叛亲离。
刘邦虽好酒及色,但入关中时“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得天下后,置酒洛阳宫,坦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通鉴》引太史公言:“高祖为人,仁而爱人,此所以得天统也。”
北宋名臣范仲淹,更是将修身之道践行于朝堂。
庆历新政期间,他力推“明黜陟、抑侥幸”,却因触动权贵利益遭贬谪。
离京时,友人劝其少言避祸,范仲淹慨然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司马光在《通鉴后记》中赞曰:“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正是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修身境界,让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千古绝唱。
《通鉴》载唐玄宗故事,尤具警世意义。
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开创盛世;
天宝年间,却沉溺享乐,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终酿安史之乱。
司马光评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及其终也,乃以奢败。”
可见帝王修身如逆水行舟,稍有懈怠,便是山河倾覆。
四、以民为镜,照见治国得失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资治通鉴》中三百余万字,字字皆在诠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为贯通南北的旷世功业。
然其“急令暴征”,强征民夫数百万,沿途“死尸满路,哀嚎震天”。
《通鉴》载:“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最终,龙舟尚未抵达江都,天下已烽烟四起。
司马光痛陈:“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
反观汉文帝,一生躬行“黄老之术”。
他废除肉刑,亲耕籍田,宫中帷帐“无文绣”,陵墓“皆瓦器”。
《通鉴》详录其诏书:“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正是这份对生死的豁达、对百姓的体恤,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引发朝野震荡。
青苗法本为惠民,却因官吏强行摊派,反成“朘民之膏”;市易法欲平物价,结果“商贾不行,酒税亏损”。
司马光在《通鉴》编纂期间,多次上书神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
他借汉武帝盐铁专卖之弊警示:“与民争利,灾害并至。”
虽言辞激烈,却句句指向治国核心——政策得失,当以民心为秤。
明末崇祯帝的悲剧,更将“民为镜”的道理刻入史册。
面对天灾人祸,他频繁更换内阁,却始终不肯动用内帑赈灾。
《通鉴》续编者谈迁在《国榷》中记载:
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崇祯泣曰:“诸臣误朕!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然当起义军打开皇家粮仓时,积粟竟“够天下十年之用”。
司马光若见此景,必会再叹:“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
结语
《资治通鉴》卷末,司马光自述编书之志:“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千载而下,这部史书早已超越简单的记事,成为照见人心的明镜。
唐太宗曾命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意在警示子孙;
司马光则以笔为刀,将三百余位帝王的成败刻入竹简。
从三家分晋到陈桥兵变,从焚书坑儒到开元盛世,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
执迷者困于方寸,觉醒者观照千秋。
今日重读《通鉴》,不必苛求成为治世能臣。
但若能以史为舟,渡己身之执念;
以智为锚,定浮生之迷途,
便是读懂了司马光藏在字里行间的终极智慧——
历史从未重复,但人心永远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