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蓝鹰书画总编辑陈放:“物换星移几度秋,青山依旧水长流。” 在历史长河奔涌向前的轨迹里,总有一些珍贵的印记,如散落的珍珠,等待有缘人俯身拾起。杨林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执着的 “拾珠者”,他以画笔为舟,以情思为桨,在横山老街的残垣断壁间,打捞起 “消逝美学” 的璀璨光芒。
当初夏的日光炙烤着横山新城区的水泥森林,杨林先生却逆向而行,踏入老街这片被时光遗忘的角落。老街斑驳的石桥、歪斜的山墙、锈迹斑斑的门环,恰似岁月写下的密语,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如今的寂寥。而那些从废墟中生长的野藤、绽放的野花,又如生命奏响的赞歌,在荒芜中孕育着生机。这看似矛盾的景象,在杨林先生眼中,却是独特而迷人的 “消逝美学”—— 它是繁华落尽后的沉淀,是新旧交替间的诗意。
杨林先生用画笔定格老街的每一处细节,以文字记录老街的每一段故事,他不仅是在描绘风景,更是在守护一段即将消逝的历史记忆。正如中国画讲究 “计白当黑”,老街的残缺何尝不是历史的留白?杨林先生的记录,让这份留白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让我们在凝视消逝之美时,读懂了时光的深意与生命的坚韧。
图文|杨林
《写在前面》
芜湖古名鸠兹,人文渊薮。乡贤萧云从,为实景山水画开宗立派,其《太平山水诗画》冠绝古今,泽被后世。明清之际,太平府辖当涂、芜湖、繁昌,山水清嘉,胜迹如星。云从遍历诸地,师法造化,熔宋之范宽雄浑、马夏清逸,元之黄公望苍茫、倪瓒简淡,及明之沈周、唐寅精妙于一炉。既师自然,又出机杼,以神来之笔,绘就山水幽韵。
其所作四十三幅,幅不雷同,或雄浑,或空灵,皆臻化境。此作不仅饱含桑梓深情,更树画史丰碑,为后世研习山水之圭臬。今承先贤遗风,秉持“鸠兹艺画”之旨,以当代笔墨重绘太平山水,续写人文新篇,冀使古韵新声,共辉艺苑。
初夏的日光斜斜洒落,裹挟着鸟鸣与热浪,将横山新城区的水泥森林烘烤得发亮。我背着画具穿行其间,恍若穿越一道无形的时光帷幕。
国道旁,房地产广告牌上“水岸名邸”“江南御苑”等字样在朝阳下泛着刺目的光,喷绘画面表现的奢华图景,与钢筋水泥的冰冷气息交织,与我即将前往的横山老街形成鲜明的反差。
横山老街,这座曾被称为“小芜湖”的商贸重镇,静静地躺在新城区的边缘。它被横溪河温柔地分割成东西两个街区,又由横山桥将它们紧密相连。如今,想要寻觅老街往昔的风采,只能在西街区寻得些许痕迹。
当我向路边摆摊售物的老者,打听横山老屋的位置时,他们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热情地指引:“过了横山桥那边都是。”
沿着老者所指的方向前行,一座石制桥墩与水泥桥面混搭的老桥出现在眼前。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印记,桥身的石块有些已经开裂,水泥表面也布满了裂缝与青苔。
走过这座桥,转过街角,几座倾颓的马头墙老屋突然撞入眼帘。墙头的狗尾巴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宛如时光老人随意挥就的几笔枯墨,为这破败的景象增添了几分萧瑟。
坍塌的老屋面后,一株枯死的老树静默伫立,虬曲的枝干伸向天空,与老屋相互映衬,将沧桑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横山老街,就这样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向我展开了它布满皱纹的容颜。
横山,昔日的繁华盛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褪色。横溪河曾是这里的交通命脉,舟楫往来,商船如织,载满了货物与希望。
如今,河面上再不见穿梭的船只,浑浊的水面倒映着残缺的桥墩,那是1956年修建的“反修桥”遗址。桥墩上布满了青苔与水锈,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忙与辉煌。
我支起画架,所处的位置恰好能同时望见桥南的“通天府埠头”与桥北的“水天门码头”遗迹。宽阔而古朴的码头台阶,一级级延伸至水面,虽已少有人踏足,但仍能从那厚重的石块与磨损的痕迹中,感受到往昔的热闹非凡。
桥头新立的碑石上,镌刻着关于此地过往的文字,字里行间,昔日的繁华似乎又在眼前重现。清道光《繁昌县志》记载的“横山桥镇在县东北三十里”的盛况,如今只剩下河岸边几处凸凹不平的青石台阶。
石缝里钻出的野菊花,此时正绽放着黄白色的花朵,与野草一同在夏风中摇曳,为这寂静的河岸增添了一抹生机。
老街的西街区,那尚存的几百米老街格局,宛如一条被截断的龙脉,新旧建筑犬牙交错,诉说着时代的变迁。保存相对完好的清末“许氏槽坊”,实则也已病入膏肓。
门旁的老窗,窗扇早已坍塌损坏,只剩下几根歪斜的木框,在风中摇摇欲坠;门环被岁月侵蚀得锈迹斑斑,表面布满了蜂窝状的孔洞,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时光的无情。
我在老街的通天巷入口处,寻得一块稍显宽阔的地方。此处是老街尚存古建筑的集中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一座座即将坍塌或已然坍塌的老屋。
山墙歪斜,屋面塌陷,门框扭曲,枯枝败叶散落一地,新生的野藤肆意攀爬在老屋之上,与破败的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
我拿起画笔,以干笔勾勒它们歪斜的轮廓,就在这时,屋檐突然掉落一片瓦当,“啪”的一声脆响,在空荡的街巷中激起层层回音,仿佛是老街发出的一声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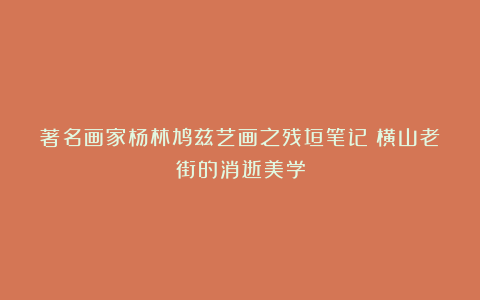
对面通天府建筑群的断壁残垣上,雨水冲刷出的色痕,恰似一幅天然的水墨长卷:上部是黛瓦留下的青黑,深沉而古朴;中部是黄土墙的赭石,带着岁月的厚重;底部则是硝碱泛出的霜白,清冷而孤寂。
这种由时间亲手调制的色彩,是任何颜料都难以模仿与企及的,它承载着老街的历史,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而繁复,线条流畅优美,展现出工匠们高超的技艺。阿婆颤巍巍地伸出手,手指划过柱础上的凹痕、坍塌的楼板、歪斜的门扇,那是几代人生活留下的痕迹,是岁月打磨出的包浆。
她缓缓说道:“以前这宅子里住着十三户人家,夏天孩子们就在这青石板上打赤膊睡觉。”她的家在大门的左边,尽管四周的房屋都已破损颓败,家中也显得阴暗潮湿,但在她的精心打理下,屋内却显得整洁而干净。
已经褪色的老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每一件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默默诉说着横山老街旧时居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
这个细节让我想起横山的民间谚语“黄蔴一线牵渔樵,孙家河上横山桥”,此刻,我突然理解了水运断绝对老街的致命打击——当龙窝湖泵站斩断横溪河与长江的血脉,带走的不仅是商船,更是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生存方式,老街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正午时分,阳光垂直照射,老街显露出它最残酷的美学。坍塌的山墙形成了天然的取景框,将湛蓝的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形状,仿佛是一幅抽象的艺术画作;蛀空的梁木在阴影里编织出蕾丝般的纹理,细腻而精致,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残缺之美;某户废弃灶台间的破碗柜中,竟长出了旺盛的常春藤,翠绿的藤蔓沿着碗柜的边缘攀爬,在阳光的照耀下,叶片闪烁着生机的光芒。这些自然与破败交织的景象,构成了一幅奇妙而又令人感慨的画面。
我坐在画架前,在宣纸上尝试着运用“屋漏痕、锥画沙”以及水墨渲染的各种技法,努力表现这些自然而丰富的细节。水墨顺着宣纸纤维自然晕染,恰似岁月渗透的轨迹,将老街的沧桑与韵味一点点呈现在纸上。
然而,这种美又是如此脆弱——可能下一场暴雨就会让某个存在了两百年的转角彻底崩塌,也可能某个拆迁文件,正在某个办公室抽屉里静静等待,一旦它被开启,老街的命运或许就将被彻底改写。
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有了《横山老街頽垣残景赋》的画作与文案:
“橫山故地,昔為徽商輻輳之所,舟楫往來,市廛喧囂。今觀此場景,但見頹垣斷壁,梁木傾欹,舊時老屋庭院,盡付荒蕪。然老樹盤根,新枝怒發,藤蔓糾纏,生意勃然。
枯榮相雜,恍若歲月之痕,斑駁其間。昔之雕甍繡檻,今唯殘椽碎瓦野蔓縱橫。然則頹敗之中,自蘊天趣,筆墨所至,尤見蒼茫。夫盛衰之理,自古如斯,而造化之妙,恒在寂滅處見生機焉”。
老街写生题记二:
《老屋旧梦》
橫山老街,昔者商旅輻輳,舟車駢闐。今過其地,但見頹垣殘棟,梁木傾欹,戶牖洞開如瞽者之眶。每行古城舊巷,睹此景象,未嘗不駐足興懷。憶昔徽樓比櫛,青石映履,市聲沸天,而今唯餘荒草蔓階,野藤攀壁。然殘椽斷瓦之間,雜花自開;敗壁頹垣之側,新綠競發。廢墟得野趣,荒穢藏生機。畫者獨鍾此境,蓋因殘缺自有真韻,凋零別含天趣。嗟乎!盛衰相繼,新舊迭更,此殆造化之微意歟?”
午后,我继续在横山老街写生。几个老街居民好奇地围拢过来,他们的目光落在我画纸上的残垣断壁,眼中满是不解。“为什么不去画新区的喷泉广场、高楼大厦?”他们的疑问,让我想起几年前在徽州写生的经历,那时也有孩童问过类似的问题。
不同的是,那时的老房子还有人居住修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而今横山老街的衰败却已不可逆转。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枯荣相杂,恍若岁月之痕,留住历史更重要,残缺有时也有另外一种艺术的魅力。”
然而,他们似乎并不能理解我的话,带着疑惑慢慢走开,背影逐渐消失在巷弄拐角,如同消失在时光隧道,只留下我继续沉浸在老街的故事与风景之中。
黄昏时分,夕阳为老街披上了一层慈悲的面纱。金色的阳光将“通天府”的投影拉得很长,那变形扭曲的阴影竟与古时商船的风帆形似,仿佛时光在此刻重叠,往昔的繁华与如今的衰败在光影中交织。我在完成最后的设色时,故意在檐角留出飞白,让观者能想象那些消失的瓦当原本的模样。
收笔的那一刻,我突然领悟: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老街的残缺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留白?那些坍塌的部分,正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只是,很可惜,这种留白,有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的泯灭和消失,成为永远的遗憾。
暮色渐浓,天空的颜色由金黄逐渐转为深蓝,我收拾画具准备离开。最后一抹余晖照在通天府的残墙上,忽然照亮了原先没注意到的一行模糊字迹。我凑近仔细找寻,却又难以辨认清楚。
我想,这或许就是横山镇,留给过往的人们在心灵中的那一抹印记吧。这惊鸿一瞥的发现,让我想起地方志记载的“买不到的东西到横山买,卖不掉的东西到横山卖”的盛况。
此刻的老街,连自己的存在都快“卖不掉”了,即将被岁月的洪流淹没。但或许正是这种即将消逝的特质,赋予它最打动我的力量。就像我的写生稿上那株从墙缝钻出的野梧桐树,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却依然顽强地开花结果,它的果实落在残瓦上,溅出紫色的诗行。
每年的春天,紫色的梧桐花,都会年复一年的,在衰败的残垣断壁中绽放,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而横溪河的水声,仍在静静地流淌,讲述着那些未被记载的故事,诉说着老街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寂寥,临行时,我看见几个年青人,在横山桥码头的驳岸上,正兴致勃勃地在横溪河钓着鱼,时光交错,这就是眼前真实的生活场景。
2025年夏于芜湖 杨林
杨 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黄岳画院院长、徽州碑林艺术馆馆长,零界点:朱零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全国首届扬州八怪杯书画大奖赛一等奖,尚意2017全国美展最高奖(中国美协)、入选2017泾上丹青全国美展(中国美协),2017年安徽省美术大赛最高奖,2018中国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画展最高奖(中国美协)。
入选2018山水砚都多彩肇庆全国美展(中国美协)、2019年弄潮杯全国中国画大赛优秀奖(西冷印社主办)、2019首届吴昌硕国际艺术大奖赛二等奖(西冷印社主办)、建国70周年安徽省美术大赛优秀奖(安徽省美协主办)、2020″中国美术世界行”成果汇报展最高奖(中国美协)、第四届”弄潮杯”钱塘江金石竹木拓片展二等奖(西冷印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