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远非简单的“折中”或“平庸”可以概括。它既是贯通天道的宇宙法则,又是指导人生的实践智慧。
中:甲骨文象形为“旗帜立于中央”,《说文解字》释为“内也,从口从丨,上下通也”,既指空间方位的居中,更隐喻“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庸:取自《尔雅》“庸,常也”,暗含“永恒普适的法则”。北宋程颐解为“不易之谓庸”,揭示其超越时空的真理属性。
中庸组合形成独特张力:既强调实践层面的动态调节(中),又指向终极层面的永恒法则(庸),如同《中庸》开篇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思想从认知维度上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区别于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庸构建“A且非A”的兼容思维。如“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的互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情感节制,朱熹比喻为“如称天平,两头轻重恰如其分”,强调对复杂情境的精准把握。
从伦理维度上实现道德实践中的动态平衡。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揭示:“中庸不可能只存于静时,要在事上磨炼”。
在《吕氏春秋》中,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这两个故事所引发的关于“取其金则无损于行”和“劝德”的辩证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子贡赎人,他出于高尚的道德自觉,没有领取应得的赎金。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令人称赞的高尚行为。然而,深入分析却会发现,这种行为可能会在无形中树立了一个过高的道德标准。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子贡那样雄厚的财力,若赎人后不领赏金成为一种被推崇的普遍标准,那么一些本有意愿赎人的人可能会因经济压力而望而却步。比如在一个经济条件普遍不宽裕的社会中,人们在面对赎回他人时,可能会因担心无力承担损失而放弃这一善举。
子路受牛,则呈现出了另一种情形。子路勇敢地救了溺水之人,并欣然接受了对方所赠之牛。这一行为在当时或许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子路的行为有贪图回报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子路的接受恰恰起到了“劝德”的作用。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做好事是会得到回报的,这无疑鼓励了更多的人去积极行善。就如同在一个社区中,如果有人因为帮助邻居而获得了一定的感谢和回报,那么其他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会更愿意伸出援手。
我们不能仅仅凭借表面的道德表象来评判行为的优劣,而应该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去审视其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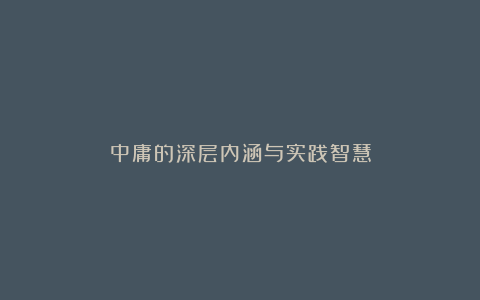
从政治维度上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弹性智慧。
在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派与大夫派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其本质绝非仅仅是表面上的观点交锋,而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这一深刻命题的中道探索。
贤良文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倡导市场的自由发展。他们认为,过度的政府干预会抑制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例如,繁重的赋税和严苛的专卖制度,使得百姓不堪重负,商业发展受到束缚。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某些朝代因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商业凋敝,社会发展缓慢。
大夫派则坚信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指出,在某些关键领域,如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和销售,只有通过政府的集中管控,才能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战略物资的稳定供应。他们以过往国家面临危机时,政府通过有力的干预措施成功化解危机的实例为依据,强调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这种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和探索。在古代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政府一直被视为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维护者,而市场自由的理念则相对较新。贤良文学派与大夫派的争论,实际上是在传统与新兴观念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深入摸索。
无论是贤良文学派还是大夫派,他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关系需要不断地调整和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盐铁论》中双方的争论,为后世研究和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中庸思想对当代人生有什么启示呢?
从职业发展上,在当今这个多元化且快速发展的时代,“在专业深耕(’攻乎异端’)与跨界融合(’君子不器’)间寻找支点”这一命题显得尤为重要且极具探讨价值。
所谓“攻乎异端”,意味着在专业领域内进行深入的钻研和探索。医学领域的屠呦呦,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青蒿素的研究,最终成功地为全球疟疾治疗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们,正是凭借着对专业的深耕,才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而“君子不器”则倡导打破界限,实现跨界融合。比如苹果公司,原本专注于电脑领域,却凭借着创新的思维和跨界融合的理念,成功地将其技术和设计优势延伸至手机、平板等多个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
然而,要在专业深耕与跨界融合之间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支点并非易事。这需要我们对自身有清晰的认知,明确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同时还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准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的需求。
从情感经营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人类在情感交往中,对于个人空间和亲密程度有着独特且复杂的需求。就如同刺猬,它们在寒冷的冬日想要相互依偎取暖,但靠得太近又会刺伤彼此。比如,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一方可能过于依赖另一方,时刻想要黏在一起,这看似亲密无间,实则可能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情感的失衡。许多长久而美满的亲密关系都在不自觉地遵循着“刺猬效应”。例如古代的夫妻相处之道,虽不如现代这般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但也懂得相互尊重,给彼此一定的空间去发展个人的兴趣和事业,从而使关系得以长久维系。
总之,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中,既能让双方感受到温暖与关爱,又能避免因过度靠近而产生的摩擦与伤害,是构建健康、和谐、持久亲密关系的关键所在。
这种流淌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智慧,正如李泽厚所言:“它不是康德式的绝对律令,而是中国乐感文化中’度’的艺术”。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迷茫中,中庸之道或许能提供一种既非相对主义、又非教条主义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