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7日离世在北京,致念悼词的,却是李先念。
他说“郑位三是一位革命老战士,为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既是如此,55年授衔,名单之上为何不见郑位三的名字?
无疾而终的指示信
1935年7月,吴焕先给郑位三等人留了封信,指示众人,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要就地坚持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两特委要合并组织成一个特委,通过小的胜利提高战斗力,最大限度的牵制敌人,配合整个西北的革命。
然而,这份重要的指示信,郑位三并没有收到。
负责传递的同志,是第3路游击师的政委李志英,可李志英在带领游击师寻找郑位三等人踪迹的过程中,被叛变的特务队队长枪杀,这封信就这样没了。
失去了省委的指示,战斗还是要进行的,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郑位三留在了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不是件可以小觑的事情,敌人二十几个团的兵力依旧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一旦掉以轻心,付出代价的直接就会是伤亡。
郑位三决定采取“兜大圈子”的战术,一会东,一会西,神出鬼没之外,还会利用有利的地形伏击。
敌人在1936年的秋天再度调兵“围剿”,分析完地形之后的郑位三决定“化整为零”,将活动区域挪到敌后,换场地的同时,还活捉了国民党新上任的督察专员汤有光。
指示信不知所踪,电台也没有,郑位三所在的红七十四师已经算是和上级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深山老林且缺乏对斗争形势的了解,完全劣势的情况,郑位三依旧没有放弃。
“老乡,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部队从这边过啊?”
走一路问一路,了解了敌情,也摸清了道路,能够在厚积中厚发,是因为郑位三本来就是一个吃得苦的人。
他出生在1902年的湖北黄安,家里是开中药铺子的,医学能治病却非郑位三的志向所在,于是在1918年的夏天,他徒步300华里,风餐露宿走了5天去报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
有心人,天不负,郑位三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也瞬时将自己的本名“郑植槐”舍弃,换上了位三。
学是能上了,走上革命道路,多亏了萧楚女的影响,进步书刊的加持,让郑位三近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从只是对现实不满,发展成了要改造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落后,是因为反动政府勾结洋人对中国人民实行剥削导致的,要想改变,就要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
肺腑之言为人生未来的发展定下基调,游击战中的显著成功,也让郑位三得到毛主席“配合的好啊”的首肯。
但这革命之路可不是好走的。
有一次敌人追的紧,郑位三咳的吐血,战士们将他抬上担架就想走,硬座对身体不好不说,对部队的行军速度也只会是拖累,最后还是郑位三巧用地形摆脱了敌人。
相较于顺遂的革命之路,郑位三身体所挂的红灯,好似从来都没有熄灭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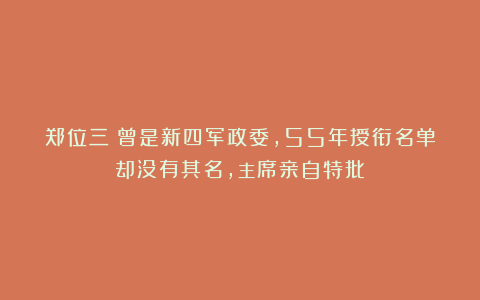
敌人眼皮子底下的自保
创建鄂豫皖苏区的1930年,郑位三染上了疟疾,整个人就虚弱的躺在一户老乡家里。
敌人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乌泱泱的一群人赶来村子抓人,这可把乡亲们着急坏了。
“位三同志,敌人马上就要搜查到这里了,我们把你藏起来吧”。
说藏也有可能,可万一曝光了,无辜村民就要为自己陪葬了,郑位三人虽然虚弱,脑子却依旧转的很快,让乡亲们帮忙将自己抬到村里最大的那棵柳树下面。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狠心的对你。”
“敌人来了你们就说我是传染病人,相信我,他们不会靠近我的”
果不其然,进村的敌人很快发现柳树下面有个床,一打听,里面躺着的,竟然是一个传染病人,就象征性的用枪刺挑了挑被子,倒也是没有直接打开来看。
虎口逃生的惊险不过如此,拖累的是病,休养的时候,学习就成了极大之乐,在鄂豫皖地区,郑位三可是有着“小列宁”称号的。
他对马列主义的勤学苦思众所周知,有次儿子听说了斯大林的一句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郑位三就把这句话所在的全文翻找出来,放在了儿子的面前。
思想上的德高望重,指挥上的有理有据,理论与实操的相辅相成,让郑位三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重回鄂豫皖根据地,还在1940年的2月,担任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政委。
徐海东加上郑位三的强强联合,有力阻击了敌人,来一次,击回去一次。
可这蒋介石的把戏实在是多,竟然在1941年有预谋的发动皖南事变,郑位三再度出击,以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的身份,配合张云逸在淮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同李先念等人在1946年6月的中央突围,也成功粉碎国民党军想要消灭中原军部队的企图,配合其他战场的同时,顺势拉开解放战争序幕。
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都知道郑位三这号人物,可除却军事上的成就,他对未来的预判也是极具前卫。
“等到我们胜利了,农民都是骑着自行车到田里种田,将来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要坐着汽车到基层检查工作”。
饭都吃不饱的情况说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以为郑位三在讲笑话,别人笑他幽默,郑位三却清楚,描绘的一切都不是幻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果不其然,改革开放之后,战争年代绘制的蓝图真的成了现实,不同的是,原本发光发热的他,忽然间偃旗息鼓,没有了一份“具体的工作”。
得到众多领导人首肯的郑位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赋闲不忘革命
战争年代,有才者不能停下来,国家安定之后,体弱多病的郑位三向组织提出留在湖北休养。
组织同意了,没过多久意识到北京的医疗条件可能要更好一些,便又在1955年的4月,将郑位三接到了北京定居。
这一年,新中国有了第一次授衔,也首次实行了工资制度。
因为身体的原因,郑位三从1948年就退出了主要工作,不满足授衔的条件,但工资方面,毛主席和周总理却一致觉得,对党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郑位三可以列为行政三级,享受政府副总理级的待遇。
每月300元的津贴,郑位三一分不动,全部用来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问题。
组织给他分配了厨师,他也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有什么就吃什么,早在1942年与妻子结婚就立下规矩:生活上不能搞特殊。
名利上从身边碾过,郑位三却从来不知名利是什么。
报刊、纪念馆、书籍,不提他的名字,可以;政委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也不在乎;昨天还是政治部的主任,今天就要带着一百多名老弱病残的战士打游击,郑位三也并不觉得有什么。
他对是非的判断只有任务的区别,留给子女最大的遗产,就是一句“一切靠自己”。
不要求什么,却总想着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人在休养,一颗心却闲不住,身体稍微好一些,就要去民众中间去了解民情。
当然,郑位三做的也并非只有这一件。
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后,政府的旧职员仅湖北就有4000多人,关于这些人的任用还是解聘是一向棘手的工作,有人提倡“包下来”,有人提倡“不接近”,只有郑位三,翻阅大量的旧职员档案,夜以继日的分析比较,区别了好坏。
李先念收到郑位三送来的报告很是高兴,一个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想着这位老友的身体,他还是说了一句“位老,要好好休息啊”。
“先念,拿着组织的俸禄,却一点不出谋献策,这不合适啊”。
即便钱没有一分花在自己的身上,郑位三还总觉得自己沾了组织的大光,想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做些回馈。
无奈时光匆匆,1975年的7月27日,郑位三离开了人世,组织给予他的敬重,是一句“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
追悼会在8月3日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致念悼词的是李先念。
“郑位三同志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两日之后的《人民日报》,版块的四分之一都是跟郑位三有关的内容。
框住的是报道,念不完的,是郑位三的好,这位革命老兵,生动诠释了舍己为人,诚如年轻时的一句,劳动人民的政权已经建立,属于中国,属于所有被前辈们托举起来的新生力量的未来,只会是光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