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雅舍
黄崖山惨案始末
赵学法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清廷衰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重了劳苦大众的负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既外仇敌寇,内恨官府,又无能为力,摆脱痛苦,幻想独立、自由、平等在情理中。北宗太谷学人张积中顺应了民众的这一宿愿,不顾客观现实条件的冷酷,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当时肥城北部山区的黄崖山,构建“世外桃源”,固执地进行“乌托邦”式的探索试验,结果不为专制文化和封建官署所容,最终酿成了惨绝人寰的黄崖山一案,万余名善男信女在清军隆隆的炮声和血腥的屠刀下,顷刻间化作亘古冤魂,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这一惊天惨案,既宣告了民间避世思想的破灭,启示人们另寻自身解放的途径,也以血的教训告诫后世,学术研究不能走火入魔,滑向极端。
一、另类太谷学人
太谷学派系兴起于清道光年间,流传于苏、鲁、皖、浙一带的一个民间思想流派。创始者为周星垣,号太谷,安徽石埭(今池州市石台县)人,世称周太谷。当今研究者认为,太谷学派是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但在传授方式和学术思想上又与儒家学派有所不同,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的一些观点而形成的新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教天下”与“养天下”,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都具有启导意义。起初,周太谷在家乡安徽石埭一带传徒,弟子达数千人。官府恐危及朝廷,将其逮捕并准备处以死刑,后经狱卒相救,周太谷才幸免于难。他隐迹江湖数年后,于道光初年来到扬州,以行医为生,经常出入茶馆市肆,言行怪异,不流时俗,因而受到扬州有识之士的关注。扬州书生汪全泰率先求道,成为周太谷在扬的第一个门徒,世称大竹先生。不久,颇有文名的七旬老翁许鹤汀也拜太谷为师,遂使周太谷名声大振,信徒日众,上至达官显贵,下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影响颇广。(参见《安徽通志箓》卷六《太谷列传》。)
周太谷对儒家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常“发往圣所未发,释先儒所莫释”。在宇宙观方面,他认为“乾,阳气也;坤,阴气也;屯,二气交于下也;蒙,二气凝于上也。需讼者,运寒暑也;师比者,建畿国而分井邑也。”又称“夫大赤之气,运日生而不坠,深黑之气,载出海而不泄。”把阴阳之气具体为能“运日星”的“大赤之气”和能“载山海”的“深黑之气”,而日、月、风、雨、雷、电、星则是两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周太谷把“诚”注入生命之学,发展了传统的生命之学。周太谷年轻时曾游学四方,分别拜精道学的韩子愈、通佛学的陈少华为师,谙熟佛、道两教,所以在他的学说中带有佛、道的思想,认为儒、佛、道的学问各有所长,是可以相互兼补的。“心息相通”是道家练气之术的入门要诀,周太谷讲学时常带有气功之类的养身之道,经过传人张积中、李光炘、黄葆年等人的发挥,演化成“心息相依”,被当成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成为太谷学派的精华所在。周太谷说:“人之始生也,知视动而视动之心已放矣,知言听,而言乎之心亦放矣。欲求其放心者,必得非礼勿视动。非礼勿言听。言近乎听,言认则不闻;视近乎动,动无往则不睹。厥后已放心之复其初也。”“言认”是不说话,“无妄动”是不做无谓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使人的心转“复其初”,这就是“心息相依”。张积中把“心息相依”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了起来,说“慎动则息依于心,沉思则心依于息。人能心息相依,则言自谨而行自慎。”“以心省察其息,以息涵养其心,故瞬有存息有养。”黄葆年不仅把“心息相依”作为养身之道,还作为门下弟子修习“圣功”的准则,并对“千经万卷”作了更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心不明不能依息,心不纯不能从心。龙川夫子有曰:心依息便是居仁,息从心便是由义。心不明,息昏之也。息不定,心乱之也,故心息相依可包罗千经万卷,千经万卷皆是心息相依注脚,识得心息相依,读书可,不读书亦可,否则多读书愈加黑矣。庄子仙心,心息相依,只在仁为己任。”还说“心息相依是格物。”太谷学派在讲授形式、入学规矩诸方面均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参见《安徽通志箓》卷六《太谷列传》)太谷学派的遗著主要有《周氏遗书》《张氏遗书》《李氏遗书》及《太谷经》《语录》等百余种,均未刊行。(参见《安徽通志箓》卷六《太谷列传》。)
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苏仪征张积中和李光炘表弟兄俩从仪征来扬州,与周太谷辩论三昼夜后,拜在周太谷门下。周太谷对他俩极为器重,说“启予者炘也,助予者中也。”第二年,周太谷病危,临终时嘱咐李光炘“传道于南”、张积中“还道于北”(参见同上书)。
太谷学派北宗传人张积中(?~1866),又名张中,字石琴,后又自号白石山人,贡生,江苏扬州仪征人,在兄弟辈中居七,世称张七先生,史书中又作张七或张琪。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亲友在清政府中任职者颇多。其胞兄张积功,咸丰初年任山东临清知州,于1854年太平天国北伐援军攻克临清时“殉难”,甚得清廷赏识,因其无子,遂以张积中之子张绍陵为嗣袭荫。张积中堂弟张积馨,同治、光绪年间做过四川、陕西按察使及代理陕西巡抚,后为免受其牵连,又改名张集馨。张积中姨表兄吴载勋,1852年后历任山东文登、武城、淄川、泰安、历城知县,1861年署理济南知府,与张积中关系甚密。曾任范县知县的秦云樵,既是张积中密友,又是其儿女亲家(子张绍陵岳父)。咸丰年间曾任清廷江北大营军务帮办的雷以諴,也是张积中的好友。张积中年轻时读书颇多,自取得贡生功名后却屡试不第,遂绝意仕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农民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1853年2、3月间由武汉经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此前,在扬州一带讲学授徒的张积中受到钦差大臣周天爵青目,以“奇才”予以保荐,得入两江总督陆建瀛幕府。3月19日太平军攻克扬州后,张积中又在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諴幕府参与机要。4月太平军破江北大营,攻克扬州,雷以諴被革职查办,充军新疆。为避祸乱,张积中乃举家北迁山东,投靠在济南做候补知县的儿子张绍陵及表兄吴载勋。因不愿在官场中应酬,遂“以会城不可居”为由搬出济南,转往长清马山投奔亲友,后来“卜居牛山(今肥城境内)后之书堂峪”。不久,肥城中黄崖庄(今属济南市长清区)生员刘耀东闻讯来访,“见积中大悦,执弟子礼焉,割宅以居积中,积中遂迁中黄崖”。([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肥城县志·黄崖纪事略》。)此后张积中即开始广泛传播本派学说,还在济南、泰安及其附近地区吸收了部分门徒,其中即包括淄川东南乡东坪村的司冠平等人。他们这一学派成员不很多,在济南及附近地区游山玩水,讨论学术,过着相对平静的隐逸生活。
1859年,捻军由皖北大举进入山东,济南近郊常见捻军“边马”活动,长清、肥城亦常有捻军过境,扰乱了张积中的平静生活,遂又应邀举家东迁淄川、博山交界的东坪,住在弟子司冠平家中。同年,领导过淄川农民抗漕斗争的刘德培被捕脱逃后也至司冠平家,积中遂与刘德培相识,两人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三续淄川志·兵事门》,民国九年石印本。)司冠平后来参加了刘德培1861年领导的淄川起义,占据县城,并曾于1863年3月奉命南下邀请捻军与长枪会军北援淄川。1863年8月,淄川起义失败,刘德培自刎殉难,司冠平则逃往黄崖,后来在黄崖惨案中罹难。
1861年3月,捻军剑指博山一带,地方又为清军骚扰,张积中在东坪无法居住,只好举家迁回黄崖故居。黄崖山当时地处肥城、长清交界的群山之中,山形三面环拱,南北峭峰对峙,中广百亩,山顶平坦,而四周险峻。山麓自北而南分布3个村落,分别为北黄崖庄、中黄崖庄、南黄崖庄。中黄崖庄、南黄崖庄属肥城,北黄崖庄属长清。在张积中到来之前,山岭上已建有石寨,系当地绅士、民众为避难而修筑。至此,张积中以为“北方当乱,此(山)可避兵”,遂“筑室山上”。(《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当时,捻军在山东南部活动频繁,闻警前往黄崖山以求避乱者渐多,张积中遂“益以其术教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肥城县志·黄崖纪事略》。)吴载勋时尚在历城知县任内,为署理山东巡抚清盛所赏识,4月履新济南知府,同年8月,因防守省城有功,奉旨赏戴花翎。(《吴载勋履历》,载《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第146页。)吴载勋在济南官绅中积极宣扬太谷学派学说,“推崇积中不容口”,省城官僚士绅在吴载勋的引介下,赴黄崖山拜张积中为师者渐多。张积中遂在原有石寨基础上,继续扩修山寨,购置弓弩甲仗,组织徒众“习战事”,以为自保守御之计。(《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闻者以为可恃”,遂辗转相告,投奔黄崖者渐达百余家。([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肥城县志·黄崖纪事略》。)当年9月,捻军进至长清一带活动,尤其是1862和1863年,捻军深入山东腹地,四周远近士绅民众前来黄崖避乱者骤增。张积中遂多方予以接济,“凡入山避难者,山上设粥,山下设汤,来者皆得饮食”。继而,张积中又在黄崖山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士绅民众多感其惠,前来归附者益众(同上志书)。与此同时,张积中在黄崖山“垒石为两寨,自筑大寨山巅,引河水环山麓”,并不断购进武器,增设武备房,随后又增设了文学房。(《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山顶所筑大堂,为祭祀堂,“旁列两庑,重帘回廊,崇阶复户”,阶下为池,有桥为之间隔,有如泮池。池南所筑台为咏归台。左右各有门,左为天根,右为月窟。门外石径迂折,为采药径。山腰增置小亭,称对松亭。([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肥城县志·黄崖纪事略》。)张积中为约束徒众,告诫他们:“从学者,深戒吝财恋色,资装妻妾,勿须顾问。”
从此,张积中“以神自畜”,不再轻易接见来访、投奔者。远方初来山者,一般安排在文学房,令吴载勋(1862年10月因淄川城失陷被革职,随后来黄崖投奔张积中)、赵建、刘耀东等授读所刊《指南针》。五日一听讲,乡农不能诵习者任其去留。需进谒张积中者要泥首(以首触地)九拜,张积中往往正襟高坐,并不答言。周太谷孙妇李素心、张积中侄女张静娟,在山寨中的地位仅次于张积中,专屋列居,进谒者如同见张积中,也要泥首九拜,两人亦高坐不答。即使是吴载勋等其他入门较早之男性高足也“莫敢抗礼”。张积中每年数次在祭祀堂礼神,总是深夜参拜,礼节繁缛,李素心、张静娟均盛装挟剑而侍,旃檀燎烛,熏赫霄汉,数十里外可见其光,不是生徒者不得入堂同参。(《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这时的张积中已走向了神坛,披上了宗教神秘外衣,屏蔽了太谷学人的面目,沦为学界的另类。
黄崖地方本颇荒僻,自张积中筑室定居以来,连年置田筑室,大兴土木,致“屋宇鳞次”,逐渐成市集。张积中还规定,“凡入山者,不得私其财,纳其半籍”。这样,张积中逐渐积累起一些资本,遂在当时的肥城孝里铺(今属长清区)、济南城内城外、东阿滑口、利津铁门关、海丰埕子口以及安丘、潍县等地,相继设肆(店铺)贸易,分别取号“泰运通”、“泰来”、“泰祥”、“泰亨”等,([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肥城县志·黄崖纪事略》。)盈利以补山寨之用。
二、揭秘惨案本相
黄崖山惨案始于平民王小花迁居。
1865年10月,潍县平民王小花治装举家迁往黄崖,知县靳昱闻报甚感奇异,遂令差役掩捕,刑讯逼供,王小花据实而招。靳昱在给山东巡抚阎敬铭禀文中报称:“拿获王小花,供称曾有人召其往黄崖山,认张积中为师,彼处聚众多人。”阎敬铭派员密查,据报:“张积中系前任临清州知州全家殉难之张积功胞弟,世袭云骑尉,现在山东候补知县张绍陵之本生父,习静居山,以授徒讲书为业。即省中官幕亦有挟眷居山者,并无违悖情迹。”阎敬铭又派员各处访闻,均称:“张积中于咸丰年间曾为前湖广总督臣周天爵明保,并在两江各处戎幕,现年逾六十,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人。”但阎敬铭又以王小花语涉可疑,遂饬令靳昱将其提省究办,研审数日,知王小花并不认识张积中,系听友人传言,慕名而往。阎敬铭认为张积中既系忠荩之家,宗族亲戚科第簪缨,似不至于聚匪为非。此案遂延宕未结。
1866年10月间,益都知县何毓福访闻县内民人冀宗华等纠众谋乱,遂禀告青州知府阎廷佩,各率勇役将冀宗华及其同伙冀兆栋捕获。冀宗华等供称:“同党有冀雄及临朐人郭似圊(嗣清),潍县人刘显庚、刘洪鳌、陈寿山,同师黄崖张琪(积中),师命率集人马,期九、十月间举事。”刘显庚等人闻同党被捕入狱,于是潜逃隐匿。何毓福搜查城内其储藏武器之处,仅得刀矛数件及四言示谕。临朐知县何维堃率兵役掩捕余党,郭似圊等率众持械反抗,格伤兵役,终以寡不敌众被缚。及审讯,供言与冀宗华所言相同,同时供出同伙刘名教、阚益成等“均结盟师张琪,期十月十九日陷济南,再陷青州,令似圊、洪鳌集众,至期趋省”。接着何维堃又捕获四人押解青州,阎廷佩督同新任益都知县魏正藻审讯,并将结果一并上报抚署,内称:“拿获匪犯冀宗华、冀兆栋,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为师,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令彼等赴青州一带勾匪,定期九、十月间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济南。”阎敬铭飞饬提犯至省究办,一面又令山东布政使丁宝桢派兵拿张积中到案对质。(《阎敬铭围剿黄崖山奏折》。)
与此同时,山东布政使丁宝桢也接到益都、临朐两县禀报,当即由省城派巡捕官守备唐文箴会同肥城知县邓馨、长清知县陈恩寿,于11月1日赴黄崖山欲捕拿积中到案。唐文箴、陈恩寿先至,宣称奉命“谕积中入省,念其老,且世大家,无意杀之也”。张积中深藏山寨,闭匿不出。唐文箴等守至夜间,山上众人闻讯聚集,准备质问进山官员。已经准备出山的吴载勋闻讯,急促唐文箴等速回。唐文箴等遂乘马连夜奔返,山上民众有多人随后追赶,陈恩寿家人黄绅被杀。刚抵黄崖的邓馨,正要入寨,突闻炮响,急转马头,原路退逃,其仆从也被杀。(《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
当时,在东平行营的阎敬铭,得到禀报后仍然存疑。鉴于张积中子张绍陵系山东待补知县,遂派员责令张绍陵随同丁宝桢所派员弁共赴肥城,劝父出山自白。此时张绍陵已乞假准备赴扬州,行前入黄崖寨与父话别。阎敬铭令已出山的吴载勋给张绍陵传话,对其父言明利害;复出示谕十余通,遍贴寨门内外。张绍陵将阎敬铭的话复述于父,劝其出山。张积中怒道:“积中此生,决不履公庭,必欲积中出者,积中出就死耳!积中亦丈夫也,伏剑而死则可,桎梏而死则不可,积中以身殉学矣,何出为!”(转引自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一书,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11月2日,山上民众将各处山路堵塞,禁绝人行,并集合各附山居民入寨防守。3日,山顶矗立红旗一面,寨墙则遍立尖旗,寨前为纯黑色旗帜,寨后为纯红色旗,而沿山路运送柴薪、粮草、煤烛进山者络绎不绝。当夜尚有山民数百名下山至下巴、归德、马家山、辛庄及肥城石罔、东张庄活动,并向乡民征购马骡。又有武定府盐民满载武器,自大清河泛舟船至孝里铺上岸入山。山之四周,皆闻炮声,黄崖南、北、中三村寨居民陆续迁往山顶。所有寨隘也都安装了巨炮。阎敬铭虑及各县禀报言过其实,遂檄营务处道员潘骏文往黄崖,先进驻孝里铺,再饬吴载勋招积中下山。吴载勋奉劝数次,张积中仍不出山。不久,丁宝桢由省城骑马到长清,令吴载勋与长清知县林溥入山谕积中,至则不得入,时道员潘骏文也进驻平阴,均以张积中“逆迹大著”,先后上报阎敬铭。(《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
11月4日,山上民众头裹红巾,分路下山,先后杀东张庄乡绅数人及驿递马夫两名。同日,在东平行营的阎敬铭,也获得了黄崖山变故的消息。在他看来,黄崖已成匪徒啸聚之地,加以黄崖逼近省垣,终系心腹之患,尤其是又以“才人”张积中为首举事,“计必多端”;再者,捻军仍在运河之西盘旋,一旦与黄崖勾结,局势将更难控制。因而“必须及早除灭”。鉴于黄崖山势深广,不易集结兵力,形成包围之势,遂函嘱赴嘉祥剿捻的山东按察使潘鼎新,先暂守河墙,若捻军南返,即分营赴黄崖助剿。随后,阎敬铭一面飞调河防各军,匀抽队伍,派参将姚绍修带两个营1000人为第一队,游击王正起带四个营2000人为第二队,阎敬铭自督知府王成谦带八个营4000人为第三队,并调副将王心安带三个营1500人为第四队,先后于11月5日、6日“星夜向平阴进发”。另外,又先期调派千总王萃带其马队,随营务处潘骏文星驰黄崖,踩看山路。随后,阎敬铭即督各军兼程并进。11月5日,千总王萃马队先行抵达距黄崖18里之水里铺,将活动在当地的部分黄崖民众击退。
11月7日以后,阎敬铭所带各军先后到达长清南乡,形成对黄崖山的包围。11月7日,继王萃之后到达水里铺的第一队清军,在姚绍修指挥下,即刻督队入山。小路如线,山民在山路设有站卡,张积中高足刘耀东亲率部分民众驻守,见清军进攻,该卡民众据隘列队抗拒。因民众尽占有利地形,双方酣战多时,官军仍不能入山。姚绍修亲自放炮轰击,击毙民众10余人,并乘山民阵地稍乱之机出击。刘耀东率众阻拒,为清军长矛刺中牺牲。双方激战之际,游击王正起亦率所部清军第二队由黄崖山东口赶到,与姚绍修第一队清军“合力猛战”,民众遭受夹击,力渐不支,被迫往山上退去。是役,清军夺获山民抬炮、鸟炮、竹竿多件,旗帜数十面,并在庄中起获号衣40余件。随后,姚绍修、王正起二军又尾随民众之后展开追击,沿途山民所设各处要路山口石卡,均为清军拆焚占据。清军还连夜分路直登上山,占据山中要害之处,山民不得已全部入寨闭守。
11月8日,知府王成谦也率第三队八个营清军赶到黄崖山,随即分登各处山顶,四面布围,断绝张积中突围之路。9日,各营俱已赶到黄崖山前会齐。阎敬铭察看山寨形势,见出山歧路极多,认为须将各军密布于要隘,层层把守,方能一网打尽;否则一旦攻破寨垣,必有乘间逃脱者,难免将来死灰复燃。但鉴于各军奔驰数日,多已疲惫不堪,遂传谕各营,暂缓进攻,以养精蓄锐;又悬示劝降,以期瓦解山民;还将吴载勋调至行营,令再缮写谕函,派专人送入寨中,令张积中早日出山;同时一面飞饬各军,将黄崖山四面大小远近各个山口全部设防,严令各营各哨分别扼守堵截。适值兖州镇总兵范正坦奉命率兵赶到,济东道卫荣光调来同知刘时霖一个营,泰安知府锡恩、肥城知县邓馨亦各带勇役民团前来助剿,协同先到清军防守。此时,官兵加上团勇,总兵力已达12000余人。
11月10日,副将王心安带所部三个营开始登山,断绝了山寨小泉汲道,使张积中师徒“遂无勺水可得矣”(《阎敬铭围剿黄崖山奏折》。),陷入绝境。
11月11日,阎敬铭派遣入山送函之人下山,带回张积中复函。张积中在复函中除先为自己辩诬外,又告以“不逞之徒,劫令主盟,势不能出”之意,同时要求官方宽以时日,“请暂将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复陈词,婉言解散。若一面进攻,一面招纳,则上宪不能示人以信,困兽犹斗,兄又何辞能劝谕诸同人耶?”(《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这些话被官方称为“要挟狂言”。阎敬铭曾再次出告示称:“寨内居民自行投首,概不加诛。张琪始则闭匿不出,继则入圩自守,并出山焚掠,抗拒官兵,罪无可逭,能缚献张琪者,破格给赏。张琪孤身老悖,岂能禁遏众人,全在尔等,勿为所惑。大兵已集,勒限两日,各自谋生,即张琪自行投首,亦曲示法外之仁。”示谕传入寨内后,迄无一人出山。寨内民众时时开枪抛石,营勇常有被击伤者。是日,张绍陵出谒阎敬铭。阎勒限一日造出寨内官僚居民名册,再令吴载勋致函张积中,许以出降不死。同时,阎敬铭又令诸营将校各挑一队靠近寨墙,分别竖起八尺或一丈高之白旗,上书“胁从罔治,投降免死”八个红色大字。当晚,张积中又复函吴载勋,内称:“人心汹汹,不能举步,须从缓造册。”当时,捻军正在曹州活动。曹州府附近州县上报阎敬铭禀文及淮军刘铭传、潘鼎新两军致阎敬铭公函也称,所获捻军人员有供出“渡河赴救黄崖”者。阎敬铭不核真伪,遂以“该匪逆势已成,难事姑容”为借口,准备次日一早发动总攻(同上书)。
11月12日黎明,按照阎敬铭部署,主攻部队知府王成谦督率所部四个营由黄崖山西面进攻,游击王正起率兵四个营由黄崖山东面进攻,两路夹击,形成钳制之势。山顶大寨地处悬崖陡壁,上山之路又为“羊肠乌道”,极难攀爬,而寨墙借助山势筑成,尤为险峻,易守难攻,但清军却凭借前两日暗中探查的山路及准备好的钩梯,直逼张积中山寨之下。寨内民众为捍卫家园,同仇敌忾,拼死抗拒,一时枪石如雨,先后击伤清军营弁数十名,“血雨流注,呼声撼山”。知府王成谦为争头功,由黄崖山西面接连施放开花炸炮,将寨墙拒敌山民击毙多名。姚绍修乘机率部由西寨门攀墙直上,守备曹正榜亦率部由悬崖之下开路争攀。寨内民众面无惧色,相持不退。
在西寨门一带民众与王成谦西路清军相持之际,东寨门一带民众也与游击王正起所率东路清军展开了浴血搏斗。开始,王正起由黄崖山东口督兵猛攻东寨门,守寨民众顽强反击,终将清军击退。王正起手刃后退数勇,“极力逼赶”,第二次猛攻山寨,始得逼近寨墙,并“扒墙上攻”。寨内民众飞石如雨,冲在前面的清军千总万年清头部被击成重伤;另一千总张福兴腰、腿也被击成重伤,但两人仍“俱各带伤摧坚,略无退阻”。后面的王正起亦极力督攻,奋猛喊呼,所部清军始得从矢石枪炮之中沿崎岖险陡之路,分路同时往墙上攀登,终于攻上寨墙。
与此同时,西路军王成谦部姚绍修、曹正榜两军亦由西面攻上寨墙。时副将王心安也由东山分队赶来增援。这样,三路清军相继攻入寨内。而寨内民众仍然持械拼死抵抗。清军且进且战,分进合击,寨内民众武装精锐七八百人在弓箭、石块等用尽后,为清军尽数“歼除”。其他夺路冲出寨墙者,突围途中遭驻扎各隘口的清军参将宋延德、都司李元、游击郭大胜、守备李炳武、同知刘时霖、县丞裕凯等部分路截杀,鲜有逃脱者。官兵先后屠杀寨内民众1700余人,堕崖落沟而死者不计其数,以致流血成川。张积中父子绝望中率同亲戚及其家属数十人均在大堂自焚殉难,其余民众及入援盐民军千余人,亦先后为官兵悉数捕杀,无一得脱(《阎敬铭围剿黄崖山奏折》。)。官方档案记载,“合寨死斗,无一生降”;“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寄居山上之官僚及弟子等男女共计200余人,也有全家共同自焚而死者。所剩妇女儿童也有400余人,亦均视死如归,“形色洒然,笑语如平常者”。张积中弟子韩美堂等数人被俘后,皆愿从师而死,而别无供词。清军将积中遗体从灰烬中拖出,枭首示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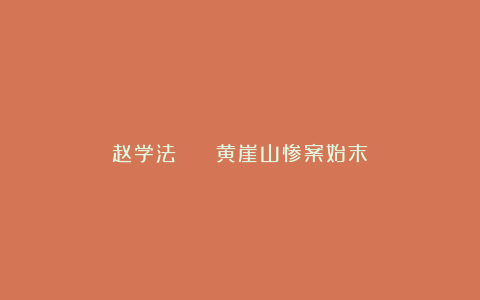
至此,黄崖山惨案画上了血色句号。
三、成败原因探微
张积中苦心经营十年之余的黄崖寨土崩瓦解,万余寨民与附近百姓惨遭屠戮,官府却没有从山寨里找到半点谋反的证据。阎敬铭也感到无法向朝廷交待,便责成王正起、王成谦、王心安三人务必寻来证据。“三王”惶悚返山,遍搜山寨,仍未查到可做谋反罪名的证据。他们无意之间发现一箱戏衣,以此借题发挥,命人寻来七位缝工,将戏衣改为太平天国号衣及龙袍等物,又把黄幔改制成太平天国旗帜,而后又杀死缝工灭口。于是,张积中谋反便有了“铁证”。
黄崖山惨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冤案。从张积中曾经参与清军幕府机要以及四处躲避清、捻两军骚扰的经历看,对清廷并无反叛之心,只是厌恶腐败官场,拒绝与官府合作,一心想寻找一块清静之地,专心讲学授徒,建立一个超越现实的“世外桃源”。至于构筑山寨、加强武备,目的也是出于单纯的自保图存,虽有抗清意图,但并非为了聚众反清。因此,当时就有人愤而不平。泰安学人汪宝树曾游黄崖山,会晤张积中,闻变后写下《吊黄崖诗》等诗文,抒发悲愤,为蒙难者鸣冤叫屈。武定府人李佐贤更是直接称黄崖寨为“桃花源”。他在《焚桃源新乐府》诗中大声疾呼:“民言入桃源,初意似避乱,谁知避乱反蒙乱。有何罪,不可逭。不争不斗不抗违,竟从叛逆一例看。旁观侧目呼奇冤,千秋谁断此疑案。”(转引自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208页。)之所以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是因为这一冤案纯属官府误判,故意构陷,强加莫须有罪名。
北宗太谷学派被血腥镇压40年后,御史乔树楠南下苏州,投师太谷学派,引见人便是太谷学派南宗掌门人李光炘的得意弟子、《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或许因为乔树楠官任御史之故,太谷学派中人就请他代为张积中一案吁请昭雪。乔树楠于次年呈奏了吁请昭雪的奏疏,清廷委托山东巡抚杨士骧彻查具复。然而杨士骧见事体重大,涉及面太广太杂,把已经草拟的奏稿搁置下来,由此张积中黄崖山案始终未得定论。倒是刘鹗在他的《老残游记》中力图为张积中翻案昭雪。据诸多专家考证,《老残游记》第八回至第十三回写武城知县申东造派其弟申子平到桃花山访求江湖奇侠刘仁甫,文中隐写的“西峰柱史”便是影射张积中,而申子平恍如走进桃源仙境的风水宝地描写,即是黄崖山及其周边山色美景的真实写照。
自古以来,历代文人多向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不仅中国文人如此,外国学人亦是这样。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托马斯的《乌托邦》,从欧文在美国搞共产主义实验,再到林语堂的《奇岛》等,无一不寄托着这种超现实的幻梦。这种理想集中反映了劳苦大众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诉求。正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文化取向,催生了张积中构建的理想山寨。
儒家学说经过西汉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经学,又经程朱陆王的第二次改造,发展为宋明理学,被专制政权所采纳,上升为官方的主流文化,在各种文化中起到了主导、统摄和挟制的作用。其他各种文化,要么向专制文化“臣服”,与之融合,因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如佛教、道教文化等;要么就是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排斥打压,逐渐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如墨家非攻兼爱文化等。经过两次改造后的儒家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三纲五常”,其中的核心是“三纲”,而“三纲”的重心又是一“纲”,即“君为臣纲”,父子之纲和夫妇之纲都要服从于君臣之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天子”,是绝对的权威,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要以皇帝为中心,为转移,而经学和理学就是以“三纲”为主要思想武器,忠实地捍卫着帝王的封建统治。这种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各级官吏,以效忠皇帝、剪灭异类为己任,决不允许“王土”之内的独立王国存在,更不允许不臣之人现身于世。黄崖惨案表面上看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实质上是专制文化对别样文化的绞杀。
黄崖山寨的败因,与张积中的极端文化个性有着密切关联。太谷学派自创立起,就因宗教神秘色彩被官方视为旁门邪道,斥之为“妖教”,创始人周太谷就因此而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苦。张积中作为太谷学派北宗领袖,不仅没有接受周太谷的教训,反而独立特行,剑走偏锋,发展为狭隘的另类文化个性,一味敌视官府,仇恨官吏,誓死不相往来,拒绝沟通交流。文化性格决定个人命运,更关乎学术团体的兴废。张积中的偏激文化性格,以悲剧收场势在必然。
而太谷学派的南宗领袖李光炘却是另外的结局。黄崖山惨案后,太谷学派面临重大危机。作为太谷学派的南宗领袖,李光炘通过强化与地方社会力量的联系,努力改善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构建全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李光炘通过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规范学派内部的组织活动,不断加强和彰显其学术属性,淡化其宗教神秘色彩,使太谷学派的社会生态系统得到明显改善。李光炘主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太谷学派继续得到发展并发扬光大。李光炘的著名弟子是蒋文田、黄葆年和刘鹗。“黄崖惨案”后,蒋文田去继承“北宗”,但因黄崖山惨案的负面影响深重,始终未能形成气候;李光炘逝世后,刘鹗主要从事实业,以兴办实业襄助“圣功”之学。黄葆年则成为太谷学派“南宗”传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黄葆年被推为山长,在苏州兴办归群学堂,人称“黄门”。“黄门”在全盛时门徒多达万余,这在晚清、民国期间的学术流派中是仅有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太谷学派才自行解体,湮没在历史尘烟中。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存在着文化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兼容现象。历代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专制政策,是既形之法律,又认真实践的。但是,传统思想文化政策中也夹带着自由主义因素。若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中华文明史上文化的繁荣与思想的发展。因为某种学术思想一旦上升为御用思想,就成为僵死的教条,不可能再有创新发展;文化的进步,学术的繁荣,只能依赖自由文化提供活力和动力。细观封建王朝的专制文化政策,可以发现它的定向性和专用性,它控制与管理的重点是涉及王朝政治、尤其是涉及皇权的那部分内容,即政治思想的专制,对于此外的各种思想意识与文化却是兼蓄并收、持一定开放态度的。太谷学派南北两宗的成败,就是这种文化政策导致的鲜明个例。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清]张曜著:《山东军兴纪略》清光绪年间刻本,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庄建平编:《近代史料文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张 鸣著:《重说中国近代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版。
[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点校本。
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
(原载本文作者著《泰山文化举要(全2册)》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2023年被山东省图书馆列入泰山文献书目。)
作者简介:
赵学法,1950年9月生,肥城市仪阳街道北辛庄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编辑,山东作家协会会员,历任肥城县边院区副区长、党史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泰安日报社编辑部主任、泰安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出版文学专著10部,文化著作1部,主编文史著作4部,发表各类作品800余万字,其中36件获省级以上奖励,业绩登录多家网站,收录多部人物辞典。
舍长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1967年4月生,山东省肥城市边院镇东军寨村人。现任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工作室主任。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初任农村中学语文教师,后从事乡镇党委宣传、文秘、办公室和市纪检监察、市政协文化文史等工作。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参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肥城市卷》《肥城文化通览》《肥城抗战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年亲历记》《汶阳田农耕文化研究》《风物肥城》等著作多部。其中,任《肥城·我的家》特邀主编,《肥城一中创建史略》主撰,《肥城五千年》《左丘明志》《让左丘明绽放光明》《文脉铭读》副主编。《肥城五千年》荣获“山东省政协优秀文史书刊评选一等奖”;《左丘明志》列入《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被评为2020—2022年度全省史志优秀科研成果。另外,策划编纂出版《藏书胜地陶南别墅》《泰山宗谱叙录》等书多部,指导编纂《牛山志》《边院镇志》等。
2014年5月,奉命具体负责筹建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并主持其日常工作(至2018年),创办全国唯一一份专门研究左丘明文化、也是肥城唯一一份具有省级内部刊号的《左丘明文化》杂志,任执行主编6期,主编2期。在省市级文史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北宋李穆墓志考》在2017年第6期《寻根》杂志(河南大象出版社主办)发表;《民国版与清代版〈左传精舍志〉之初步比较》,在2015年第2期《泰安文史》发表。主持的《左丘明文化发掘传承研究》被泰安市社科联确定为2016年度重点社科课题,被鉴定为优秀等级;撰写的课题研究报告获得泰安市社科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
出版个人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并被国家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省政协文史馆等单位收藏。《甲午书简》荣获第三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三等奖。为央视《魅力中国城》节目和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山东卷·肥城篇》提供肥城特色历史文化咨询,并出镜后者访谈。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
主编简介
花非花,一个与文字为知己的女子。喜欢诗和远方,喜欢文学并热烈的追求着诗一样的人生。
“莫言性格多乖张,只把诗词当故乡”。
本期编辑:汪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