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再战
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技术发展是雷达,无论是用于搜索(英国称之为预警)还是用于火炮瞄准。战争爆发时,主力舰上安装空中预警雷达(79型,随后是279型和281型)的计划已经相当进展。这些雷达都工作在长波长(导致波束定义不佳),最初它们需要在主桅上安装发射天线,在前桅上安装单独的接收天线。火炮雷达工作在较短的波长(50厘米),但波束仍然太宽,无法实现盲射;指挥仪仍需通过光学方式指向。这一系列的雷达包括282型(用于高射炮指挥仪,测距能力最差)、283型(用于弹幕指挥仪,由282型改进而来)、284型(用于主炮)和285型(用于高角度射击)。从1941年开始,厘米波雷达投入使用,最初用于高清晰度水面搜索:271型(“灯笼”),随后是273型和277型(带有可倾斜的抛物面天线,具备有限的高度探测能力)。火炮现代化意味着安装了厘米波的274型雷达。它提供了狭窄的非扫描波束,因此除了直接在线上的水花外,无法探测到其他水花。加拿大还专门开发了931型雷达用于探测水花,但它仅在战争结束时出现。282型和285型的厘米波后继型号分别是262型和275型,后者与Mk VI指挥仪配对使用。
雷达设备本身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们的数据必须进行关联,以向指挥官提供连贯的战术画面,这是战前绘图技术的延伸。到1945年,舰艇通常拥有多个雷达数据关联空间,如飞机指挥室、火炮指挥室和总绘图室。除了通过语音外,没有其他方式将它们整合在一起,雷达数据的整合成为战后使用计算机的一个重要主题。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任何大口径主力舰。德国人也拥有雷达,最初性能优于皇家海军,但他们从未发展出像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那样的绘图/态势感知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列舰最重要的两项技术发展是雷达和近距离防空炮。1943年10月4日拍摄的照片中,刚刚完成改装的“皇家君主”号展示了这两项技术。她的顶桅装有281型空中搜索雷达的天线(照片中不可见)。她的主桅顶部装有273型水面搜索雷达的“灯笼”天线。前桅高角度指挥仪上的“鱼骨”天线服务于285型火炮雷达。类似但更小的天线用于282型高射炮雷达和283型弹幕指挥雷达,但在此照片中并不明显可见。指挥仪顶部的横杆(位于指挥塔顶部)服务于284型主炮雷达。所有这些火控雷达基本上都是战前晚期的技术,工作在较长的波长(50厘米),因此波束较宽,无法在方位或高度上跟踪目标。273型雷达是新一代厘米波(10厘米)雷达的一部分。其短波长的优势在于雷达波束的垂直部分可以足够窄,以避免被海面反射干扰。到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已经装备了厘米波火控雷达,因此即使目标不可见,也能跟踪并攻击目标。这种能力被称为“盲射”。雷达本身是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独有的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数据通过AIO(最初是雷达绘图;美国对应的是战斗信息中心)进行整合。尽管战时盟军的雷达通常远优于德国雷达,但压倒性的优势在于整合雷达数据以生成可用的指挥画面(德国人主要将雷达用于火炮测距)。英国人在战前通过防空组织预见了防空整合,该组织基于专门位置的瞭望员。“皇家君主”号在带窗的罗盘平台上方展示了这样一个位置。战时对重型近距离防空炮的需求体现在她的两座超射炮塔顶部的四联装高射炮(覆盖帆布)和大量厄利孔炮上。皇家海军特别喜欢厄利孔炮,因为与高射炮不同,它不需要外部电源或控制。他们还开发了双联装动力厄利孔炮。
此外还有干扰器。皇家海军部署了FV1/91型干扰器以对抗德国火炮雷达。在“约克公爵”号与“沙恩霍斯特”号的早期交战中,她操作了干扰器,据信显著降低了德国舰艇的火炮精度。德国舰艇的精度在英国战列舰的主桅被击中后有所提高,击毁了干扰器。1943年德国部署导弹后,英国开发了650型和651型干扰器,安装在为诺曼底登陆轰炸部队准备的舰艇上。
丘吉尔的“凯瑟琳”行动似乎促成了对额外可能武器的研究,例如英国陆军采用的博福斯炮。此时采用的最奇特武器是UP(非旋转弹)火箭发射器。尚不清楚它与丘吉尔有多大关系,尽管在船员心中它与他的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博士有关。UP发射器的细节出现在“凯瑟琳”文件中关于快速防空升级的部分。UP发射器被设想为空军部线缆弹幕的海军版本,旨在保护机场免受低空轰炸机的攻击。发射器中的二十枚7英寸火箭每枚都携带一根电缆和一个降落伞。当火箭达到设定高度时,降落伞释放以悬挂电缆。电缆下端有一颗炸弹。十枚火箭齐射以快速形成一道屏障,低空飞行的飞机必须穿过。UP发射器安装在“巴勒姆”号、“纳尔逊”号、“乔治五世国王”号、“威尔士亲王”号和“胡德”号上。它似乎一直被视为权宜之计,因此随着高射炮的广泛可用,安装于1941年1月停止。该计划在完成前被放弃,可能是由于德国炮弹在“胡德”号上引发火箭储存火灾。
“威尔士亲王”号和“乔治五世国王”号完工时安装了UP,取代了计划的八联装高射炮。“乔治五世国王”号有四个UP安装(一个在“B”炮塔,两个在“Y”炮塔,一个在舰尾),这些在1941年12月的改装中被移除。当时“B”炮塔安装了计划的八联装高射炮,但“Y”炮塔安装了四联装(在最后一次战时改装中被八联装取代)。“威尔士亲王”号有三个UP(一个在“B”炮塔,两个在“Y”炮塔),在1941年8月的最后一次改装中全部被八联装高射炮取代。
与美国海军相比,英国战列舰在战争期间只安装了少量博福斯炮,现有的八联装和四联装高射炮被认为足够。计划“凯瑟琳”行动的人提议从陆军借用一些单管风冷博福斯炮作为快速升级。一门无动力的单管炮被安装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用于地中海护航,该舰沉没时仍在原位。英国开发了荷兰双联装稳定哈泽迈尔的版本,但用于驱逐舰,而非主力舰。1945年的计划设想在英国等效的“巴斯特”(后来称为STAAG [简易测距防空炮])安装在“先锋”号的“B”炮塔上。当时美国海军告诉皇家海军,他们偏爱的厄利孔炮对神风特攻队几乎无效。因此,美式博福斯炮出现在为太平洋战争现代化的“乔治五世国王”级舰艇上。在“乔治五世国王”级现代化之前,英国主力舰上增加的防空武器是高射炮和单联装及双联装厄利孔炮。
1943年11月,提出了为太平洋服役的所有四艘幸存的“乔治五世国王”级舰艇进行现代化的建议。由于部分计划设备短期内无法获得,两艘舰(“乔治五世国王”号和“豪”号)将进行部分现代化,两艘进行完全现代化。完全现代化包括为5.25英寸炮塔提供盲射能力,由新的Mk VI指挥仪和新型窄波束雷达(275型)及RPC提供。两座高射炮和两座美式四联装博福斯炮将安装在拆除弹射器后腾出的空间中的后部上层建筑上。现代化包括在293型天线下方的星鱼平台上安装新型277型水面搜索天线。修改281型空中搜索雷达将为前桅腾出空间安装293型目标指示雷达。舰桥绘图室将扩大,雷达数据将输入完整的AIO。主炮DCT配备了274型火控雷达。第一艘舰(“豪”号,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改装)未获得293型或新的Mk VI指挥仪。她在后部上层建筑上增加了两座八联装高射炮和两座四联装博福斯炮(后部上层建筑上的两座)。1945年9月,她进一步武装了七座四联装高射炮(两座在“B”炮塔后方的上甲板,两座在下层舰桥平台,两座在后甲板,一座在舰尾)和十八座单联装博福斯炮(“博芬”安装)。“乔治五世国王”号(1944年2月至7月改装)未获得新的Mk VI指挥仪,但获得了293型。她的四联装高射炮被计划的八联装取代,后部上层建筑上又安装了两座八联装高射炮和两座四联装博福斯炮。由于274型短缺,两艘舰在后部DCT上安装了改进的285型。“约克公爵”号(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改装)拥有293型和277型,但没有新的指挥仪。安装了六座四联装高射炮(两座在“B”炮塔后方,两座在“Y”炮塔前方,两座在“Y”炮塔后方的上甲板上),以及两座四联装博福斯炮和两座八联装高射炮在后部上层建筑上。只有“安森”号(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改装)拥有Mk VI指挥仪。除了后部上层建筑上的博福斯炮和高射炮外,她还拥有四座四联装高射炮(两座在“B”炮塔后方,两座在“Y”炮塔后方的后甲板上,后来移至舰桥翼以取代双联装20毫米炮)。所有舰艇都增加了厄利孔炮。她们非常重的防空炮组带来了巨大的人员成本,战争结束时和战后被削减。
### “凯瑟琳”行动
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温斯顿·丘吉尔重新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他立即提出了“凯瑟琳”行动(以凯瑟琳大帝命名):英国舰队应夺取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主要是为了鼓励瑞典人和芬兰人,甚至可能说服苏联人打破与希特勒的联盟。被迫对抗英国的德国人将不得不冒险出动自己的舰队。这是丘吉尔在一战期间参与的流产的波罗的海计划的现代版本。即使英国舰队——皇家海军的一小部分——在此过程中被摧毁,德国对英国使用公海的表面威胁也将被消除。德国人还将被剥夺瑞典铁矿石等必需品。为了在波罗的海生存,舰队需要更好的防空保护。
为了在短期内执行该计划,丘吉尔不得不依赖现有舰艇,最多进行轻微修改。他的预期舰队包括三艘战列舰“厌战”号、“勇敢”号和“马来亚”号,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号仍在以战时优先度较低的条件下重建。移除“马来亚”号和“厌战”号的跨甲板弹射器将为两座双联装4英寸炮腾出空间。高角度炮弹容量将从早期的每门炮200发增加到450发。对于“马来亚”号,还可能在拆除弹射器后腾出的空间上增加装甲,并在机库顶部安装两座高射炮。两艘舰都将为暴露人员提供防弹片保护。“马来亚”号将获得与另外两艘舰相同的发射长(5/10 crh)15英寸炮弹的能力,以简化弹药供应并增加2000码射程。此外,使用相同的炮弹,三艘舰可以集中火力。“马来亚”号的弹射器在行动前未移除,因为她需要它进行一般服务。尽管“马来亚”号未进行改装,但甲板装甲和防弹片保护已订购并交付马耳他,第二套交付德文波特。除了额外的防弹片保护和更大的4.5英寸弹药库空间外,未计划对“勇敢”号进行重大改装。“勇敢”号配备了特殊的除冰装置,但其他舰艇未进行任何改动。舰队中的所有舰艇都将配备飞行弹幕气球。1940年初,“巴勒姆”号取代了“马来亚”号。
1943年6月13日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展示了双联装4.5英寸BD炮座,这是20世纪30年代末现代化计划的关键部分。“B”炮塔顶部的遮蔽物是双联装动力操作的厄利孔炮。
战时最令人不快的意外之一可能是中口径防空炮火的无效性,皇家海军(以及其他海军)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不仅火控系统(HACS系统)表现不佳,炮弹的杀伤力也远低于预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中口径炮火缺乏威慑力。随着近炸引信的引入,炮弹的杀伤力显著提高,但除非炮弹能够接近目标——这需要更好的火控系统——否则近炸引信也无济于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10月,展示了“乔治五世国王”号在墨尔本港的5.25英寸炮座。
“凯瑟琳”行动中最奇特的计划改装之一是为舰艇配备Actaeon反鱼雷网。这一计划在1939年11月被讨论。与一战时期的反鱼雷网不同,这些网旨在保护移动中的舰艇。这些网最初是为了保护商船(在二战中成功使用),商船可以以最高15节的速度拖曳它们。班轮“百慕大女王”号被用于更高速度的测试,最高达19节。“勇敢”号本应成为“凯瑟琳”行动的 原型,安装了特殊的吊杆以操作这些网。为海军部建造了一个提议安装的模型。它被批评为在航行中难以安装和拆卸。如果它被炸弹或炮弹损坏,它将拖在船尾并缠住螺旋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鱼雷网的主要问题)。即便如此,“勇敢”号本应在1939年11月24日之前完成改装(但未实现)。
防弹舰艇
与“凯瑟琳”行动并行的是丘吉尔的想法,即让一些老式战列舰具备防弹能力。1939年10月,他提议重建“皇家君主”级舰艇。丘吉尔写道,DNC告诉他,如果在舰艇外侧增加两层空舱,将舰宽增加到140英尺,舰艇将在水中浮起9英尺,从而可以使用仅26英尺深的波罗的海航道,且不受任何火炮控制。内层 空舱 将在船坞中安装,外层在港口中安装。丘吉尔写道,在最小吃水时,速度可能降至16节,但在正常吃水时,速度将为13或14节。舰艇的上甲板将得到加强,以提供“卓越”的防空保护。至少应准备两艘“皇家君主”级战列舰,但三艘更好。
到1939年11月,丘吉尔希望两艘“皇家君主”级和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进行改装。双层 bulges 的想法似乎被放弃了,但装甲计划更加具体:在 炮廓 区域的 艏楼 或上甲板上覆盖160磅(4英寸)装甲,后甲板上覆盖80磅装甲。包括1200吨的新 凸起 和已经批准的装甲,总增加量约为4200吨(包括1470吨在 forecastle 甲板上,560吨在上甲板上)。新的 bulges 必须至少增加这么多浮力(DNC的战列舰设计师H S Pengelly希望更多,约4500吨,以减少深吃水)。
为德文波特起草了改装“皇家君主”号的指示。旧的 凸起 将保留在舰艇的中央部分,但在前后部分被切割以腾出空间安装新的 凸起。对旧 凸起 的改动越少越好,以便更容易为新 凸起 设计框架。新 凸起 中的 隔舱 将与旧 凸起 中的 错列 相对。船厂将在整个 露天甲板上铺设3½英寸装甲,覆盖在木质甲板上。这种保护最初旨在防止6000英尺高空投下的1000磅穿甲炸弹;结果发现,最初想要的4英寸装甲可以从7000英尺高度防住,而3¾英寸可以从6000英尺高度防住。边缘可以火焰切割而不是机械加工;板材之间的紧密接合不是必需的。烟囱将保持现状。DNC估计,舰艇在改装期间将在干船坞中停留约八个月。如果没有额外的加固,新装甲将重1935吨。新的 凸起,以25英尺的 间隔 建造,将再重990吨。根据“拉米利斯”号的数据,在改装前,轻载排水量为29,420吨。新装甲和 凸起 将共重3242吨,因此新的轻载排水量将为32,662吨,新的深载排水量将为37,077吨,包括填充上层 凸起。1939年11月8日,DNC下令停止所有“皇家君主”级舰艇的工作,并将精力转移到“伊丽莎白女王”级上。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号,DNC基于在 炮廓 区域铺设3英寸装甲的方案进行工作。这种装甲将增加1600吨,增加吃水1英尺3英寸,并在深载条件下减少 干舷 高度0.63英尺。舰艇将损失四分之一节的速度。将额外装甲限制在弹药库区域将减少至920吨(增加9英寸吃水,干舷 高度减少至0.4英尺,损失八分之一节速度)。DNC补充说,已经计划的额外弹药库和机械空间装甲已经交付,部分已经安装,但该舰的优先级较低。
更糟糕的是,英国工业最初无法同时满足新舰和改装舰对近距离防空炮的需求。或许“凯瑟琳”行动流产的主要遗产是对替代武器的调查。其成果显然包括1941年1月在“乔治五世国王”号上展示的UP火箭发射器。
1940年10月27日,“胡德”号上展示了UP火箭发射器(遮蔽)和传统的双联装4英寸高角度炮。在与“俾斯麦”号的战斗中,“胡德”号被击中,击中了UP发射器的备用弹药存放区域。由此引发的大火(虽然未造成严重后果)使海军部确信,UP火箭发射器对装备它的舰艇的危险性大于对任何攻击者的危险性,因此该计划被取消。用于防御低空攻击者的投射线缆装置的想法得以保留,但这些装置仅部署在辅助舰艇上——包括许多LST(登陆舰)。
丘吉尔的想法出现在1940年2月22/26日的海军部会议记录中:两艘“皇家君主”级战列舰应加强甲板装甲,使其能够在敌方岸基飞机的攻击范围内作战——即不受航母起降限制的飞机。丘吉尔声称,花费100万英镑,这些舰艇可以在1941年秋季前完成改装,从而在当前战争中发挥作用。同时,他提议用类似的资金为“苏尔特元帅”号炮塔建造新的船体和发动机,这可能是近岸作战所需的。没有提供相关的设计说明(海军部在1940年5月批准了该炮塔的设计说明)。船坞主管指出,即使没有支撑梁且不对上甲板开口进行任何保护,准备工作也需要两个月,舰艇将在三个月后进入干船坞(提前六天通知出坞),并在十个月后离开船坞,整个工程将在一年内完成。
该项目在丘吉尔成为首相后仍然存在。随着“闪电战”的持续,1940年8月22日,他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展望恢复正常建造:“我希望现在有机会修复对’皇家君主’级舰艇改装的灾难性忽视,将其改装为具有重型甲板装甲的适当装甲和 bulged 的炮击舰艇。这些舰艇明年将用于对意大利的攻击。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些舰艇。它们当然应该优先于恢复战列舰的建造。”9月初,海军参谋部指出,从作战角度来看,这个为期18个月的项目是不可行的。
丘吉尔的继任者作为第一海军大臣,在1940年10月“决心”号在达喀尔被鱼雷击中后重新启动了该项目。他没有提到将主力舰停泊18个月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绝对不可能性,而是辩称该项目被搁置只是因为舰队过于紧张。战争初期的损坏使“纳尔逊”号和“巴勒姆”号瘫痪了几个月。修理/改装设施和劳动力已经紧张,以应对在挪威和法国沿海遭受的损坏。
在“皇家君主”级中,“复仇”号需要护航远洋船队,“拉米利斯”号用于护航部队,“决心”号用于奥兰和其他地方的行动。既然“决心”号无论如何都需要修理,她可以接受全面改装。1940年10月8日的 海军建设局局长 会议批准了该项目,图纸被送往朴茨茅斯,直到1940年11月,包括包含新 bulges 的修订船体图。然而,作战问题仍然存在:18个月在战时是非常长的时间。1940年12月27日,海军建设局局长 决定“决心”号的工作仅限于修复损坏和最小改动。然而,两座前炮塔应“抬高”至30°最大仰角。但次年在美国修理时,甚至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胡德”号的沉没
1941年5月24日,距离日德兰海战近25年后,皇家海军最大的舰艇——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被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击沉。这次沉没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尽管“胡德”号被描述为战列巡洋舰,但她实际上是新型快速战列舰的第一艘。她的防护比“伊丽莎白女王”级和“皇家君主”级更好。迫切需要找出击沉她的原因,因为迫切需要应对“俾斯麦”号的姊妹舰“提尔皮茨”号的威胁。
DNC对“俾斯麦”号的防护有一些了解,因为一名幸存者在被救起时紧握着一本损害控制手册。1941年6月12日,他的下属W G Sanders提交了一份关于如何最好地攻击“俾斯麦”号的初步报告。水下攻击将是最经济的方法,因为很明显该舰的水下防护系统较为简单。她的机械空间比英国最近的设计更大,因此她特别容易受到非接触鱼雷(英国有磁性引信鱼雷)等水下武器的攻击。
**胡德号沉没时的状态**,展示了其最近安装的雷达(主桅顶部的281 B型雷达[用于空中预警/空中搜索]和前桅顶部的284型雷达,前桅已被改装为DCT,以便与计划在下一次改装中安装的AFCT配合使用)。图中显示了三座高射指挥仪中的两座,一座位于前桅后腿的侧面,另一座位于后部上层建筑的顶部中心线上,其后还有一座高射炮指挥仪(前桅顶部也有高射炮指挥仪)。此时,胡德号的所有5.5英寸火炮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七座双联4英寸高射炮:两座位于后烟囱侧面,两座位于主桅侧面,两座位于后部上层建筑侧面,还有一座位于中心线上,覆盖“X”炮塔。胡德号装备了三座八联装高射炮,并保留了四座四联装0.5英寸机枪(位于指挥塔后方和后部上层建筑侧面)。最引人注目的新武器是五座火箭(非旋转弹,或UP)发射器:一座位于“B”炮塔顶部,前烟囱两侧各一座,两座4英寸炮座之间各一座。图中显示了沿船侧突出的消磁电缆,但未显示后部的水上鱼雷发射管。
手册显示,俾斯麦号的装甲布局与英国基于二十年测试的实践相反。其布局类似于一战时期的战列舰,尽管甲板更厚,但浅层装甲带无法阻止俯冲炮弹。与其试图击穿侧装甲(倾斜通常会使这变得困难),舰船应寻求在约20,000码的距离上进行俯冲打击。英国测试表明,将甲板置于装甲带上方(以应对俯冲炮弹)并在舰船内部抬高甲板(和装甲带顶部)以应对炸弹的重要性。这两者都在军事特性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德国人未能理解这两个问题,因此在攻击其舰船时,英国人应使用他们牺牲火力和速度来应对的方法:俯冲炮击和半穿甲SAP(而非穿甲AP)炸弹。
在20,000码的距离上,即使以90°倾斜(最有利的情况),乔治五世号也无法击穿俾斯麦号的装甲带,但炮弹可以穿透其较薄的上部装甲带和上部装甲甲板。即使炮弹未能穿透下方的主装甲甲板,它们也会在其附近爆炸,对水密性、浮力储备、火炮支撑、通信等造成严重损害。此外,这艘宽大舰船的甲板将占据目标的大部分。在20,000码和50-70°倾斜的情况下,俾斯麦号将呈现出几乎是乔治五世号两倍的易受攻击目标体积,因此将遭受最大的损害。纳尔逊号将呈现出稍大的易受攻击体积,但其火力也更重。桑德斯补充说,如果炮弹无法击穿装甲带,那么将其设计为AP炮弹所固有的许多牺牲就被浪费了;最好采用相当于SAP炸弹的炮弹。
对于较老的舰船,前景更加黯淡。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装甲布局与俾斯麦号大致相同,但甲板更薄,装甲带相当:“坦率地说,伊丽莎白女王级不应被视为适合与俾斯麦号交战,但如果必须行动,则应尽可能进行侧舷交战,因为即使是伊丽莎白女王级中最好的舰船,其弹药库的防护效果也不理想。除了这一建议外,伊丽莎白女王级只能通过更精准的射击和更高的射速以及可能更优质的炮弹来击败俾斯麦号。”皇家君主级甚至不值得讨论。
这几乎不可能是日德兰海战后得出的结论,当时被击沉的舰船明显劣于战列舰。胡德号沉没后,海军部立即向所有旗舰指挥官和战列舰舰长发送了紧急信号,给出了此类舰船可以交战的安全距离。现代舰船(纳尔逊级和乔治五世级)应在约20,000码或更远的距离上交战,但纳尔逊级应避免接近正对或正尾的方位,因为之前提到的“防护伞”问题。现代化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应在13,000-15,000码的侧舷方位上交战(很快修正为18,000-22,000码),因为它们的甲板装甲较差。战列巡洋舰可以在接近正对或正尾的方位上交战,但应尽可能得到支援。
海军建设局局长于8月11日召开了一次经验总结会议。他认为乔治五世级的设计是合理的,纳尔逊级也基本如此(除了需要完成前部甲板装甲)。所有伊丽莎白女王级舰船都缺乏弹药库前后应对俯冲炮弹的防护伞。马来亚号正在美国维修;海军建设局局长希望紧急发送信号,在前部中层甲板上安装4英寸装甲,后部中层甲板上安装3英寸NC或(美国)特制钢(STS)装甲,并在全船宽度上安装横向装甲,即使需要以补丁方式安装。如果无法做到,应将装甲板安装在木板上,以便舰船返回英国后安装。巴勒姆号应安装相同的装甲,但还需在机舱中层甲板上安装防护伞和160磅NC装甲(约150吨)。重建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舰船都需要在前部下层甲板上安装140磅NC装甲(70吨),后部中层甲板上安装120磅装甲(如马来亚号,约100吨),以及端部舱壁。
声望号最薄弱的部位是从后部穿过辅助锅炉房甲板进入前部4.5英寸弹药库的可能弹道。炮弹进入该处后会遇到一段8英尺长的150磅NC装甲,其后是60磅NC装甲。然而,考虑到舰船的垂直防护较弱,增加甲板装甲是否值得尚不确定。后来的会议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副海军建设局局长表示,该舰最好在约18,000码和45°方位上与德国沙恩霍斯特级交战。从未重建的却敌号应在前部下层甲板上扩展150磅NC防护伞(66吨),在前部锅炉房上安装防护伞(100磅NC覆盖现有的40磅HT装甲,延伸至船侧,50吨),并在后部下层甲板上扩展防护(120磅,60吨)。
所需措施部分取决于胡德号发生了什么。胡德号的设计专门是为了避免日德兰海战中战列巡洋舰的命运,而且她显然没有采取自杀式的弹药库操作。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在25,000码的距离上开火,舰船在约16,500码的距离上沉没,这大致是皇家海军偏爱的交战距离。高速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为28节)符合英国公认的战术。当俾斯麦号击沉胡德号时,胡德号的倾斜角度约为50°。这一角度使胡德号的侧装甲比俾斯麦号以接近90°的方位平行航行时更为有效。胡德号的“A”炮塔在沉没前刚刚开火,并从“X”或“Y”炮塔发射了一轮齐射。俾斯麦号的炮术官后来写道,胡德号的几轮齐射都未命中,但她正在调整射程时被摧毁。
胡德号以梯队队形率领威尔士亲王号,两舰相距约4链(800码),方位相差45°。胡德号首先开火,随后是俾斯麦号,然后是威尔士亲王号,所有开火均在一分钟内完成。俾斯麦号的第三轮齐射覆盖了胡德号,一发炮弹显然在主桅前的左舷爆炸。这次命中靠近“P.2”(从前数第二个)双联4英寸炮座。它引发了火药火灾,显然是由于堆放在炮附近的备用弹药。诺福克号的舰长(曾担任胡德号的指挥官[执行官])认为他看到了与这次命中相关的明亮闪光,并将其与水上鱼雷发射管联系起来,但调查委员会认为,如果鱼雷弹头爆炸,其破坏效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火药火灾显然向前后蔓延,并在舰船被摧毁时逐渐熄灭。普遍认为火灾已蔓延至高射炮和UP弹药。
下一轮齐射显然刚刚越过,第五发命中并摧毁了舰船。只有一名观察者看到了命中,他表示命中位置与前一次相同(主桅附近)。爆炸的中心位于主桅底部,升至估计500-600英尺的高度。大量残骸被抛向空中。诺福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的观察者都同意这次爆炸的位置。由于两舰与胡德号的方位不同,调查委员会认为这一位置是准确的。爆炸几乎没有声音。舰船随后被火焰和烟雾包围,向左舷倾斜,并在两分钟内沉没。威尔士亲王号改变航向以避免残骸。胡德号的船首以陡峭的角度从水中伸出,然后滑回水中。当胡德号向左舷倾斜时,威尔士亲王号的特里中校认为他可以看到“X”炮塔和主桅之间的底部装甲板被炸开;当舰船倾斜时,他可以看到右舷的框架。一名在封闭罗经平台上的幸存者表示,爆炸的冲击力将所有人都震倒在地,残骸开始落下。关于舰船后部底部被炸开的说法使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胡德号是由于后部弹药库爆炸而沉没的。
调查委员会完全依赖目击者的证词,因为没有拍摄照片。有人指出,在日德兰海战损失调查期间,很明显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决定为所有舰船配备战斗摄影师,他们没有其他职责。这一教训显然被遗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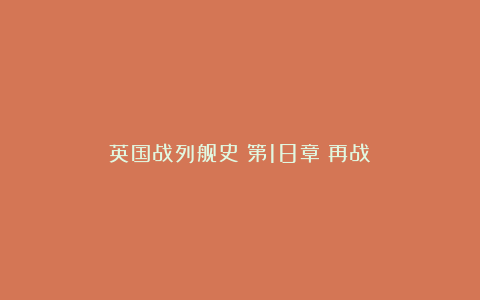
没有弹药库直接位于主桅底部附近命中位置的观察位置下方。最近的是位于约65英尺后的4英寸高射炮弹药库。该弹药库的爆炸可以通过后机舱向观察到的爆炸位置排放。委员会指出,该弹药库的爆炸几乎肯定会引爆相邻的15英寸弹药库。
委员会检查了舰船的骨架模型,可以追踪炮弹的可能路径。模型清楚地表明,俾斯麦号第五轮齐射的炮弹如果幸运且具有足够的延迟,可以到达后部弹药库。如果炮弹击中主桅附近的某个位置,延迟时间必须非常长才能使炮弹到达前部4英寸弹药库的前舱壁。更幸运的炮弹如果击中更靠后的位置,可能会在4英寸弹药库群中爆炸。这足以导致后部的15英寸弹药库爆炸,摧毁舰船。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舰船可能是由于一枚或多枚15英寸炮弹直接穿透其防护而被击沉的。
DNC指出,前部的4英寸弹药库仅包含407发定装弹。他发现很难将主桅底部的大爆炸与弹药库爆炸联系起来,弹药库爆炸本身应该是可见的。此外,后部的4英寸弹药库群有许多舱口和通道,爆炸会通过这些地方排放——并且是可见的。火焰应出现在上层建筑的后端和“X”炮塔前方。如果15英寸火药库爆炸,产生的压力将非常大,以至于上方结构会解体,火焰应出现在“X”和“Y”炮塔周围。DNC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次爆炸的火焰会通过后机舱排放到如此靠前的位置。4英寸弹药库的后舱壁距离主桅中心约115英尺,“Y”弹药库的后舱壁距离主桅中心180英尺。DNC发现很难将主桅底部的爆炸与如此远距离的大规模爆炸联系起来。
然而,在爆炸观察到的位置附近确实有大量爆炸物,主桅侧面的上层甲板上储存了约4000磅TNT。由于大量火药快速燃烧和TNT快速燃烧的火焰之间存在可观察到的差异,DNC希望熟悉两者的观察者能够发表意见。他的观点是,上层甲板上的爆炸物靠近水上鱼雷发射管中的鱼雷。尽管有防护,如果足够多的TNT在足够近的距离爆炸,会引爆鱼雷弹头。由此产生的爆炸将正好出现在观察到的位置。鱼雷弹头在密闭空间中的爆炸将是毁灭性的。它们可能会折断舰船的龙骨。
然而,许多针对鱼雷的测试表明,一枚15英寸炮弹在胡德号鱼雷发射管外爆炸(如胡德号的防护罩)不会引爆鱼雷。观察者是否准确记录了爆炸位置也不清楚,因为他们都处于舰船的某个角度。威尔士亲王号的特里中校拥有良好的视野,他认为爆炸发生在主桅和“X”炮塔之间,这将更接近弹药库。DNC的反对意见被海军建设局局长驳回。然而,前部的鱼雷发射管从声望号和却敌号上移除。
CNS不愿简单地拒绝DNC的分析。他发现DNC关于15英寸弹药库爆炸会直接向上的评论无法反驳。为什么它会沿着机舱向前排放?威尔士亲王号的利奇舰长表示,爆炸发生时,胡德号的“X”和“Y”炮塔仍然完好无损。在同一炮术站的特里中校表示,当烟雾散去时,胡德号仍然完好无损,尽管倾斜且尾部下沉。VCNS理解,如果弹药库爆炸,尾部将完全被摧毁。因此,他召集了第二次调查委员会,由胡德号前舰长韦克-沃克少将担任主席。一名造船师和一名爆炸专家担任顾问。分析包括对舰船在不同位置可能断裂的弯矩和剪切力的估计,以及各弹药库中火药的含量。
第二次委员会支持第一次委员会的结论,即致命命中发生在4英寸或15英寸弹药库内或附近,最有可能是4英寸弹药库。尽管DNC的鱼雷弹头建议不能被排除,但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一枚或多枚鱼雷弹头爆炸。此外,没有证据表明鱼雷弹头爆炸会如此毁灭性,以至于导致舰船立即沉没。在船甲板上看到的大火不可能导致舰船沉没(正如之前的委员会已经得出的结论)。爆炸为何似乎在特定位置排放的谜题仍未解决。
DNC指出,如果4英寸弹药库的爆炸确实摧毁了舰船,那么之前关于QF弹药库比袋装弹药库更安全的假设将不再成立。甲板间的水上鱼雷发射管是不安全的;鱼雷应存放在爆炸不会严重损害舰船的位置。船甲板上的大火(即使不是致命的)推翻了之前关于备用弹药火灾不会轻易从储物柜蔓延到储物柜的假设;显然发生了这种情况。DNC认为问题可能是下层甲板上的UP弹药火灾。尽管报告没有明确谴责UP炮座不安全,但其安装被停止。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解释了为什么海军建设局局长对防护伞和中部装甲产生了兴趣。装甲设计用于应对来自侧舷的炮火。在这种情况下,甲板装甲可以根据其下方的空间进行评估,例如锅炉房甲板装甲下方的锅炉。胡德号几乎被正面击中,炮弹可能穿过锅炉房上方的甲板。锅炉房甲板装甲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舰船可以失去一些锅炉并继续航行。胡德号被赋予了额外的内部装甲(防破片保护),以容纳任何由炮弹穿透装甲后内部爆炸产生的碎片(“破片”)。其效果取决于炮弹被触发后行进的距离。击中足够靠后甲板的炮弹(大概在主桅附近)不会立即爆炸。它可能很容易进入4英寸弹药库后爆炸。这足以引爆4英寸弹药库,产生的气体会向前进入锅炉和机舱,向后进入“X”弹药库。“X”弹药库中的火药火灾足以摧毁舰船。炮弹穿过锅炉房后直接进入“X”弹药库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它会遵循更陡峭的弹道,并可能被锅炉房内部结构触发。胡德号沉没后订购的防护伞和其他补充装甲旨在使炮弹在远离弹药库的地方爆炸,特别是在正面交战中,并容纳其产生的破片。
胡德号并未进行重建,但在1940年进行了改装,大幅增强了防空火力,代价是拆除了其单用途的5.5英寸火炮。新的防空火力包括总共七座双联4英寸火炮、第三座八联装’呯呯’高射炮(pom-pom)以及五座UP(非旋转弹)发射器,其中包括“B”炮塔顶部显眼的一座。此外,前桅顶部的指挥仪/测距仪被改装为DCT(指挥与观测[火控]位置),以便与计划安装的新AFCT(先进火控台)配合使用。新的AFCT将取代现有的德雷尔火控台和其他仪器,安装在原有的传输站中。这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新的火控台(计算机)需要在现场组装,而不是简单地吊装到位。图中展示了1940年10月9日胡德号在斯卡帕湾的状态。
1941年5月22日,胡德号在前往对抗俾斯麦号的途中。天气相对较好;在更汹涌的海浪中,胡德号被认为相当潮湿。DNC后来评论说,平静的天气极大地帮助了其敌人俾斯麦号,这是一艘非常坚固的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会迅速摇摆。战斗中的一个主要讽刺是,直到英国人捕获了德国船的损害控制手册后,他们才清楚地意识到,两艘船都容易受到俯冲炮火的攻击。俾斯麦号拥有一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类型的保护系统,其装甲甲板与带的下边缘相连,并且重要的管道和电线布置在其上方。这种装甲本可以保护她免受弹药库爆炸的影响,但不能防止被击毁。哪艘船先被击中可能非常关键。
鱼雷攻击:皇家橡树号和巴勒姆号
皇家橡树号和巴勒姆号都被U型潜艇的鱼雷齐射击沉,推测使用了类似的引信和弹头,因此这两个案例可以进行比较。皇家橡树号是皇家主权级中最好的,因此自然有人质疑她的损失是否显示了该级别的一些基本缺陷。她于1939年10月14日在斯卡帕湾被鱼雷击中并沉没。第一次击中,右舷前部,被解释为内部爆炸,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阻塞船已经使斯卡帕免受潜艇攻击。这次击中几乎没有效果。大约十到十二分钟后,船又被三枚鱼雷连续击中。最前的一枚靠近“A”炮塔,第二枚在烟囱旁边,第三枚在主桅杆旁边。船立即开始向右舷倾斜,悬挂或缓慢倾斜约45°,然后翻转,使其底部在八分钟内朝上。然后她慢慢下沉,没有前后倾斜。没有弹药库爆炸。由于一切发生得太快,伤亡惨重;没有放下救生艇,切割器已被收起以清理防空火力弧,因为空袭似乎是主要威胁。
在侧舷保护系统中,空的凸起部分位于船的双底之外,形成了一层水层。其内侧是一个油箱,然后是鱼雷舱壁,接着是一个内部油箱,然后要么是一个锅炉房前的空气空间,要么是一个没有空气空间的翼机房。水保护舱室是满的,因此理论上船的侧舷保护系统是尽可能有效的。燃油舱室几乎满了。由于没有预料到水下攻击,侧舷窗打开通风,带有遮光通风口以保持黑暗条件。水密门通常是关闭和夹紧的,除了为正常港口工作留下的一些门。
分析显示,三个几乎同时的击中使凸起舱室进水,使船倾斜得如此之陡,以至于上甲板和主甲板下的舷窗都浸入水中,使右舷侧进入更多的水,直到甲板开口被淹没。这种进水的临界角度远小于45°。派去分析损失的海军建造师得出结论,船本可以在第二次击中中幸存下来,因为它未能引爆“A”弹药库。他认为其他两次击中致命,因为它们导致了船无法恢复的进水。然而,调查委员会报告说,从第二次爆炸的那一刻起,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拯救船,也不可能广播弃船命令,因为灯光熄灭,电力失效。
第三次击中是在锅炉房旁边。它使内侧燃油箱(鱼雷舱壁内侧)坍塌,导致烟囱外壳处可见闪光。然而,没有证据表明鱼雷舱壁本身被击穿。第四次击中可能是在右舷翼机房。它击穿了那里的鱼雷舱壁,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油箱是满的。它产生了细小的油雾,蒸发并点燃,通过机舱舱口排出。它烧伤了在餐厅的海军陆战队员。似乎这是最严重的爆炸,可能还突破了中心线机舱舱壁。
船在第一次爆炸后二十五分钟和第二次爆炸后十三分钟沉没。委员会认为关闭舷窗和死灯不会拯救船,尽管这会减慢她的下沉速度,从而可能让更多的人逃生。回顾起来,关键因素可能是机舱内的纵向舱壁,使得翼舱室可以迅速进水,不仅造成突然的倾斜,还产生了相当大的动量。战争损害的官方总结补充说,这一事件强调了船只需要保持水密性,直到深水线以上约8英尺。
HMS 决心号的经验证实,一枚鱼雷不会致命。她于1940年9月25日在达喀尔附近的前锅炉房旁边被击中。凸起结构的全深度在50英尺的长度上被破坏;凸起舱室在80英尺的长度上进水。前锅炉房和其他一些舱室缓慢进水,最初她倾斜12°(通过转移油和便携设备纠正)。主炮保持完好,但受损侧的副炮被鱼雷爆炸产生的水柱损坏。强制润滑在4½小时后失效,暂时使船无法移动。主要教训是二次进水大大增加了鱼雷的效果。对马来亚号的类似击中(1941年3月20日)在前锅炉房前舱壁后方仅破坏了35英尺的凸起并进水100英尺的凸起,但造成的倾斜较小(7°),并且修复得更快(十三周而不是六个月,都在美国)。
HMS巴勒姆号于1941年11月25日在地中海的一次战斗部队扫荡中被三到四枚鱼雷击中。鱼雷击中在烟囱和后炮塔之间,使船迅速倾斜。击中后四分钟,船倾覆,可能是在“X”和“Y”弹药库之间发生了严重爆炸。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鱼雷击穿了船的侧面,导致如此迅速的进水,以至于她迅速倾斜到40°,稍微停顿,然后完全翻转。委员会无法确定爆炸的原因,但推测是由于左舷4英寸弹药库引发的火灾,蔓延到相邻的15英寸弹药库。船爆炸时已经倾覆。附近HMS 勇士号的值班军官表示,所有观察者都同意有三枚鱼雷爆炸,一枚然后两枚快速连续,都在烟囱和主桅杆之间的中部。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大爆炸是6英寸弹药库而不是“A”或“B”,因为爆炸中心在桥后方;军官认为它在“X”和“Y”弹药库前方。巴勒姆号的ADO/PCO感觉到三枚鱼雷爆炸,然后第四枚在主桅杆旁边。
HMS威尔士亲王号的损失
如果HMS胡德号的损失突显了防火保护的可能问题,那么威尔士亲王号的损失则令人担忧,因为她被认为对鱼雷有足够的保护。威尔士亲王号在航母皇家方舟号之后不久沉没。两艘船都采用了被认为足以承受750磅装药的保护;据信,击沉威尔士亲王号的轰炸机发射的日本鱼雷携带的装药要小得多。官方报告将水下保护称为保护船的“水带”,这可能会与船的装甲带混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被任命来考虑鱼雷保护在每种情况下是否足够。
有三次独立的攻击。在第一波九名攻击者投下鱼雷后,船转向避开鱼雷轨迹,避开了两枚鱼雷,但被第三枚击中,位于左舷后部“P.4”5.25英寸炮座旁边,于1144.22。这次爆炸致命地损坏了船。它还严重破坏了内部通信,使损害控制变得困难。尽管鱼雷击中后部,但由于涉及左舷外侧螺旋桨轴,它直接涉及“B”机舱,该机舱驱动该轴。与其他三个机舱一样,“B”机舱与其自己的锅炉房(两个锅炉)和其自己的行动机械房(一个涡轮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发电机)房在机舱外侧相关联。每个机舱都有自己的动力控制室,可以监控和控制所有四个机舱。它提供了在机舱必须撤离(例如,在气体攻击的情况下)时的备用。机舱和锅炉房并排配对,因此“A”机舱与“B”机舱并排,“A”锅炉房与“B”锅炉房并排;锅炉在发动机前方。没有足够的长度将动力机械舱分成两个单元,相距足够远,以至于没有一次水下击中可以击毁船。威尔士亲王号的可怕意外是,螺旋桨轴可以将损坏传递到整个动力机械舱。不清楚是否可以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这种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带来了新的水下威胁,特别是磁性水雷。1940年,英国捕获了德国的水雷后,他们能够通过消磁来保护船只,最初使用的是外部电缆,例如在胡德号上可见的那种。后来有人推测消磁可以用来保护船只免受磁性引信鱼雷的攻击,并且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努力。所有在战争期间使用被动磁性鱼雷的海军都尴尬地发现它们不可靠,因为地球的磁场因地而异。德国人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让鱼雷产生一个磁场,目标船只会干扰这个磁场。消磁对这种引信不会有太大作用,这种引信现在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中是标准的。
1941年4月,胡德号展示了其改装后的DCT(指挥仪)顶部的284型火控雷达。
对沉船的检查显示,在左舷外侧轴从船体伸出的位置有一个大洞(约4 x 6米)。由于爆炸主要发生在船体下方,导致船体发生鞭状振动。这种振动可以将较小的船只直接折断成两半(现代鱼雷通常以这种方式击沉船只),但在这艘巨大的战列舰上,它打开了接缝,导致后续的渐进性进水。最近一份基于沉船检查的报告将洞的巨大尺寸和左舷外侧轴的变形归因于爆炸产生的竞争性力量。爆炸向上推挤船尾,但“X”炮塔及其基座的重量抵抗了这种力量。螺旋桨轴周围的整个结构都发生了变形,轴旋转的管道也受损;轴本身也发生了变形。由于外侧轴受损,它在高速旋转时发生晃动。最终,轴的后部、螺旋桨以及A型支架的残余部分从船体上撕裂,部分残骸击中了左舷内侧螺旋桨。
爆炸摧毁了最近的舱壁,轴管穿过该舱壁,并严重损坏了封闭轴通道后端的舱壁。尽管轴已经变形,但它继续旋转,进一步打开了其他舱壁,导致整个轴通道进水,尽管沿通道布置了水密舱壁。虽然一些舱壁基本保持完好,但螺旋桨轴周围的密封装置被毁坏,水得以通过。在击中后的18分钟内,“B”机舱进水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必须撤离。机舱内的人员并未意识到轴已经严重受损。涡轮机仍在运行,因为船只仍需要尽可能保持速度以躲避进一步的攻击。然而,螺旋桨已被击中产生的残骸摧毁,因此该轴实际上已经失效。内侧螺旋桨(由“Y”机舱驱动)叶片的损坏导致“Y”机舱内发出撞击声,进而导致机舱内的人员关闭了它。此外,“Y”锅炉房因燃油吸入管损坏而失效。随着左舷两侧的轴都失效,船只速度降至15节,并开始缓慢向左舷转向。船只实际上已经失控。
关键的是,进水的轴通道位于船的鱼雷保护系统内部。水从轴通道涌入,淹没了“Y”行动机械房,然后是柴油发电机房,进而淹没了“B”机舱。冲击和进水导致船上的八台发电机中有五台失效。电力环网的后部(但非前部)也失效了。后部的两组5.25英寸炮塔电力中断。“P.1”炮塔在旋转时卡住,“P.2”炮塔电力失效。船只迅速向左舷倾斜11.5°,船尾下沉,左舷后甲板在1220时被水淹没。
第二次攻击到来时,船只正在进行反向注水以恢复平衡。两个由三架飞机组成的小组从右舷攻击威尔士亲王号,另外三架攻击其伴舰反击号。此时,威尔士亲王号由于之前的损伤已无法机动,因此被六枚鱼雷中的三枚击中。其中一枚鱼雷击中了“S.4”炮塔附近的位置,正好与第一次鱼雷击中的另一侧位置相对。另一枚击中了前部防浪板附近,第二枚击中了罗经平台附近。此时,水下保护系统的内部空隙已被注水以纠正之前的倾斜,舰长利奇不得不决定注满外部空隙。他意识到这样做会显著降低水下保护系统的有效性,但这是恢复船只平衡的唯一方法。
幸存者可能误判了后部击中的位置,因为鱼雷接近时船只正在转向(就像致命左舷击中时船只正在转向一样)。这次击中造成了一个更大的洞(4 x 11米),并卡住了右舷外侧轴(潜水员发现轴弯曲得非常严重,螺旋桨被楔在内侧轴上)。由于第一次击中导致船只严重进水,这次击中位置更高。除了鱼雷损伤外,沉船还显示船板因近失弹(或鱼雷爆炸的冲击)而深深凹陷,这可能导致水下保护系统的外侧部分进水。
到1230时,只有“X”机舱(右舷内侧轴)仍在工作。船只明显下沉。剩余电力足以维持部分防空炮和三座5.25英寸炮塔(“S.1”、“S.2”、“P.1”)的运行,以抵抗九架水平轰炸机的最后攻击。它们直接击中了弹射器甲板,并有几次近失弹;装甲甲板未被击穿。然而,船体侧面的碎片损伤导致进一步进水,进一步降低了船只的稳定性。水通过变形的舷窗流入。1250时,威尔士亲王号向新加坡发出无线电请求拖船,这意味着至少船上仍有人认为船只可以获救。1310时,船员被命令充气救生筏,船只大约在1320时沉没。
1940年8月21日,胡德号在斯卡帕湾展示了两座双联装4英寸炮。此时,雷达尚未安装在前桅顶部的DCT(指挥仪)上。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后部的鱼雷发射管口似乎可以操作;前部的一对似乎已被焊接封闭。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沉没是对英国防空理论和火力的考验。威尔士亲王号似乎击落了第一波攻击中的两架飞机和第二波中的两架,但每次都是在它们投下鱼雷之后。舰上的炮术军官报告称,一旦电力中断,5.25英寸炮塔无法手动调整以应对由于严重倾斜(来自第一次攻击)带来的巨大角度问题。最后开火的是“S.1”和“S.2”炮塔。
威尔士亲王号遵循了在地中海地区发展出的战术,即通过可见的弹幕来威慑鱼雷轰炸机。然而,日本飞行员直接穿过了弹幕,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经历过类似的防空弹幕。砰砰炮(pom-poms)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它们没有曳光弹:攻击者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开火。相反,厄利孔(Oerlikons)和后甲板上的一门博福斯(Bofors)炮被认为非常有效,因为它们即使在船只大部分电力失效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开火,并且它们的曳光弹确实给攻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炮术军官认为,一门带有曳光弹的博福斯炮在本地控制下开火,比没有曳光弹的八联装砰砰炮更有价值。砰砰炮在炮弹和弹药分离时经常发生卡壳问题。这在地中海行动(“戟”行动)中已经出现过。虽然此后弹药经常被检查,但卡壳问题比“戟”行动时更加严重。“B”炮塔上的砰砰炮一直开火,直到船只最终倾覆前五分钟才停止。它没有机械故障,但经历了12次弹药分离的情况。其中一门砰砰炮由于倾斜而卡住。反击号也报告了类似的砰砰炮问题。厄利孔炮也发生了卡壳,但次数少得多。
舰上的281型空中预警雷达在船只进入防空状态前不久一直处于待机(反方向探测)模式。它出现了一些保险丝问题,但一直工作到被一枚炸弹击中腰部,切断了两个天线之间的连接。其中一台285型雷达没有工作,但另一台在12,000码的距离上捕捉到了攻击者。舰上的火控设备(包括282型雷达)一直存在问题,可能是由于湿度的影响,只有一台282型雷达处于工作状态(指挥官决定不在这些次要设备上投入太多精力)。
威尔士亲王号沉没后,舰长利奇因采用了错误的战术而受到批评。他最初将船侧面对接近的鱼雷轰炸机,以便充分利用他认为最有效的中程防空火力——5.25英寸炮。此外,他知道剧烈的转向可能会影响他的高角度火控系统。利奇舰长直到明显看出5.25英寸炮的弹幕对来袭飞机无效时才开始转向(以避开鱼雷轨迹)。这一延迟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其中一枚鱼雷击中后部时,船只仍在转向。如果利奇舰长像反击号那样早些转向,他本可以避开鱼雷轨迹并幸存于那波攻击。他可能还能成功躲避最后一波攻击者。日本飞行员集中攻击了反击号,反击号成功避开了19枚鱼雷中的17枚。他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对威尔士亲王号发动进一步的攻击。相反,如果利奇舰长完全不转向,鱼雷会击中船侧的防护系统,该系统设计用于抵御更强大的弹头。当然,不清楚在遭受严重鱼雷损伤后,威尔士亲王号的表现会如何,或者如果她在那种状态下幸存,新加坡是否能够修复她,使她能够在日军向基地推进时逃脱。然而,这些考虑表明,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远非一个必然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飞行员集中攻击反击号(其战斗力远不如威尔士亲王号),这表明他们在分配攻击目标方面并不特别擅长,这也预示了美国在莱特湾的失败(飞行员集中攻击武藏号,但对其他船只只造成了轻微损伤,这些船只在第二天出现在萨马岛附近)。
在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的主力舰进行了改装。到1943年,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急需现代化的时间点,英国海军部计划在美国对纳尔逊号进行现代化改造,而在英国对罗德尼号进行改造。然而,这两个计划都未能成功。美国海军拒绝了英国海军部设想的广泛现代化改造。这个风洞模型展示了英国海军部的期望,包括四台美国Mk 37指挥仪和八座双联装5英寸/38倍径炮塔。
**生存:亚历山大港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
1941年12月19日,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都停泊在亚历山大港时,遭到了意大利人操鱼雷的袭击。意大利人将500磅到1000磅的炸药直接放置在船体下方或海底(水深8英寻,约48英尺)。伊丽莎白女王号下方的炸药将“B”锅炉房的底部炸入船体,并在“A”和“X”锅炉房下方造成了类似但较轻的损坏,损坏区域覆盖了190 x 60英尺的范围。所有四个锅炉房最终都进水至主甲板水平,锅炉和辅助设备严重受损。船只虽然进水,但仍继续漂浮。在美国诺福克海军船厂进行的修复工作耗时17个半月。
勇士号下方的炸药放置得不太理想:它位于左舷凸起部分下方,靠近“A”炮塔的位置。它炸开了60 x 30英尺范围内的下部凸起结构。尽管在破损区域外的损坏较轻,但“A”炮塔旋转结构的底部发生了变形。“A”炮塔因此失效。修复工作首先在亚历山大港进行,随后在德班进行,耗时6个半月。
1943年,德国人引入了一种新武器:制导导弹(包括炸弹和滑翔导弹),其中一枚严重损坏了战列舰“厌战”号(另一枚则击沉了意大利新战列舰“罗马”号)。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开发了防御性干扰器(Type 650/651),这些设备被安装在所有被指派参与诺曼底轰炸任务的舰船上。拉米利斯号展示了她的干扰器,位于主桅后方的短桅杆上。她的前桅顶部安装了用于拦截E艇通信的“Headache”拦截装置的垂直偶极天线。她还配备了美国提供的TDY和Carpet III(通常用于空中)干扰器,其中TDY可能使用了前桅下方指挥仪位置的天线。值得注意的是,她保留了这一侧的四门6英寸炮,而马来亚号和厌战号在轰炸任务中移除了这些炮。
**厌战号与FX 1400的对抗**
厌战号在萨勒诺海滩附近以10节的速度航行时,遭到了两枚德国制导炸弹(FX 1400)的攻击。一枚炸弹击中了烟囱后方的艇甲板,穿透了多层甲板并在双底结构中爆炸,炸出了一个20英尺长的洞,并摧毁了4号锅炉房。另一枚炸弹在5号锅炉房附近的舭龙骨底部水下爆炸,导致2、3、4、5和6号锅炉房、双底空气层及其他舱室进水。两个机舱和1号锅炉房、两个发电机房、轴通道及其他机械舱室的缓慢进水得到了控制。所有锅炉都因冲击和进水受损,但主涡轮机未受损坏。电力系统失效,船只失去动力。
这次攻击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未来的战争形态,因为攻击者能够在厌战号机动时修正第二枚炸弹的轨迹。这似乎是唯一一次对英国主力舰造成真正破坏的近失弹。厌战号进水5000吨,被缓慢拖往马耳他,抵达时距离被击中已经超过两天半。在那里,她进行了临时修补,以便在11月前往直布罗陀。厌战号已经被指定为诺曼底轰炸部队的一部分,因此没有时间进行大规模修理。1944年3月9日,她带着两门15英寸炮塔和4号锅炉房失效的状态启程前往英国。在罗塞斯,其中一门15英寸炮塔得到了修复,但“X”炮塔仍然无法使用。在轰炸诺曼底海滩后,厌战号返回朴茨茅斯,随后被命令前往罗塞斯更换炮管。途中,她于1944年6月13日在“Y”炮塔附近触发了水雷。左舷的两根轴失效,船只速度降至10节。船体结构的削弱使得“Y”炮塔每次只能发射一门炮。左舷外侧轴从未被更换,剩余三根轴中有两根偏离了正常状态。1944年8月,她进行了修理后的试航,速度达到15.5节。她仍然是北海轰炸部队中唯一可用的战列舰,与浅水重炮舰“厄瑞玻斯”号和“罗伯茨”号一起执行任务。1944年11月,朴茨茅斯司令部接到通知,只有在陆军推进到德国时才会需要她,届时她可能需要支援夺取控制埃姆登或汉堡入口的岛屿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海岸防御非常强大,不仅需要厌战号,还需要所有其他可用的战列舰。需要提前七天通知才能调动厌战号。1945年1月5日,厌战号进入待命状态,但当时计划的行动被无限期推迟。厌战号于1945年2月1日退役并转入预备役,1946年7月31日被列入处置名单,此时她的所有炮塔已被移除。
这是皇家海军所得到的改进。对纳尔逊号最明显的改进是增加了四座四联装博福斯高射炮,其中两座安装在舰桥结构前方的新炮座上,另外两座则安装在烟囱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