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晚,传奇指挥家库恩以 85 岁高龄跨越重洋重返中国,带来了一份珍贵的音乐大礼:执棒中国爱乐乐团连续演绎六首瓦格纳的歌剧序曲。消息一出,“瓦迷”们瞬间沸腾,迅速锁定于中山音乐堂上演的这一场音乐盛宴。回溯 19 世纪,卓越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横空出世。其音乐作品如同他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激情、矛盾和戏剧性。其歌剧作品更是艺术丰碑,叩响着一代代听众的心门。
音乐会的开场曲目是《黎恩济》序曲。《黎恩济》1842年首演于德累斯顿,是瓦格纳第一部取得成功的剧作。它由瓦格纳本人编写剧本唱词,取材于罗马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史。人文主义者黎恩济带领群众反抗贵族的暴行,虽然初时取得了成功,制服了贵族,但最终却因与市民的冲突,黎恩济在寺庙祈祷时被群众放火焚烧,悲惨地死于烈焰之中。这部序曲的音乐效果堪称惊艳,其配器法运用精妙,营造出壮烈之感。丰富的织体、叙事性的旋律,再加上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强大张力,充分彰显出这是一位年轻天才的扛鼎之作。序曲开首的长音是反抗狼烟的动机,弦乐接着奏出沉稳而抒情的乐句,代表着黎恩济甘愿为人民牺牲的决心。随后慢慢推往高潮,欢欣的气氛代表人民取得了自由,是为胜利的呼叫。黎恩济动机以轻快的形式再次出现,和人民一起庆祝,最后序曲于有如圣咏颂歌的氛围下完结。本场音乐会见证了中国爱乐首次演出《黎恩济》序曲,艺术家们的演奏充分地展示了瓦格纳并不只是有着高超技巧的大作曲家,更是一位音乐家、艺术家。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绝妙的作曲技巧、而在于创作作品中浑然天成的独特灵感与音乐直觉。
音乐会上,库恩大师尽显亲和风范,与现场的乐迷们展开了温馨的互动。每一曲演奏完毕,他都会优雅地转过身来,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向台下热情的观众们送上诚挚问候。不仅如此,大师还凭借着自己深厚的音乐造诣,逐一对瓦格纳那些经典作品背后蕴藏的音乐内涵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与介绍,配合着大提琴首席赵云鹏优秀的翻译,引领着乐迷们一步步踏入瓦格纳的音乐世界,让大家沉浸在音乐与知识交织的美好氛围之中。
第二首《罗恩格林》序曲,是瓦格纳有史以来创作的最动人的歌剧序曲之一,如天国般美妙:音乐中充满了悠扬的乐句,满是神圣的意象。乐曲最开始的部分就写得非常有趣。开头四小节的主题动机先由4个小提琴组演奏,接着是2支长笛和2支双簧管,最后由4把独奏小提琴的泛音收尾,形成了幻彩迷人的音效。瓦格纳在序曲中对弦乐的分层方式也非常有趣。描绘圣杯的移动,他通过一层层配器的微妙变化,创造出潺潺流动的效果,主题顺着声部依次传递。圣杯在一群天使的护送下降临人间,细细聆听这熠熠生辉的两个音,由黯淡到光明,最终又渐次式微,恰似圣杯在幽暗中散发出迷人的光芒,神秘且令人神往。接下去由第一独奏小提琴和第一小提琴组演奏圣杯的主题,悠远神秘。然后圣杯主题转到木管声部,由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来演奏,音色变得更加明亮温暖。圣杯主题的第三次出现,由圆号和中提琴、大提琴来演奏,更加宽广深情;接着,圣杯主题逐渐推向高潮,仿佛宣示出圣杯骑士罗恩格林对艾尔莎的爱情。但这高潮转瞬即逝,音乐渐弱,下行的音调显得非常惆怅。当四把独奏小提琴在序曲接近尾声时再次出现,令人联想到天使将圣杯带回天国,静谧中仿佛圣杯骑士渐渐远去……
随后演绎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是第一部瓦格纳自己认为完美的歌剧作品。从这首序曲于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上演的情况来看,在演奏技巧上对乐团而言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然而,库恩先生却认为,在中国爱乐乐团这里不存在这样的困难。事实也的确如此,最终演出的效果正如他所期待、所赞誉的那般精彩绝伦。1838年,瓦格纳乘船在海上遇到风暴,轮船停在荷兰的一个港口,这使他想起了《荷兰人的故事》,于是产生了将它改编为歌剧脚本、谱成歌剧的想法。1841年,他写成了这部歌剧,并起名为《漂泊的荷兰人》。乐曲从描写海上的风暴开始,音乐夹杂着水手的呼喊和大海的汹涌与喧嚣。在小提琴用震音描写海上风暴的音乐中,不时响起荷兰人顽强拼搏的主题。激昂的乐声逐渐平息,一支柔弱的英国管奏出了温雅而美丽的乐句,仿佛荷兰船长的船已驶入平静的挪威港湾。后面一部分则是用荪塔决心以自己忠诚的爱情,去拯救船长唱段的旋律。在音乐的进行中,荪塔的主题与荷兰人的主题不时交织出现。尾声中,荪塔的主题变得坚定而有力,音乐描绘了荪塔纵身跳进悬崖,船长的船也沉入到海底深渊。全曲在柔和的乐声和幻影中结束,使人联想到荪塔和船长的爱情冲破了诅咒,终于收获了幸福。
怀着对艺术理想的追求,瓦格纳创作出了《唐豪瑟》。这部巨作力求最大程度地表达英雄主义情怀,同时融入了瓦格纳深邃、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考。而其序曲一直是音乐会中脍炙人口的作品:它以音乐叙述出全部故事梗概,李斯特把它称为“根据歌剧剧情而写的交响诗”。该序曲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与第三部分描绘了缓缓而行的罗马朝圣者的行列,具有赞美歌和进行曲的特点,旋律悠缓庄重,充满了虔诚、崇高的情绪。第二部分采用奏鸣曲式,描写了维纳斯堡中众神狂宴、花天酒地的场面。关于这部歌剧序曲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天瓦格纳出门散步,走到半路听到一阵声响,是消防队的警笛声。他从中取材,翻起袖子开始写。又一阵警笛声响起,他继续往前走,琢磨着将会发生什么。随后消防队开到一栋失火的房子跟前,当瓦格纳走到那里时,整栋房子已经全部着起火来。有个老太太等在那里……可以说她等着被瓦格纳写进曲子。乐队开始了大独奏,长号尖啸着:老太太坐在那儿抽泣起来——因为是她造成的火灾。这部歌剧对于瓦格纳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成功,但在巴黎抵制他的人也不少——正如生活道路困难重重,但音乐总是如此美好。这是中国爱乐的“看家曲目”,自他们建团音乐会以来,这一定是演出的最频繁的瓦格纳作品。
最后演绎的是瓦格纳十分著名的两首序曲——《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瓦格纳堪称一位爱就要爱到极致的浪漫主义殉道者,他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其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这部作品的故事蓝本源自一首古老的爱情诗,该诗在中世纪欧洲的诸多语言中历经反复改编,传唱着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凄美爱恋。单独演奏序曲而不演奏爱之死是不多见的,我想可能是长期浸泡在歌剧乐池中的库恩无法容忍器乐的改编所致。
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之死之后瓦格纳创作了《纽伦堡的名歌手》,这对他来说是精力了耗尽力气的狂热之爱后巨大的释放与松弛。瓦格纳理解到:为爱疯狂固然重要,但同时应该保持大脑思维的清晰与生活与音乐创作的严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深深吸引着年轻人,它深情而动人;同时纽伦堡的名歌手也吸引着那些有着复杂生活阅历的人。瓦格纳在这两部作品中将音乐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为所有后世的听众提供了非常丰厚的精神食粮。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中,弦乐依然璀璨,灵巧的双簧管独奏演奏地自信而充满活力,庄重深沉的大号在演奏这件乐器的困难片段时在高音与颤音是展现了对这件乐器十足的掌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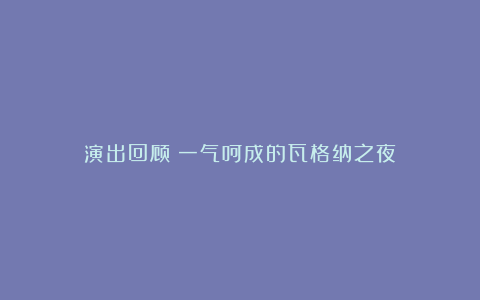
瓦格纳的歌剧前奏曲是“浓缩的精华”,一气呵成的瓦格纳之夜,让听者如饮玉液琼浆。
文/胡玛李赫 摄影/韩军、罗维、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