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哥号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行路去。就开车捎上文哥和我,奔粤东而去。
没有既定目的,走到哪算哪。
走到汕头,我们停了下来。
汕头最火红的打卡点是小公园,走走看看半小时,再就生腌海鲜吃个砂锅粥,也就差不多了。
南澳岛说是“海岛天花板”,但对于深圳来的人,海并没有太大吸引力。
我最想去的是牛田洋,但汕头所有的旅游资料中,包括最红的网红,都没提及牛田洋。
贺哥知道牛田洋的故事,听我一说,也想去看看。
文哥是转业军人,听说牛田洋故事的主角是军人,也同意去看看。
牛田洋田间一景
牛田洋位于汕头市西北部,榕江与梅溪河的入海交汇处,本是一片滩涂。
1962年,解放军41军122师进驻牛田洋,围海造田,造出良田11700亩,亩产量达1190斤。其时,中国刚从大饥荒中挣扎过来,122师的成功,如同引爆一颗精神原子弹,造成了全国性影响,并催生了毛泽东后来的“五七指示”。
1968年,122师调防,55军219师接过了牛田洋这杆生产红旗。
与219师一起来到牛田洋的,还有来自北京、四川、广东等地的2183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遵照“五七”指示,来接受“再教育”的。经过部队的大熔炉锻炼,再分配至合适的岗位。
1969 年 7 月 25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台风预警,6903号超强台风(英语Typhoon Viola维奥娜)正逼近中国大陆,可能在广东汕头地区登陆。
此时,正是牛田洋的“双抢”时节,抢收完了早稻,正在抢插晚稻。解放军战士与大学生正在进行劳动竞赛,没有人在意收音机里的警告。
台风预报,倒是惊动了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深夜里亲自给汕头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做好防灾抢险准备,一定要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一定要保证国家财产安全。
老鼠和蛇听不懂天气预报,但它们能预感到危险来临,不顾人们追打,纷纷从洞里爬出来,向高处转移。
鸭子不愿意出窝棚,不愿意下水。
7月27日午后,鲍浦公社的一个副主任不放心,来到牛田洋军垦农场司令部。部队官兵和大学生多为外地人,基本上没见过台风,更没有抗击台风的经验,副主任只怕基地有个闪失,1922年的大台风,可是让汕头死了8万人!
基地领导胸有成竹:请放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不可能让旧时代的悲剧在汕头重演。
部队领导班子面对军用地图,开了一个会,精心制订了抗台风作战方案。
家属和子弟学校,按撤退线路,有序撤退至安全区域。
部队战士和大学生则分为若干个突击队,带上只有战时才使用的无线电台,巡查大堤,发现情况,马上组织抢险。“人在大堤在”,122师打下的红色江山,绝不能毁在我们手里。
张朝生,潮阳县人,1941年出生,家中独生子,华南农大兽医专业毕业,来牛田洋锻炼刚满一年。台风要来之前,张朝生请了三天探亲假,回家去了。在家里听到台风预报,张朝生提前一天归队。危急时刻,张朝生知道自己不能躲在家里当逃兵,不然,会影响他的考评成绩、影响分配。临近宿舍,张朝生看到同学们正列队朝大堤进发,就丢下行李,跑步跟上去,上了大堤。
1969年7月28日上午10点30分,6903号台风在汕头地区惠来县神泉港登陆,沿海平均风力在12级以上。台风来临时,正值大潮期,风、潮、雨交加,十多米高的巨浪,一浪接一浪汹涌而来,看似坚不可摧的石砌堤坝,在巨浪的拍击下,如同豆腐渣一般,扭曲、变形。
当年被台风摧毁的堤坝又建起来了,成了牛田洋一景
一处崩溃。
又一处崩溃。
手拉手护堤的勇士,只来得及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就被巨浪吞没。
张朝生成了第一批被冲下大堤的烈士。
1969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狂风恶浪无所惧 一片丹心为人民》的文章,再现了大堤决口时的英雄壮举:
突然,东堤出现了一个裂缝,海潮汹涌地灌了进来。
“堵住它!”共产党员、迫炮三连连长陈志兴一马当先,率领突击队用土袋、石头把裂缝堵住了。接着,工棚附近又被海潮冲开一个口子,堤土一块块往下崩塌。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抱起石块、土袋填进裂缝,抵御海浪。可是,风猛流急,石块土袋都被冲走了,脚下的堤土在继续滚滚流失。怎么办?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为保护人民群众安全转移,我们必须排除万难,堵住缺口!”指导员詹得洛话音刚落,陈志兴第一个跃进了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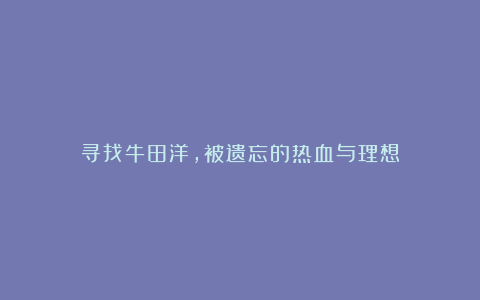
“向连长学习!黄继光能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我们也要用身体堵住海潮!”战士张衍钦纵身跳进缺口。接着,第三个、第四个……大家都跳进缺口,手挽手,心连心,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指挥部发现形势严峻,想通知部队撤退,才发现特意搬出来的无线电台,因为机房被台风摧毁,不管用。
按照作战计划,三发红色信号弹,也是撤退命令。
可是,信号枪打出的信号弹,一上天,就不知道给风吹哪儿去了。而且,第二发哑火,信号枪一举起来,里面就灌满雨水,打不响。
营长把信号枪信号弹擦干,勉强打出第二枪,也是只蹿升几米,就给风吹跑了。
通讯员赶紧往大堤跑,通知部队撤退。
三十里长的大堤,此时已被冲垮好几处,有些地段,通讯员过不去。
接不到撤退命令的战士们,只能死守在大堤上,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七机部(后来的航天工业部)有一批北京过来的女大学生,按司令部的部署,所有女生及家属都在先撤之列,但七机部的女生不愿意做温室里的花朵,坚持要和男同志一样战天斗地,也上了大堤。
当大堤垮塌,三个女生被卷入大海,慌乱中爬上一个稻草垛,随波漂浮。
突然,三个女生感觉不对劲,互相打量,才发现彼此的胳膊上、腿上,都缠满了五彩缤纷的蛇。好在,蛇没有咬人的意思,它们只是太冷,缠在人身上取暖而已。
《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情节:83名来自5个单位的勇士,困在一段长两米五宽四米的断堤上,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员在中间抱紧石头,群众抱紧党员的腰,一个抱一个,抱成一团,抵挡风浪。煎熬一夜,他们终于熬到风浪平息,太阳出来了。83人齐声唱起了《东方红》。等他们终于获救,发现最里面紧抱石头的党员,胸脯和手脚被石头磨得露出了骨头。
《汕头大事记》记载:6903号台风,造成汕头全区死亡894人(一说1554人),其中553人(解放军官兵470人,大学生83人)被授予烈士称号。
死里逃生的大学生中,有一个男生叫李肇星,后来成为外交部长,他为牛田洋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站着死去的是英雄/永垂不朽的是理想。”
正是为了寻找永垂不朽的理想,我和贺哥、文哥走进了牛田洋。
贺哥和文哥一直在寻找永垂不朽的理想
牛田洋如今以美食著称,青蟹、糯米饭、番石榴,人称牛田洋三宝,更是远近闻名。但已没有多少人记得6903号台风,七八十岁的老一辈,对当年的台风还有印象,却说不清楚抗台风烈士纪念碑在哪里。我们驱车在牛田洋三进三出,几乎走遍其间的大路小路,才终于摸到了方向。
按照导航指引,我们来到“七·二八烈士纪念碑”。
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堆用雨布盖着的石碑,有一个角落没盖严实,能隐约看到几个军中大人物的名字。
我心中一愣,烈士纪念碑拆除了?
贺哥掏出纸巾,不断地拭擦那些石碑。
惆怅四顾,看到一道铁栅栏门。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写“开门请联系:135311……”。透过铁栅栏看进去,可看到山坡上的一个碑尖。原来纪念碑锁在里面,
我打通门上的电话,请求开门。
对方问我是不是烈士家属?我说我们是烈士敬仰者。
对方犹豫片刻说,门没锁,伸手进去就能拉开门栓,出来时,记得栓上门。
烈士陵园空空荡荡,就我们三个人。
贺哥擦拭纪念碑
上山的路,扫得很干净,有鸟在树丛中鸣叫,也有蛇从容自路这边蜿蜒至路那边。
碑记表明,1972年春,164师于此立碑纪念,碑上只有“七·二八烈士永垂不朽”9个字,以及4位烈士的名字。1999年重修,553位烈士的名字,全都刻上了。
至此,我突然明白,山下的那些石碑为什么拆除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术,从前与潮流合拍的语句,如今可能不合时宜,于是,必须重新来过。
“七·二八烈士”,曾是激励全国人民革命斗志的榜样,如今,却淹没在商业大潮中,默默无闻,只在每年的7月28日,这里会热闹一天,全国各地的牛友(牛田洋老战士和大学生自称),会汇聚在此,凭吊逝去的热血和青春。
对于牛田洋的这一段往事,大部分人选择遗忘,没遗忘的人,也不敢随便评说,只有内部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五军大事记》,简短评述了此事:由于对当时的灾害估计不足,忽视了强台风与大海潮的客观现象,另外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缺乏科学性,在特大自然灾害到来、人力难以抗拒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提出“人在大堤在”等口号,没有使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伤亡很大,国家财产损失严重……
站着死去的是英雄/永垂不朽的是理想。
(本文基本史实来自陈树仁著作《牛田洋灾难亲历记》及网络)
感谢关注,感谢分享
工作信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5687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