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一支军队如何从受命平叛,到陷入血战?一个政权如何从怀柔招降,到挥刀清剿?西宁,没有退路。
叛乱起源与清廷应对
1862年,青海大地动荡,不是边疆战争,不是外国侵略,是自己人动了刀子。
那年,湟中民团夜袭回民村寨,起因不复杂:田地争执,传教摩擦,税役重负,最终是一把火烧了清真寺,杀了三个阿訇。
马桂源没等清廷发话,直接杀回去。
马桂源,青海大通人,回族,祖上靠赶牲口起家,后来转做经商,弟弟马本源是骑手出身,打仗比说话利索。
兄弟俩平时在西宁贩马,和撒拉族人关系密切,几次小冲突都能摆平。但这一次,摆不平。
民团屠村后两天,马桂源集结八百人夜袭西宁东门,烧毁税卡,砍死知州。
当天夜里,西宁城西方向也起火,撒拉族人配合突袭,半个月内,叛军控制西宁周边十八个堡寨。
局势失控,陕甘总督迟迟不调兵,清廷不急,是因为这两人本来就是官府招抚过的绿营弃将。
地方官寄望他们“以贼制贼”,暗中运粮给马桂源,令其驱赶“更凶”的陕甘回军。
马桂源装得很像,他写信给兰州,说愿归顺朝廷,愿协助清军剿乱,信送到时,他已在湟水以西自立“陕湟兵马大元帅”。
招降政策继续,有人说,只要稳定,不怕假降,有人说,左宗棠一来,麻烦就大了。
1871年春,左宗棠抵陕,第一件事,不是部署剿匪,而是撕了马桂源的招降书。
他留下一句话:“马械不缴,不休战。”不解释,不妥协。
他命刘锦棠出兵青海,不是谈判,是进攻,老湘军还剩下五千主力,从长沙调至兰州,补齐枪械,整军三月。
左宗棠不信这场乱能靠收编解决,他见过陕回之乱尸堆如山,不打,不会停。
刘锦棠出兵,路线定在碾伯出发,经乐都、湟源,直插西宁,先切西宁粮道,再逼大通,让马桂源失去退路。
这不是清廷惯用的围剿路线,是突袭,是斩首,左宗棠押宝刘锦棠,不看信、不留情。
关键战役与双方伤亡
1872年9月,湘军从碾伯出发,越过湟水口,进入西宁战区。
前锋刚过羊角沟,就出事,七个堡寨同时点火,烟尘遮天,敌兵满山遍野,从石堆、灌木、土墙中杀出。
不是正面会战,是猎杀。
清军第一次进攻失败,先锋副将朱世超中弹而亡,四百士兵全数被围困,退路被切断,这不是游击,这是陷阱。
湘军迅速换打法,刘锦棠调出随军火炮,设置短距发射点,集中炮击山谷堡寨,再用三路突击强攻,他只给每支部队三个时辰,攻不下,就换人。
第三日,攻下小峡堡,堡内尸体堆到门口,腥臭难闻,回军撤退时,放火烧了粮仓,埋了地雷,炸死清兵七十余人。
战事进入焦灼,十月,回军发动反攻,白彦虎率骑兵偷袭湟源清军粮道,未能成功,被火炮击退,他放弃骑战,转入大通方向撤退。
这时,西宁城外围清军已完成合围,刘锦棠兵分四路,从小峡口、黄南堡、盘道岭等地同时推进,每日攻城,每日伤亡。
西宁城门被火攻灼开,十一月初十,清军强攻入城,遇巷战,回军用民宅掩护,架设地道,反复炸塌街巷。
城破日,马桂源未战,退守大通,马本源带两千人断后,清军主力从城南逼近向阳堡。
向阳堡之战最惨,白刃战,短枪、短刀、肉搏,天降大雪,士兵冻伤、失血、呕吐,地上全是断肢,根本分不出谁是湘军谁是回军。
三昼夜后,堡破,马桂源兄弟被俘,白彦虎突围逃往肃州。
清军损失惨重,阵亡提督2人,总兵4人,营官、校官百余,战后清军入城设坛祭阵亡将士,未设庆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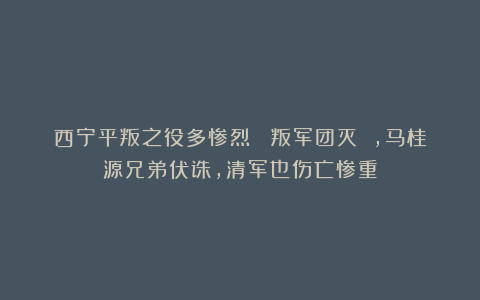
没有庆祝,只有死人。
叛军覆灭与马桂源伏诛
马桂源不是战死的,他被俘那天,右臂骨折,身上冻伤,牙缝里夹着焦炭。
押解当夜,他没说一句话,官兵怕他诈死,用马鞭挑开嘴唇,看他是否咬舌,他没咬,嘴角冻住了,说不出话。
马本源更惨,一条腿炸没了,是地雷炸的,自己埋的。
他们被用铁笼装起,从西宁押往兰州,日夜不歇,途经民村,有人扔石头,有人撒尿在笼子上。
到了兰州,未审先斩的呼声压满衙门口,左宗棠没急。他要他们开口,不是为了真相,是为了牵连。
审讯用了六天,马桂源咬死不说,马本源撑了三轮棍棒,说了。
供词不是长篇大论,是名字,一张名单,四十八人,分布在西宁、肃州、临夏、张掖。
其中一个名字特别刺眼——马麒。
马麒,曾是凉州营都司,后辞职返乡,在西宁开药铺,没人怀疑他是军人,马桂源和他是表亲,一起练兵、筹饷,私下还合资买过火药。
马麒是马步芳之父,审讯官记下这个名字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左宗棠懂,他下令彻查,不给机会。
马麒被斩于兰州南关,斩前只说了一句:“我不是乱臣贼子。”没人听懂。
马桂源、马本源,二月初六凌迟,一刀不快,七百六十三刀才死,三岁幼子,被阉为奴,送入守备营做杂役。
他们的族谱被焚,亲族被编为苦役,女性发配西藏做“边妇”,再不许称“马”姓。
清军未停,三月后,攻占巴燕戎格厅,焚毁撒拉族据点,斩首千余,残部逃至肃州,白彦虎带着数百人潜入酒泉以西。
肃州守军未开城,白彦虎被围三月,弹尽粮绝,十月投降,身披麻衣,徒步出营。
他没死,因识字、通波斯语,被遣戍新疆伊犁,后又流亡中亚。
西宁平叛结束时,青海三年未种地,百姓三成死于战乱,官员赴任需带兵,否则寸步难行。地上还残留断臂枯骨,黄羊啃骨如常。
役影响与历史反思
战火停了,官场开始动作。
清廷设“西宁办事大臣”,由陕甘总督节制,驻军八千,火炮百门,专责三事:清查教派、编户改土、征兵练武。
先动的是教门。原来挂在清真寺上的教旗被砍、焚、踩,阿訇限期登记,不许再开教习,所有经书收缴审查。凡不服者,充军。
西宁民众习惯“门宦制”,宗教大于行政,改土归流后,族长无权徭役,地方由知州、守备双线统管,实际听命于驻军。回民只能在军中留存话语权。
编制新兵时,马家残部主动请缨,左宗棠允之,设“青海回勇营”,实为分化收编,编入的多为原叛军子弟,给饷、给粮,但不予军衔,只称“卫士”。
这支部队十年后扩编为“西陲马队”,再后来就是“马家军”。
回看战役,最深的裂痕不是城池损毁,是人口空缺。
湟水谷地回民锐减六成,乡寨断绝,有人四代单传,再无亲戚。
左宗棠私下说过:“要剿,更要抚,但人心,怕的不是刀,是隔绝。”
他的话没传出去,传出去的,是“以汉制回”四字政策。
每年陕甘两地输送汉人屯垦,以备驻军所需。西宁逐步形成“回中汉城”格局,日后,城内汉商主粮,城外回民贩马,彼此有用,互无信任。
军事上,刘锦棠写的战报被送入军机处,成为边地作战范本,特别是“围点打援、分兵突袭、火力压制”,在后续镇压新疆叛乱时再次使用。
左宗棠未奖功,湘军兵员已损,需养,他只写一封信给刘锦棠:“你不败,是幸运,不是天意。”
后来有人说,西宁一役,杀得太狠,也有人说,不狠,就不叫平叛。
没人再去羊角沟,听说每逢秋后,山谷里还飘血腥味,风吹草动,有声如哭。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