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华县西关街的故事
作者:徐稳朝
西关街是华州城区一条街道。它位于城区的北面偏西位置,东起新秦路与华州路交会处,西与龙山路相接。因其地处古华州城的西门外而得名。和临渭区的老城街一样,街面都处在“三秦要道,八省通衢”的官道上。
西关街 刘焕民摄
在我们“六零后”这一代和前几代人的记忆里,西关街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一
听老人们说:明清时,有个华州人到北京去了,一说起华州城就说“yibaiyishiyiyanqiao”,有个北京人听了“赫得张不开嘴”。心想,黄河、长江够宽大了吧,也不见有几个桥洞?你华州倒是个“一百一拾一眼桥”?那河该有多宽哪?拗着劲要到华州来,结果被带到西关街“西头”一看——一棵柏树下有块石头,那块石头旁有个小河。
更大。
杨巷村口的“一百一十一眼桥”遗址 网友供
明清时,人们到华州城来,多是步行或是散行。指定聚集的地点,就是“yibaiyishiyiyanqiao”。
这分明就是个笑话,却笑得有理。让小不丁点的我,记下了“西关街”,也惹引着小不丁点的我要到“西关街”。
二
小不丁点的我,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西关街”的早已记不清了。
蒙童记事时,似乎并不知道“姑父”是在华县城里上班的,只知道“姑姑”最爱去的地方,是华县。而“姑姑”每到华县去之前,都是先到我们家来。那时的我,仿佛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小得尚能坐在“姑姑”飞鸽牌的自行车的前梁上,由“姑姑”带着到华县去。
“姑姑“用自行车带着我到华县去,是要经过北沙村的。再从北沙村穿行到老西潼公路。然后,沿着老西潼公路到西关街。到了西关街,也就到了华县。而到了“西关街”,“姑姑”最爱买“米花糖”让我吃。
西关街老房子 刘焕民摄
现在知道了,“米花糖”是一种著名的传统小吃。那时却不知道这么多,只知道糯米被弄成了圆圆的小球状,拿手中好玩,吃在嘴里香甜。
少小时,西关街就是这样和我联系在一起的。
三
西关街东头,有一个坐南朝北的“群益浴池”,给无数的华州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到浴池洗澡的人逐渐增多。特别是每年农历腊月廿三前后,农村里一些人便会拖儿带女,相约着到县城唯一的澡堂子“群益浴池”去洗澡。
我有幸也成为其中的一员,由父亲带着到西关街“群益浴池”去洗澡。既享福受到了洗澡的美处,也见识了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到西关街,再到浴池门前排队等待的场面。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洗澡人群,真是成当年西关街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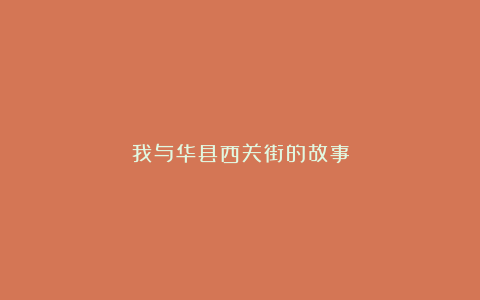
约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父亲在老家村北的“华县拖拉机修理厂”干活。由于父亲“勤奋好学,睿智多思,精通木瓦石诸工之匠能,名著乡梓”,技术堪称“全能把式”,受到厂领导的关注和肯定。
那时,西关街东头坐北向南的华州剧院和华县剧团正方兴未艾,四面八方的人云集“华州剧院”,观看华县剧团的精彩演出,成一时之风。“华县拖拉机修理厂”为了奖掖父亲“们”的贡献,我便有了和父亲“们”一起乘坐着“拖拉机修理厂”选派将要修返的“解放牌汽车”,到西关街看戏的好运。
母亲提早为我和父亲准备好干粮,我和父亲乘坐着厂里选派的“解放牌汽车”到西关街看戏。
“汽车”把我们我们拉到西关街东头。在离“剧院”不远处的地方,大家一一下车后,排列成队,负责人领队,我们鱼贯而入,进入了“华州剧院”。霓虹灯下,我见识了影视剧中上海滩似的演艺环境,远比我在家乡、在瓜坡镇戏楼的更现代大气。更意想不到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歆慕无比的男女“美”演员。
华县剧院南大门旧址 姚文龙供
我们看的是改编为现代戏的古装剧《窦娥冤》。新婚成寡的窦娥,在无赖张驴儿陷害、昏官桃杌的毒打下,成了杀人凶手,被判斩首示众。该剧剧情曲折,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尤其是窦娥在临刑前,满腔悲愤地许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要用异于常态的反自然现象,警醒世人,佐证她的怨屈。当舞台一一展现“窦娥冤屈感天动地,三桩誓愿一一实现”时,我很非常高兴和万分感慨的,深感艺术魅力的迷人与独特。
由此,西关街成了我内心深处的天堂!
五
西关街还是一个有历史故事的地方。
史载:西周末期,周幽王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演绎出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终导致西周灭亡。当犬戎入侵烽火燃起时,被封于华县的郑桓公,毅然决然地“报国勤王”,殉难于骊山之野,尸身被战马驮回,后迁葬于今郑桓公墓所在地。
民国时期的郑桓公坟 自民国华县志
我少小时,随父亲来西关街,在当时的华县锣钉厂后院中西侧,亲眼看过郑桓公的墓地。一介农夫的父亲虽说不出太多的《史记·郑世家》故事,却焉然在西关街给了我最初的“实物堪证”教育。
六
2003年春,被调到当时的华县党校工作。而工作单位,就在西关街西头。2007年冬,所办的身份证上的“地址”就分明地写着:“陕西省华县华州镇西关街党校院内”。
2008年郑桓公陵园修缮管理委员会成立,世界各地的郑氏族人纷纷捐款相助。2011年秋,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修葺一新。
郑桓公陵园 宋朝峰摄
现在占地10余亩的陵园,内有牌坊、前后照壁、陵冢、殿堂、尊塑、连廊等。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建成后,世界各地郑氏族人每年都来此地举行规模盛大的祭奠大典,也给西关街增添了新气象。
而我,就恰是这一“新气象”的见证者。
七
站在西关街中间的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内,倘佯在被称为“华夏郑氏之根”“世界郑氏世祖”的郑桓公墓旁,一种作为作县人的自豪感在心中奔腾。
蒙童时,被姑姑用自行车戴着来西关街;少小时,被父亲领着带着走着来西关街;少年时,与同伴相约来西关街;青年时,自己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串行在西关街;壮年了,就工作在西关街“西头”;老年了,还要将西关街在心里坚守。
我仿佛一下子就明白了西关街于我的意义——
西关街,不仅是一条古老、富有历史感的街巷,更是刻进血脉中的生命年轮。春日里,郑桓公陵园的松柏新抽嫩芽,与儿时姑姑车篮里晃动的槐花同频生长;盛夏时,父亲汗湿的衬衫后背洇出的盐渍,和少年时与同伴长途奔波后在饭店一碗面条的美味,都化作了西关街蝉鸣里的记忆琥珀。
来党校工作后,从校园正好能看到街口那株百年老槐树,看它春生新绿、秋染金黄,恍然惊觉自己已从追着夕阳奔跑的少年,变成了暮色里守望归人的老者。每当晨雾漫过青瓦屋檐,总能听见晨练老人哼唱的秦腔与童年节庆的喧天锣鼓重叠;暮色四合时,商铺亮起的灯笼又与父亲曾牵我走过的暖黄路灯交相辉映。
西关街 刘焕民摄
此刻,徜徉在郑桓公墓前,抚摸着斑驳的碑刻,突然懂得这片土地为何总让人流连。原来,它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西关街,更是连接着三千年前郑国始祖的精神脐带,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时光容器。那些被岁月揉碎的脚印、笑声与叹息,早已和青石板下的泥土融为一体,让每个漂泊的游子,都能在这里找到灵魂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