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大专院校、文化艺术机构纷纷内迁,许多著名艺术大家如徐悲鸿、庞薰琹、叶浅予、关山月、闻一多等,随着这内迁大潮来到了贵州。本文通过记叙三位漫画大师丰子恺、马得、黄尧抗战期间在黔艺术与生活趣事,以思前贤,以启来者。
一、丰子恺为遵义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造像
(一)遵义生活激发创作激情
1940年初,一袭长衫、美髯飘飘的丰子恺,应浙江大学之邀,携全家历经艰辛后抵达遵义,担任“艺术欣赏”和“现代文学习作”课程的讲授老师。
起先,子恺先生寓居在士绅罗徽五位于遵义新城北郊外的庄园。罗庄虽然很宽敞,但远离浙大在遵义城区的校本部和各学院。没过多久,他一家就迁到遵义新城狮子桥南侧的南坛巷,租赁熊作霖家一楼一底数间新房子安了家。
熊家新屋临湘江河而建,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当时,租住在熊家的还有浙大一蔡姓教师一家。丰家小女儿丰一吟,没多久就成了三家小孩们的“娃儿头”。子恺先生对新居非常满意。有一天,他倚楼临窗独酌,仰望夜空月明星稀,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即以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笔意,为新居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星汉楼”。
除了繁忙的教学外,子恺先生以旺盛的精力创作了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漫画和宣传画,其中最著名的为《国难之忧》。编辑出版了《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客窗漫画》《抗战歌选》第一、二册等等。尤其是重新编绘整理出版的《子恺漫画全集》,汇集了他前半生的全部漫画成果。其中,许多漫画本来已遗失,全靠他回忆整理。当时因赠送给蔡家小孩蔡贵侯等原因,他在遵义的画作只有少部分没有收入集中出版。全集得以出版,了却他的一桩心愿。
▲《黔道》丰子恺
子恺先生一家在遵义逗留近四年的时间里(1942—1946),是他一生中创作成果丰硕的时期。黔北丰厚的文化底蕴、遵义淳朴的民风、自然美好的山川、无不给子恺先生留下美好的印象。一家人在遵义获得难得的团圆与安宁,长女在遵义成婚,膝下欢乐孩子们的童真烂漫,激发了他艺术创作的灵感,而且画作也有了新的变化。以前的作品以水墨为主,子恺先生在遵义所画的作品开始上色。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前任主席、著名艺术家谌宏微先生认为,“在遵义,黔山贵水的影响使丰子恺先生在’古诗新画’的再次创作中绘画风格大为转变,水墨转向设色,小尺幅转向大画幅。而逃难中的三年安定生活,在这些尺幅之间不经意地流露”。丰子恺的外孙宋菲君说,一大批以古诗词为画题的彩色山水人物画,代表“子恺漫画”的最高水平。
在大后方流寓的艰难岁月里,子恺先生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雅士一样,居陋巷,仍喜“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改其乐。他与遵义文化名流李培荪、蹇先艾、王光衡、朱穆伯、李维伯等结识,尤与德高望重的乡贤、大学者赵乃康相交最深。他与赵乃康先生等朋友结伴到距遵义城东80余里的乐安江畔的“沙滩”子午山谒墓之行,为遵义的文化历史记忆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子午山纪游册》丰子恺
笔者通过顾朴光、顾雪涛、陆昌友等先生之文,了解到子恺先生《子午山纪游册》产生的背景、经过及其间的逸闻趣事,具体情形如下:
1941年正月初七,是民间习俗所称的“人日”那天,丰子恺、赵乃康两位先生,偕“雁荡才子”李瑜、浙江乐清人冯励青、湖南长沙人罗展,到位于遵义沙滩子午山为仰慕已久的“沙滩三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扫墓,后将此行绘画成册,是为《子午山纪游册》漫画册。
子恺先生一行在沙滩历经5天的行程,他们访幽探胜,先后游览了沙滩禹门寺、节孝祠等名胜古迹,参拜了郑、莫、黎三贤墓,他们深为沙滩美妙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又为“寺观之兴废,陵谷之迁变”而发思古之幽情,纷纷吟诗作画以抒情怀。在节孝寺寺僧请求下,丰子恺描摹了寺中佛像。赵乃康称:“先生画佛,每一笔一呼佛,百八笔而佛成,此独有之奇也。”赵乃康作诗云:“一笔一佛佛生辉,百八笔声皆慈悲。”李瑜诗云:“何劳尘外访,画里见维摩。”
他们返回遵义城后,丰子恺、赵乃康、李瑜将此行所创作的诗文、漫画编辑成册,交遵义孤儿院印刷发行。由于郑珍是沙滩文化名人之首,其旧居和墓地均在子午山,故诗画集定名为《子午山纪游册》。
《子午山纪游册》共收录诗词25首,文章 6篇,漫画13幅。漫画全部为子恺先生所绘,题材大致有四类:第一类为人物肖像,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造像共三幅;第二类为郑、莫、黎墓茔共四幅,其中三幅为写生,一幅为郑墓原状想象图;第三类为沙滩的风景名胜,共三幅,分别绘胡忠相山庄、节孝祠和清乘桥;第四类为诗意画,共三幅,《坐久意未厌》和《柳待春回绿未生》系根据冯励青、李瑜所作诗句绘成,《折取一枝城里去,教人知道是春来》绘子恺先生自己所作诗意。
▲《苗族情歌》马得晚年绘
子恺先生所作的这批漫画既可作为单幅作品欣赏,合起来又似一组连环画,作品构思精妙,人物造像传神,生动记录了子恺先生一行沙滩之旅的行程及活动。在《清乘桥》《坐久意未厌》和《柳待春回绿未生》这三幅作品中,子恺先生将自己的形象绘入画中,这在他的漫画作品中十分罕见。该画册也是子恺先生一生中专门为一次旅游而创作的作品。
1946年,丰子恺先生一家随浙大东归,结束了在贵州的生活,但他为贵州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著名漫画家、艺术家马得(1917—2007),姓高,南京人。出生那年,因母亲属马,马年得子,故取名马得。马得7岁时,父亲去世,给马得留下的只有笔墨纸砚、碑帖画册、金石印章,这些文物墨宝对马得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生受用无穷。
(一)创作《苗家情歌》,崭露头角
1987年,《漫画世界》杂志重刊了马得的十幅作品,更名为《苗家山歌》。2004年,贵阳市档案馆研究人员在发掘老贵阳资料时,找到了两篇马得先生所写的有关贵阳的文章。他们读后深受感动,觉得有责任将马得所画的情歌漫画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出版,于是到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查找当时出版的《新民报》。可惜各馆收藏均不全,未能见到马得描绘贵阳风情的漫画。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先生的工作单位——江苏省国画院,并非常顺利地联系到了年近九旬的马得先生及其夫人陈汝勤女士。当他们说明来意,却被告知江苏美术出版社已将稿件拿走,准备出单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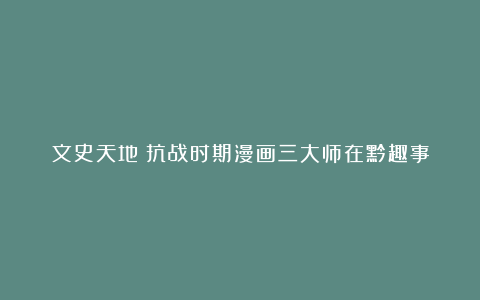
最终,曾在贵阳生活了七年,对贵阳充满深厚感情的马得先生及其夫人,觉得画稿交由贵阳出版意义更大,遂要回了稿件,成就了贵阳市档案馆为其整理编辑出版《漫画情歌:马得的贵阳情结》这一幸事,让贵阳市民、贵州人民能够见到50多年前就备受欢迎的佳作。
2014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张立宪先生策划编辑的《蛮情歌》。编后记中介绍道:
1949年之后,曾陆续出版过部分情歌漫画的作品集,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作品未能公开面世。此次他们征得马得夫人陈汝勤老师同意,将马得情歌漫画作品重新整理出版。应该说,本书是到目前为止,能够比较全面反映马得所创作这部分题材的资料。收入书里的黑白画稿部分,都是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遗憾的是,历经多年,原稿已失,现有画稿是马得家人从各方搜集的复印件,因此在印刷和制版上有一定难度,我们通过处理,尽量再现出原作“原始又这样现代的漫画语言”、“稚拙”又这样诗意的漫画境界。
▲《漫画贵阳》黄尧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马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创作的部分彩色作品。马得在书中序言说:过了若干年后,他的绘画技巧提高了,也曾试着用水墨方法来画《苗族情歌》。他在探索过程中用了几种不同的笔法。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变化,很难找到当年的感觉,缺乏那种带有原始意味的淳朴和拙味。
马得年轻时所绘的黑白苗族形象更具山野之气,画中自然直朴的个性、爱憎分明的性格特色、热辣辣的情感表露令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中年后一改画风,所画戏曲人物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在同一艺术家身上前后期创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一现象比较罕见。可以说,马得的苗族情歌画与戏曲人物画自成一格,各有千秋。
黄尧(1917—1987)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漫画运动的中坚力量和积极推动者,他所创作的“牛鼻子”艺术形象享誉中外。他在贵阳创作了一百多幅以“牛鼻子”为主角的漫画,为贵阳永远地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社会风貌的写照。
黄尧的家世谱系,可以追溯到汉朝。先世黄香被列为历史上的“二十四孝”之一,“儿童知子职,千古一黄香”写的是他。一千多年以后,黄尧的父亲希望三个儿子能光宗耀祖,因此以中国三位传奇贤君“尧”“舜”“禹”为他们起名。黄尧没有让父亲失望,作为漫画家、书法家、画家、历史学家、作家和哲学家,他一生都不懈地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着对他人的关爱。
黄尧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传统书画启蒙。日复一日,黄尧用毛笔蘸雨水,在父亲给他的光面城砖上习练汉碑,狂草,全用中锋,以掌握运笔的基本技法。黄尧说:“我必须学习拿画笔时胳膊的正确姿势。在砖上的不断练习给了我胳膊一种内力,并且让我养成了工整而流畅的书写习惯。”
▲黄尧回忆贵阳的文章
1933年,16岁的黄尧成为一名记者,供职于上海《新闻报》,从事专栏和时评的编辑工作。不过一年后,报社让他创作漫画,让他的深厚绘画功底有了用武之处。很快,这位艺术家以汉画线条作的漫画人物“牛鼻子”诞生了。
黄尧的漫画还有一大特色:每幅漫画的标题都用毛笔书写,并且采用颠倒写法。这样写的字看起来很像是小孩子写的,为漫画增添了些许童真和童趣。黄尧称之为“出云书”,因为写的时候每个字都是180度颠倒写的,正如晋末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所描绘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牛鼻子无论是他的外形,为人处世的态度,还是他的幽默感,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典型的时代特征,贴近当地生活。当时上海《新闻报》的读者,往往是先看“牛鼻子”再看新闻。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牛鼻子在马来西亚》 黄尧
被誉为“中国动画之父”的万氏四兄弟万籁鸣、万超尘、万古蟾、万涤寰,联名写了评论文章《剖解牛鼻子》。他们十分推崇牛鼻子,认为“这一形象汇集了中国充分有趣的诙谐点,不去拾西洋滑稽的牙慧,在国际幽默漫画上创立自己一种特别的风格,高高地独飘起一面旗帜,扬起另外一种号声来”。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四兄弟联名写一篇评论是相当罕见的文化现象。
1942年,为躲避在沦陷区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黄尧流寓贵阳。他写道:“承朋友的留邀,觉得寒凉中有些温暖。”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保留着许多古幽风趣的贵阳。
贵阳自然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色彩,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在三个多月内,创作了一百多幅以“牛鼻子”为主角的漫画,表现了贵阳这一很有诗意城市的风土人情、百态万象。《百寿图》和他在贵阳创作的《漫画贵阳》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发行,为贵阳永远地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社会风貌的写照。黄尧先生在《漫画贵阳》序言中道出了他对贵阳的深厚感情:
我觉得“贵阳”城很有诗意,尤其是四环净白的城墙,配合着啷啷啷驮马铃的声音,假使我要写描写贵州的剧本,不论制曲、谱歌,或舞蹈,这是再好不过富于诗景的背景和效果。
黄尧先生在贵阳先后举办了4次画展,分别为《百寿图》《战争中的中国人》《漫画贵阳》和《漫画昆明》《漫画桂林》,观者如潮。1942年11月26日至29日,应《贵州日报》邀请,黄尧先生在贵阳富水路商友俱乐部免费举办《漫画贵阳》。并精选24幅由金马摄影社摄制成两套(各12幅)供爱好者收藏。售画所得捐作救济流民与乞丐的基金。
在这些作品中记录下许多十分亲切与久违了的风俗人情、名胜特产,如“茅台酒”“烧腰柳”“黄磷引火片”……更为后人留下了“梳子似的蓄水塘叫月亮井”“谁说天无三日晴”等特色景观。
黄尧先生在贵阳期间与学者名流交往甚密,他晚年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上的一篇文章,亲切地回忆了当年他与贵州学者谢六逸、陈恒安等雅聚的情景,这也成了贵州文坛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尧先生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到了南洋,于1987年病逝于吉隆坡。2008年,通过研究亚洲动漫的专家约翰·兰特博士的引荐,笔者与黄尧先生遗孀和孙女取得了联系,并于2009年5月,在赴新加坡开会期间,与她们相聚在狮城。经过几小时的交谈和连夜阅读她们不遗余力搜集到的有关黄尧先生的资料,这位热爱祖国、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穿越历史的尘埃,和他创作的经久不衰的漫画形象“牛鼻子”,出现在笔者眼前。
黄尧先生把贵阳漫画化,存心把漫画化的贵阳介绍到四海之内,使海内外人士知晓贵州真相,鉴赏贵州品格,赞扬贵州风光……当再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和文字时,他对贵阳的深厚感情和亲切眷念,仍令人感动不已。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