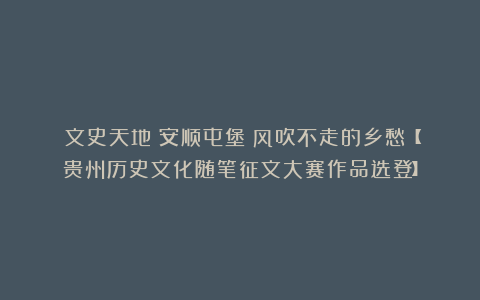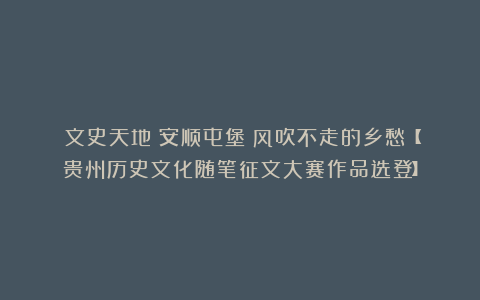|
总有几条老街睡在这里,总有几块石头横在这里,总有几个老人坐在这里,总有几间老屋守在这里,总有几个故事藏在这里。
屯堡,是一种方言,是一种建筑,是一种唱腔。贵州安顺,一个个屯堡村寨,一个个六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大明遗风的山寨,一个个石头一样默默不语的村庄,在时光的影子里静默在大山深处,石头一样不说话。这里曾经是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的主战场,如今是黔中腹地鱼米之乡。屯堡是明朝散落在贵州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朱元璋一落子就是几百年。如今,下棋的人已随风而去,这枚生根的棋,静默成历史天空中一个个标点,打在贵州安顺那些叫屯、叫堡、叫旗、叫哨的屯堡村庄。
在安顺,屯堡村寨石头一样随处可见。西秀云山屯、平坝天龙屯、普定下坝屯,是着墨较浓的那几个标点。
时常有画家,或学画的学生,三三两两,雨一样轻轻悄悄地落在屯堡村寨。定位,展纸,落笔;素描,写生,国画。或怕时间来不及,一时吸收消化不了,掏出手机先拍摄下来,回去再慢慢品味,慢慢落笔。石头的建筑,沿石巷而来的水牛,靠墙而坐的老人。用什么帮助时间记忆这些石头部落?用画笔,用镜头,用游走的心,用那些在风中飘来飘去的故事和歌谣?
安顺的春雨和江南的春雨一样,寂静。远处,学校里孩子的读书声;近处,演武堂地戏开场的鼓声,都被这无声的春雨湿润了。
春分了,油菜花开得疯狂。高原大地像一个被淘气的孩子打翻的颜料盒,平坦的田野,起伏的坡地,大块大块的黄,大块大块的绿。田埂上跑过放风筝的孩子,笑声在油菜花上跳来跳去。慢慢地又静下来,像被花上的蜂儿蝶儿带走了似的。牛蹄走过石板的声音,是不紧不急的鼓点。冬去了,春来了,夏种了,秋收了。
屯堡村寨,一般都有高大厚实的石寨门,卡在山垭口中间,挺立在仰望的目光里。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石板房,跟着一条石板街,从寨子的这头,走到寨子的那头,故事一样曲折,时光一样厚重。街口的第一间石板房,常常有一个老人守着一个石铺子,卖的是碗里的油盐酱醋,书包里的铅笔橡皮,办事用的香蜡纸烛。老人常常眯在阳光下瞌睡,但瞌睡极轻。听到有人走来,轻轻睁开眼,淡淡地打声招呼:来家喝茶。狗不叫,不咬,走过来闻闻裤脚,判断不是坏人,自己懒懒地走回去,在阳光影子里的滑石板上躺下来,继续它的狗梦。
走在屯堡村寨的石板街上,不时会迎面遇到赶着牛,扛着犁的男边老人,侧着身,笑着让你过去;女边老人一只手牵孙孙,一只手拿着两棵大白菜或三五棵葱蒜,慢慢地朝家里走去。男人们没有什么特别,倒是那些妇女们。从地里拎着菜回家的也好,在院里做针线活的也罢,一色的宽袍,大袖,花鞋。衣服是天蓝色的,头上的髻是乳白色的,脚上的鞋是藏青色的。耳上,还缀着环,说话的声音圆圆的,脆脆的,还会轻轻地转弯。你以为你是穿越到了明朝,遇到了江南水边的女人呢!没错,屯堡人600多年来一直沿袭了明代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恪守其世代传承的文化生活习俗,屯堡人的花灯曲调还有江南曲子的韵味呢。
屯堡人这支贵州最大的移民,600年来,由一支从北方出征的军队,平定南边这方水土后,一道黄色的圣旨,就把亦兵亦农的根深深扎在这里,在大山里生存繁衍。我的老家普定,以前就叫“定南”,一块“大明定南府”的石碑,就在石板街口横卧着。在贵州安顺很多屯堡村寨,很多房子的大门,不少坟墓的石碑,方向总是朝着远远的南京——南京是一座石城,安顺有无数个天龙一样大大小小的石头村寨,牵着它们,连着它们的,是根,是魂。
地戏是一定要跳的。农闲了,过节了,来客了,锣鼓响起,面具戴上,放下锄头,舞起刀枪,在石头舞台上酣畅地跳一回《薛仁贵征东》。地戏,从田间地头跳到寨子中间的石头舞台上,跳到国外的大剧院。法国人把这种头戴彩色脸谱,肩背五彩战旗,手持木制刀枪,大声阵前叫骂,在一块圆形空地上厮杀的地戏,叫做“戏剧活化石”。平时看到的地戏,场面不是很大,远没有过年时热闹。因为,有些跳地戏的人,到外面闯荡去了。过年的时候,他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放下行李,戴上“脸子”,背上战旗,拿起刀枪,高喊一声:“嘿,放你的兵马出来杀一仗喽!”何等的威风啊!
在安顺,在任何一个屯堡村寨,街道都很干净。哪怕是刚下过雨,也不显得湿,不积水。原来,600年前修建的石街,也有下水道。不低头认真看,看不出来。隔十余米,街上就会有一块石板,外圆内方,有棱有角,古钱的样子,当地叫做水漏,用来排水的。水就是从石孔里慢慢渗下去的。石坎,石柱,都是整块,或圆,或长,或方,根据位置承受的重量而定。院子也是由石块铺成,不管大小方圆,中间的一块,都刻有八卦或阴阳图案。日晒,雨淋,脚踩,光滑透亮,看起来,凝重,走上去,踏实,坐下来,安逸。石墙,石雕,是用石灰或糯米粑做浆垒石墙,石灰是石头烧的,糯米是土里生的,它们团结在一起,坚实无比,针插不进。再仔细看,房子地墙上都有朝着各个方向的射孔,细细的,十字形,手指般宽,筷子般长。从里面能把外面看得清清楚楚,而从外面,只能看到一个十字架的缝,黑黑的,琢磨不透。红十字是人道主义的标志,在屯堡村寨,曾经是防御的盾和还击的箭,如今,成了寻找过去的指针。
屯堡人是战争移民,几百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是从江南的大地方来的。远在纸上和唱词里的祖先,在江南的土里,跟自己同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的爷辈和父辈,在山上石头垒成的坟里。南京,是思念的故乡;安顺,是生活的热土。600年前,披坚执锐的军队来到这里,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后,又把老人和孩子接到这里,用石头垒起家,在石头上做起梦,成了战时是军人,闲时是农民的屯堡人。如今,他们的儿孙,一个个带着梦想离开这里,去求学,去经商,去闯荡。当年祖先们来了,没有回去,是因为皇命难违军令如山;如今儿孙们走了还会回来,是因为故土难离亲人难舍。有亲人埋葬的地方,有亲人生活的地方,就是故乡!屯堡,是屯堡人的故乡。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腊八……要泡谷种了,要收包谷了,要炕腊肉了,要舂糍粑了。大姑娘要发八字了,小儿子要剃毛头了,本家二爷爷要送上山了,高铁要穿过寨子,要拆房子,也要迁坟。遍插茱萸,少的岂止一个飘泊异乡的游子?在泪花模糊的眼里,故乡和亲人,石头一样真实得触手可及。
只有过年,鞭炮炸响后带着香味的硝烟在石头巷子石头房子间弥漫开来,时髦的高跟鞋和流行歌在石头之间欢快地跳动,锣鼓声中木制的刀枪在握锄的手里舞成回忆和向往,这些石头的村庄,就会更热闹,更生动,更丰满!
▲屯堡人服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妇女的衣着和装扮上。屯堡妇女始终保持大袖长袍尖头鞋等明代遗风,身着或青色或蓝色或紫色或粉色或绿色或白色的大襟大袖长袍,系“丝头腰带”,后吊长长丝绦,在袖口、衣襟处镶嵌美丽的花边。长发挽髻套上马尾编织的发网,插上银质和玉石发簪,腕戴银手镯,耳吊银质玉石耳坠,脚穿尖头平底绣花布鞋,客扎白布带(老年人多为黑色)。
风吹走的歌谣飘远没有,雨带来的消息湿透谁眼眸。千年万年大国小家如梦,岁月如歌人未老,回头一望是乡愁。
编辑:一 丹 付宗燕
校对:姚胜祥 王封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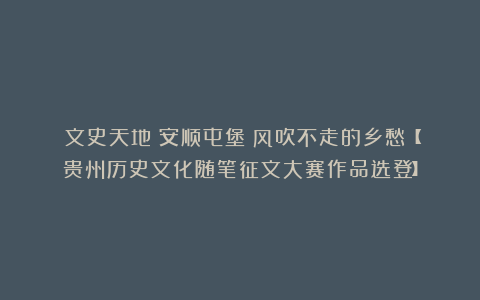
统筹:黎艳萍
审核:罗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