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草书《秋兴八首》为其四十一岁所作,诗文结合了秋日景致、古典韵味与诗意幻境,通过卓越的笔法展现出了他非凡的书法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与深思。通过精湛的笔法,王铎将秋日的萧瑟与诗意完美地呈现出来,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了艺术的力量与魅力。临习此作,尤需关注其用笔节奏的微妙变化,从疾如风雨的纵逸,到凝若沉铁的顿挫,皆在笔锋提按的平衡中构建了独特的艺术张力。
在王铎此卷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米芾的身影。但与米芾相比,王铎在书法创作上展现出更重的用笔力量和更大幅度的字形变形,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在长长的纵笔之中,枯笔与飞白交相辉映,神秘而充满活力。字的体势大多向左下方倾斜,如同从空中飞驰而下的飞仙,展现出一种动感与韵律。整幅作品都透露出一种兴奋与自如的气息,不受任何拘束,挥洒自如。
王铎草书的节奏感始于起笔的“蓄势”。其笔锋多以中锋裹锋入纸,如《秋兴八首》中“摇落西风”的“摇”字,首笔逆锋藏势,蓄力后骤然发力,形成“重若崩云”的起笔效果。这种起笔方式赋予线条以“蓄—发”的节奏对比,起笔蓄势与行笔的疾徐交替,正如马宗霍所言“纵而能敛,势若不尽”。
行笔过程中,王铎善用“疾徐交替”的节奏变化。例如“红树城边蝉欲断”一句,长纵笔如“蝉”字的竖画,行笔迅疾如风,枯笔飞白自然流露,而转折处(如“断”字右部)则骤然减速,以折锋顿挫形成“断金切玉”之力。这种快慢交替的节奏,既呼应了诗中“萧瑟”的意境,又暗含王铎对米芾“八面出锋”技法的理解与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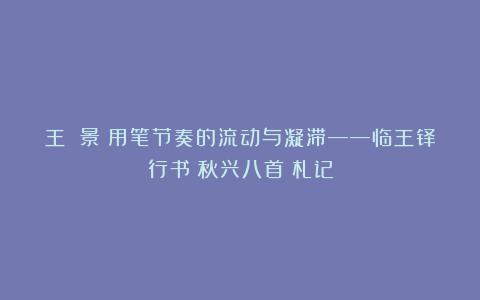
王铎用笔的提按幅度极大,提按顿挫的韵律化表达,形成强烈的视觉韵律。在《秋兴八首》中,单字如“白云天际雁初回”的“雁”字,主笔横画以重按起笔,提锋轻掠后复按收束,形成“一波三折”的节奏感;而“回”字的圆转则通过连续提按,营造出“盘纡回环”的动态,这种提按的节奏很好的强化了线条的骨力。
此外,王铎的“顿挫”技法独具匠心。很多三点水的字,皆以侧锋重顿入纸,随即迅疾提笔,形成“点如坠石”的爆发力。这种顿挫的节奏,既是对米芾“刷字”的继承,又融入了碑学的雄浑骨力,使草书兼具“狂”与“敛”的双重特质。
王铎的“涨墨法”与“渴笔飞白”在《秋兴八首》中形成了强烈的节奏对比,墨色虚实形成了对节奏的烘托。这种墨色由润至枯的渐变,不仅强化了空间层次,更在时间维度上延展了节奏的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王铎的“虚笔”处理亦暗含节奏玄机。如“夜静山楼吹画角”中“静”字的右部,以细若游丝的牵丝连带,与左侧厚重的笔画形成虚实对比。这种“无墨处求笔”的技法,使整体章法如音乐般疏密有致,张弛有度。
从章法层面看,《秋兴八首》的节奏感源于字组间的“断连”与行气的“摆动”。例如“关门峭壁月如霜”一页,前四字以字字独立、笔断意连的方式书写,至“月如霜”三字则突然连绵不绝,很多字组形成了“静—动—静”的段落节奏。这种布局既受米芾“字组”理念启发,又融入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的纵势,使通篇如交响乐章般跌宕起伏。
王铎对每行轴线的大幅度摆动,进一步强化了节奏的跌宕感。如“慷慨闻鸡挥剑舞”一行,字势向左下方倾斜,似“飞仙”凌空而降,而下一行又通过字组的右倾调整平衡。这种“险中求稳”的节奏把控,展现了王铎对空间张力的极致驾驭。
王铎的用笔节奏是情感的外化,临习时需体悟这种“以书载情”的深层关联——节奏的快慢不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心灵的震颤。 临王铎《秋兴八首》,须以“节奏”为钥,解其笔法之妙。从微观的提按顿挫,到宏观的章法布局,皆需在动态平衡中寻求“势”的延续。王铎以“纵逸而不失法度”的节奏语言,将草书推向“诗境与书境合一”的至高境界,为后世临池者提供了书法艺术表达的范式。
岁次乙巳四月廿一日
王景浅识于双凤西隅梦欧室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