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十三行》的书写时间虽无确切记载,但可推测为其艺术成熟期(约30岁后)所作。此时王献之已脱离王羲之书风束缚,追求“妍媚流便”的审美,且正值东晋士族文化鼎盛阶段,文学与书法高度融合。
作品内容节选自曹植的《洛神赋》,以洛神形象寄托对理想之美的追求。东晋文人偏好玄远超脱的文学题材,王献之选择书写此赋,既是对文学经典的致敬,也符合当时士族审美趣味。
王献之突破王羲之的“内擫”笔法(笔势内敛),改用“外拓”笔法,笔锋外展、线条圆润流畅,形成宽绰疏朗、俊逸潇洒的风格。
《洛神赋十三行》将真书推向精丽妍媚的高峰,点画细腻而不失力度,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韵律感贯穿全篇,是真书的极致表现。
《洛神赋十三行》标志着东晋真书的成熟,终结了以钟繇、王羲之为代表的古拙书风。
其外拓笔法和妍丽风格为唐代楷书(如褚遂良、颜真卿)奠定基础,成为晋唐书法承启的关键节点。
明代董其昌赞其“风流倜傥,无一点尘俗气”。
《洛神赋十三行》不仅是王献之个人书法巅峰的体现,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以外拓笔法和疏朗体势开创了真书新境界,既凝练了东晋士族的超逸风神,又为唐代楷书的规范化提供了美学范式。尽管真迹已佚,但通过历代刻本与临摹,其艺术生命力至今不衰。
洛神轻盈地戏水,左倚五彩旌旗,右傍芬芳桂旗。她挽袖露出皓腕,在洛水边采摘湍流中的玄色灵芝。我倾慕她的娴雅姿容,心中却怅然若失。苦无良媒传递情意,唯有借水波倾诉衷肠。愿以玉佩为信物相赠,盼她解我诚挚心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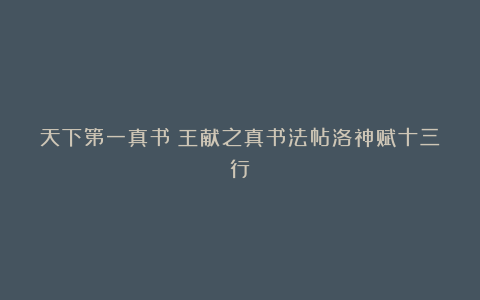
她果真德容兼备,既通礼乐又善诗文。举起琼玉回应我的心意,手指深渊相约佳期。我紧握信物忐忑不安,恐这神灵终将失信。忆起郑交甫被神女背弃的传说,不禁犹疑徘徊。收敛心绪重整仪态,谨守礼法自我克制。
洛神感应到我的情思,徘徊间身影若隐若现。忽如白鸐轻盈立起,似将翱翔却未展翅。踏过椒兰铺就的香径,行经杜蘅丛中暗香浮动。她引颈长吟遥望远方,清越之声愈发哀婉绵长。
众神闻声纷至沓来:或嬉戏清波,或遨游沙洲,采撷明珠,拾取翠羽。娥皇女英相伴而至,汉水女神结队同行。感叹女娲独居无偶,歌咏牵牛孤守星河。洛神轻扬纱衣临风,以袖遮面久久伫立,转瞬又如惊鸿掠影,倏忽隐没于碧波之间。
晋中书令王献之书
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捥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
心怅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託微波以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习礼
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拳拳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怅犹豫
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傍偟。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擢轻躯以
鸐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慕远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
灵杂逯。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姚。携汉滨之游女。叹
㚿娲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伫。軆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