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胜败乃兵家常事”。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敢说自己平生从无败绩的将军,也是寥寥无几。
但在我国近代史上,却的的确确有这样一个人,30年军旅生涯未尝一败。
他不仅是全军上下公认的军事家,其亲创三大战术,更让日军吃尽了苦头。
他就是,罗炳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一个陨落在曙光之前的将星。
在他身上究竟发生过哪些传奇经历?从未打过败仗的他,又是因何而亡的呢?
“神行太保”
上世纪70年代末,曾经有一部被广为播映的电影,名叫《从奴隶到将军》。
故事讲述了一个出生奴隶的少年,为了生存和活命参军入伍,一路从一个小兵成长为名震中外的不败将军的事迹。
而这个影片的主人公原型,正是罗炳辉。
罗炳辉本出生在云南彝良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生活穷苦,10岁时便被迫辍学。
由于自小受尽了地霸恶绅的欺凌,少年时的他便立志要“当兵报仇”。
为此他两次“离家出走”,历经了多番艰险,终于在18岁那年加入了滇军,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
随后,他又参加了北伐。并一路凭军功晋升,做到了团长。
但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内军阀争锋,竞相排除异己。
屡立战功的罗炳辉,竟丢了职务。
由此罗炳辉开始思考,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和民族的出路。
就在这时,他开始接触 到了“工农革命”的理念。并在1929年7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此后的罗炳辉,犹如雄鹰找到了翱翔的天空。
一次次的作战,他连战连胜,屡立奇功。
尤其在1930年10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罗炳辉更是创造出了令敌一个师片甲不还的传奇。
彼时国民党将领张辉瓒奉命指挥18师和新编的第5师,向东固一带进犯。
战役开始之初,敌军第5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进攻。
奉命驻守此地的罗炳辉部,一开始便故意一路示弱后退,致使敌人接连扑空。
但在后面压阵的18师,并不知晓先行部队根本没与我军发生实际遭遇。
在罗炳辉的故意误导下,随后而至的18师,误将己方的5师当作我军,来了场伤亡惨烈的窝里斗。
罗炳辉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步步牵着敌人的鼻子,将其引入了龙冈的埋伏圈,来了个瓮中捉鳖。
此战大获全胜。“18师片甲不还”的战绩,令敌我双方将领无不咋舌。
其中他一天内急行120公里,攻占两座县城的传奇,更让美国著名记者尼姆·韦尔斯也盛赞其为 “神行太保”。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金牛山上“梅花桩”
1930年,自龙冈一战,罗炳辉打响了自己“神行太保”的威名。
接连几次的反“围剿”作战,他所率领红九军团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数立功勋,被盛评“战略轻骑”。
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转入长征后,艰苦条件下,罗炳辉超高的指挥艺术,更是发挥的凌厉尽致。
他以2000人的兵力,对抗敌整整6个师的编制,却生生为主力红军南渡乌江,牵制住了围堵之敌。
在被称为世界奇迹长征中,罗炳辉建立了不朽奇功,成为了红军中名重一时的高级将领。
他“军事家”的名头,自此显露无疑。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但要说起他最被盛赞的传奇战术,还要说到抗日战争。
作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守卫者,罗炳辉的多谋善断,是根据地安稳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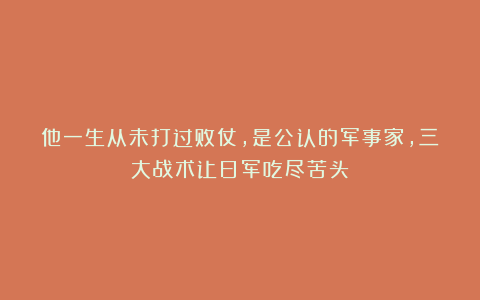
为了护卫根据地的安全,减少战士们的伤亡,经过多番构思和实践,罗炳辉打造除了一套全新的战术——“梅花桩战术”。
即把部队分布在几个相距两三公里范围内的地方驻守,点状分布形似梅花,故名“梅花桩”。
而该战术的第一次使用,是在六合县金牛山。
金牛山地理位置优越,四面山河环绕,十分适合发展有生力量。
1941年4月中旬,罗炳辉率兵进抵金牛山。
为了有效打击日伪势力,利用地形和战术,他将酝酿已久的“梅花桩”战术付诸实践。
首战便一举大获成功!击毙日伪军共计500余人。
不甘失败的敌人,一个月后又以数倍兵力卷土重来,对罗炳辉部发动第二次“大扫荡“。
罗炳辉再现战术传奇,诱敌深入“梅花桩”阵地。
战斗不过六七天,日军伤亡千余人,敌军官大为震怒的同时,也对罗炳辉的战术极为好奇。
但翻遍了中外史书,也没找到类似的记载。
只能气急败坏地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罗氏战术”。
战场之上罗炳辉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战术战略。
罗炳辉与张明秀夫妇
除了“梅花桩战术”外,他还根据不同的位置条件,创造了“麻雀战术”、“地堡战术”等等。
三大战术因地制宜,让气焰嚣张的日军吃尽了苦头。
将星陨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筹备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书。
在《军事篇》中,从人才济济的解放军指挥官中,评出36位“军事家”,冠以荣誉称号。
罗炳辉位列其中。
或许在“军事家”这个名头之下,人们往往关注的都是他的指挥作战能力。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从军三十年老战士,罗炳辉的单兵作战能力亦十分突出。
他是部队里声名远播的神枪手。
不仅可以打双枪,射击准度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既可以用单手举枪,射击几十米外树梢上的鸟儿。也可以百米之外打鸡蛋,而百发百中。
此外凭借惊人的臂力,平端重机枪的情况下,也可以瞄准目标长达20分钟。
据记载,某次作战中,他用一支步枪,单枪匹马便封锁了敌人进攻的一个路口,掩护部队转移的同时自己也全身而退。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除此之外,战场之下的罗炳辉,却是一个爱兵如子的好领导。
不仅常年坚持与士兵同地而席,同锅而食。每次到各连视察,必定要到伙房检查战士们吃的食物好不好,有没有吃不饱。
每有伤员,也一定会叮嘱炊事员,给伤者开小灶,关照受伤战士的情况。
但在治军时,又极其严明。训练也异常严格,绝不允许偷奸耍滑。
因为在他看来,“战场乃立尸之地”。训练时不严格,战场上付出的就将是血淋淋的代价。
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刻,我们彷佛看到了中华大地上,又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然而常年作战,艰苦的条件严重损害了罗炳辉的健康。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高血压。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
本已经组织批准,即将前往苏联治病疗养的罗炳辉,毅然决心留下来协助陈毅转战山东。
是年6月初,枣庄战役打响。
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罗炳辉不顾每况愈下的身体,告别妻儿毅然奔赴前线。
6月中旬,枣庄胜利解放的捷报传至后方,全军振奋。
但罗炳辉却昏倒在了前线指挥所,并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心脏停跳,永远地离开了。
就像他在战前的日记中记述的那样,毕生从未一败的他,以生命完成了对“党的最后一次献礼”。
将星陨落,光辉永存。
参考文献:
1、罗炳辉:一生从未打过败仗,大众日报,2021-08-18
2、罗炳辉:“三大战术”显威力,人民政协报,2024-11-20
3、“神行太保”罗炳辉,北京日报,2014-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