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的十月,苏轼被贬黄州后,“杜门谢客”,冬至后又去天庆观养炼。毫无收获的他,写以菩萨蛮,填了回文四时闺怨词,自我消遣。
回文诗,据说起源于前秦窦滔妻子苏蕙的《璇玑图》,因回环往复均能成诵而得名。苏轼被贬黄州,初期的迷茫,到中期的通透,他的的心境变化,诗词是最好的见证。苏轼的《四时闺怨》比《定风波》早了大约两年,风格异,他的心路历程,尽在词中。
这四首回文四时闺怨词,以回文形式为皮,以道家自然观为骨,在传统的闺怨体裁中,开辟一片超然的新天地。苏轼告诉我们,文学的真境界,在于心性的通透,而非题材的宏大;在于返璞归真的真诚,而非技巧的繁复。恰似《菜根谭》的观点:“乾坤妙趣,天地文章”。
他的另一首写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创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即苏轼贬居黄州的第三年,此时的苏轼,已逐渐适应贬谪生活,躬耕东坡,心境趋于豁达。
《菜根谭》说:“长袖善舞,多钱能贾,漫炫附会之伎俩;孤槎济川,只骑解围,才是出格之奇伟”。苏轼以闺怨题材为媒介,将政治失意转化为诗词创作,恰与其中意境相似。
回文四时闺怨词,恰是苏轼从“文字解闷”到“心性通透”的转折点。才刚摆脱牢狱之灾的他,受伤的心,尚未平复。此时的他,尚需借助文字游戏转移苦闷。
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四首菩萨蛮,感受苏轼排解郁闷的消遣之作,看他如何在困境中自救。
菩萨蛮回文春闺怨
苏轼 宋代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
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
菩萨蛮,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名。又名“菩萨篁”、“重叠金”、“花间意”、“梅花句”等。上下片各四句,均为两仄韵,两平韵。
上片以指代手法,写暮春时节昏睡的少妇,由发式之美写到耳垂之美,由耳幔的美,写到秀发的美,再到整体的美。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女子梳着环形发髻,幔,意为遮盖,又有帷幔、帷帐之意,云,女子美而长的头发。”云”字一语双关,既指女子的鬓发美如云,又暗含思绪缥缈无依之意。这两句回文,形成空间闭环,暗示女子困于深闺,词语反复中,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
“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暮春困倦,昏沉欲睡。而春天,也在昏睡中渐行渐远。词中,美人昏睡的图画,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此处回文,将春色将尽与慵懒的心绪交织在一起。唐代吕岩在《大云寺茶诗》中曾写道,“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人肌肤”,与苏轼词中的韵味颇为相似。
下片以心探手法,写暮春时少妇的愁思。“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梨花如雪般易碎,随风飘零。此处回文,”坠雪”与”梨花”互换,花瓣与飞雪意象交融,暗喻青春易逝,伤春之人,思念纷飞。”梨雪”一词,让春闺怨笼罩一层哀愁。
“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女子轻蹙蛾眉,所思何人?自问自答的回文,道尽相思无解的怅惘。苏轼以文字为丝线,将女子的情绪织成一张网。空间上,闺阁景物,正反皆可入画;时间上,春日将尽,昼夜昏沉,无尽的思念与惆怅,与即将离去的春天,隔空对话,互相映衬。
每一组回文,不是单纯的语言游戏,而是情感的双向流动。反复吟诵诗句,字句颠倒间,写出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韵味。如果说,前句的落点为物、为景,那么,第二句的落点,也许是人,也许是情。由景物渗入人情,回环往复,正是苏轼的用意所在:乐从趣生。
苏轼的这首《回文春闺怨》,宛如苏州的双面绣。正面,是一幅闺阁工笔图,背面,是用淡墨写意的离愁别绪。苏轼以回文为舟,载读者渡入春愁深处,见天地,见众生,终归于,女子那一抹欲说还休的哀愁。
菩萨蛮·回文夏闺怨
苏轼〔宋代〕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苏轼的这首“夏闺怨”,上片写昼眠情景,情景交融,闺中少女夏日的生活,跃然纸上。“柳庭”二句,突出一个“静”字,上句写“风静”,下句写“人静”,清新唯美。风静时,庭柳低垂,女子困倦而眠。女子昼眠正熟时,清风起,吹拂庭柳。
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识天地自然鸣佩。这种物我交融的意境,恰与苏轼《夏闺怨》中“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的回文结构,不谋而合。不仅形式精巧,更以“风静”与“人静”的互动,展现了动静相生的自然韵律。“静中见动,动中有静”。
风吹香汗,薄衫生凉,凉衫中,依稀透出女子的汗香。“薄衫”与“薄汗”的变化,以“衫”之薄,点出“夏”意。此处风韵,耐人回味。以一“凉”字,串起夏闺昼眠的形象。过片二句,“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是女子睡醒后的活动。
她用红润的手,拿着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这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冰了她那红润的手儿。上句的“冰”是名词,下句的“冰”作动词用。古代,人们常在冬天凿冰,藏于地窖,留待夏天解暑之用。杜甫曾有诗“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与苏轼词中的意境颇为相似。
“长丝藕笑郎”,一语双关。”藕丝”谐音”偶思”,明写藕断丝连,实则暗喻情思缠绵的人间情愫。“藕丝长”,象征情意绵长。《读曲歌》写道:“思欢久,不爱独枝莲(怜),只惜同心藕(偶)。”
词中”郎笑”,与”藕笑”对应,透露出恋爱中男女微妙的情感。这笑声,似有调笑之意,所以女子才会报以“长丝藕笑郎”之语。笑郎,或许是笑他的不领情,不识情趣吧。情意不如藕丝长,这才是“闺怨”的本意。
纵观全词,苏轼以垂柳、薄衫、红手、冰藕等意象,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清凉的夏日画面。以”香汗”、”凉衫”、”冰碗”的对比,暗示人物的心境。又写风静人眠,以无声反衬内心的躁动。
苏轼的这首闺怨词,突破传统闺怨题材的悲情色彩,以游戏笔墨展现文人雅趣。回文与情感交融,是回文诗词中难得的佳作:形式美与意境美完美统一,堪称典范。
菩萨蛮·回文秋闺怨
苏轼〔宋代〕
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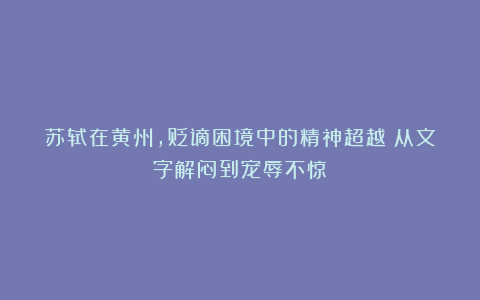
苏轼的这首秋闺怨,回文设计堪称天衣无缝。”井桐”与”桐井”意象互换,”新妆冷”与”冷妆新”情感反转,既保留了词意的连贯,又通过视角转换深化了意境。这种回环,将闺中女子的愁思,折射出千般愁绪,万般无奈,形成”愁肠百转”的意境。
词的上片,运用象征、寄寓手法,写了少妇见物动心的“愁”情。“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以深井梧桐,暗示女子深锁闺阁的孤独。南朝梁王训在《应令咏舞》中说,“新妆本绝世,妙舞亦如仙”,与苏轼词中的意境,异曲同工。
“双照”指月影成双,与形单影只形成对比。井中倒影,不过是女子自怜自伤的虚幻之花。”羞对”与”对羞”的回环,将物我交融的愁绪推至极点。苏轼将象征萧瑟的“梧桐”,与象征美女的“新妆”,放在一起,互相映衬,形成树与人的共鸣。
“梧桐”与“新妆”的对比,为了突出少妇的感叹,时光易逝,青春不再,她因此“愁”思满怀。“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从“梧桐”照秋,写到“井花”愁秋。从“井花”愁秋又写到少妇“对羞”。花与人对话,仍是为了突出少妇的伤感,秋色衰败,春心消融,“愁”思绵绵。
词的下片,少妇夜思郎君却不归,字里行间,都是自嘲的意味。“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从“影孤”到“孤影”,从“夜永”到“永夜”,可见少妇夜思之漫长。一个“怜”字,贯穿始终,让人动容。江南才子周邦彦,曾在《倒犯·新月》中说,“徘徊处渐移深窈,何人正弄,孤影编趾西窗悄”。两首词中徘徨不安的情态,是那么相似。
“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少妇秋夜思君,其深沉的心态,被描写得淋漓尽致。“楼”与“秋”互不兼容,楼已横秋,人何须眺望,一语双关。全词以象征、双关的手法,将微妙的情愫写得含蓄不失内涵。
细节处见真情,“桐”、“井”、“花”、“楼”,苏轼从细节着笔,将少妇“永夜”孤影的寂寞感和愁苦,写得深入人心,让人动容。
这首《菩萨蛮·回文秋闺怨》,写出女子秋日闺怨的缠绵情思,全词八句两两回环,形成音律与情感的往复之美,堪称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回文体的典范。
菩萨蛮 回文冬闺怨
苏轼 宋代
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
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
苏轼的这首《菩萨蛮 回文冬闺怨》,上下片各自形成独立的回文系统,每两句构成一组对称,通过语序的逆转,诉说季候轮回的永恒,突破传统叙事的局限。每一组回文,都似一面铜镜,一面是现实,一面是回忆。
既保留了冬日闺阁的视觉温度(雪花与香颊的冷暖交融),又暗含了时间的循环性——飞雪与融雪构成永恒的季候轮回。这种结构创新突破了线性叙事的局限,将女子等待的焦灼感置于时空旋涡之中,每一组回文都似一面铜镜,正照是现实,反照是回忆。
词的上片,苏轼以烘托的笔法,写少妇在暮冬时节盼郎君归来的情景。她站在雪地里,忍受着严寒的侵袭。“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点明女子盼望郎君的时令、气氛与环境。漫天飞雪扑面来,反觉雪暖了脸,脸融了雪。
冷与雪,原本不可变暖,却因人的不同心境,被赋予人情,雪有人情,人有真理,物随人变。“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直写少妇身穿单衣,冒着严寒,等待的心,从未动摇。一“欺”,一“任”,将坚贞如一的精神,描写得丝丝入扣。
词的下片,苏轼以回忆与推进相结合的手法,进一步展示少妇思念郎君、盼君归来而未至的心态。“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回忆里那些甜蜜的岁月,当初离别时的美好,历历在目。“梅子”,表面写少妇与郎君离别时的时令,实则暗喻他们爱情与青春。
“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这两句写出少妇难言的隐痛。此时此刻,在她看来,只要夫君归来,她不会嫌弃梅花开晚了。对她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梅花开了,果子结了,夫君却依然没有回到她的身边。
“恨”中饱含几分真情,“恨”中平添几分情趣。可谓牵肠挂肚,刻骨铭心,“恨”思绵绵无尽期。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将苏轼黄州时期称为”谪居者的精神涅槃”,这一视角恰可解读《四时闺怨》的创作动因。结合文本与林氏观点,苏轼以闺怨诗自遣的背后,实为三重精神突围:
乌台诗案后,苏轼曾感慨,”平生文字为吾累”,但以他的为人,不可能不作诗。闺怨题材,恰似政治审查的”防弹衣”,是他在黄州初期最合适的选择。
《冬闺怨》里,他以男女相思,暗喻君臣遇合。”归不恨开迟”,暗含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对待召还朝尚有期待。
《秋闺怨》里,他以”楼上不宜秋”,隐喻”高处不胜寒”的仕途。“闺阁空间”,或许是他正在面临的“政治困局”。《春闺怨》里,“颦浅念谁人”,或许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形式。
苏轼的回文四时闺怨词,看似香艳的游戏笔墨,实则是他以文字搭建的”精神防护堤”。有了这层“防护堤”的保护,让他免受政治风浪的侵蚀,又为两年后《定风波》的精神超越,积蓄能量。
其实,苏轼的这四首自我消遣作,本质上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戏剧”。他的孤独,无人能懂。
初到黄州,苏轼在自己的农舍里,为天地展示自己的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