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围
我们被水围困,
在高原与海的夹缝里,
刻下同一道暗流。
雪水从指间滑落,
像未写完的信,
沉入东江的闸门。
马家窑的陶纹,
在东莞的混凝土上,
长出新的裂痕。
祖先的骨殖,
在电站的轰鸣里,
碎成光斑。
我们测量水位,
用沉默的标尺,
却量不尽
上游与下游的债。
水围住我们,
像未拆解的谶言,
在入海口,
我们终于学会——
用咸涩的方言,
交换体内
淤积的沙。
■ 寒溪河:一尾鱼正游向深处
水纹在片岩上刻下五十九道年轮,
一道年轮,一道停泊的绳痕。
当汽笛代替了橹声,
你收拢七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倒影,
像母亲叠起泛黄的船票。
砂石厂在左岸吐出乌云,
新楼盘在右岸练习站立。
唯有你依然平躺,
让起重机在脊椎上,
寻找古河床的穴位。
水葫芦的紫色王冠时沉时浮,
塑料瓶在漩涡里练习空翻。
突然,一尾鱼刺破油膜,
向深处游去——
它闪亮的鳞片,
正把水下的天空,
焊成完整的盾牌。
■ 大岭山
松涛在账簿背面醒来,
数字的根须,扎进钢铁的脉搏。
荔枝林间,未熄灭的炉火,
锻打一把钥匙,通往东江的黎明。
而历史是哑默的秤砣,
沉在游击队的枪膛里。
脚手架在云端写诗,
每个焊点,都是星辰的标点。
流水线搬运光的碎屑,
工装服裹着未冷的月光。
而风穿过马山的石刻,
把经文,刻进我们的骨头。
祠堂的香灰落下时,
新漆的货柜正驶向大洋。
孩子们用拼音拼写“岭”,
而岭外,仍是岭——
我们以齿轮的耐心,
在每道焊缝里,埋下潮汐。
■ 银瓶山叙事曲
一、攀登者说
石阶把云雾钉在峭壁的宣纸上,
我们带着心跳的铅锤攀登——
每一级都站着年轻的自己,
用松针数着褪色的诺言。
二、高度志
海拔计在爆石顶失效,
紫烟阁正用飞檐收集星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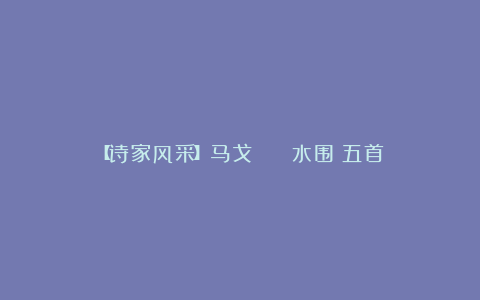
有人把名字刻在观景台,
比青苔消失得更快。
三、山风抄
松涛在翻动未写完的信笺,
山雀突然噤声——
整座山开始侧身,
让落日滚过茶林径,
像枚熟透的野果坠向三坑水榭。
四、等高线
此刻我站在898米的逗号上,
看自己的影子被拉长成破折号。
飞鸟用翅膀称量群山的重量,
而云雾的橡皮擦,
正在修改清溪与谢岗的边界。
五、紫烟阁记
这座木结构的天空收容所,
把月光铸成新的海拔计。
当薄雾淹没清峰路标,
有人用枯枝在台阶写道:
“所有高度都是租借的——
除了深渊,
我们什么都不配占有。”
六、下山辞
现在整座山开始退潮,
石阶松开咬住鞋底的齿。
回望处,
紫烟阁正把晚霞,
装订成峰顶的最后一章。
■ 双湟书:高原与潮汐的凝视
我们切开同一枚果实
在两种季风里辨认齿痕
高原的雪线垂落成水闸
而三角洲正收集每一滴
不肯坠落的黄昏
那命名的沙粒不断迁徙
从马家窑陶罐的裂纹
到客家围屋的砖缝
我们共用同一种干渴
在县志的夹层中
豢养暗哑的河神
水利枢纽的探照灯下
祖先的骨殖泛起磷光
他们用淤积的方言争执——
关于梯田怎样爬上云端
又怎样在发电机组里
碎成齑粉
我携带整个上游的寒意
在混凝土堤岸上刻写
水纹的判决书:
当东江吞下最后一片月光
湟水会在它胃里
找到未消化的星群
两个母亲河互相哺育
用倒影缝补断裂的海拔
在入海口 盐的遗嘱里
我们终将学会
用咸涩的舌头
亲吻彼此身上
所有未完成的河床
2025年4月 东莞
广东诗人(gdsr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