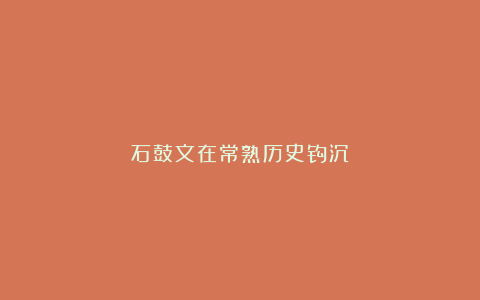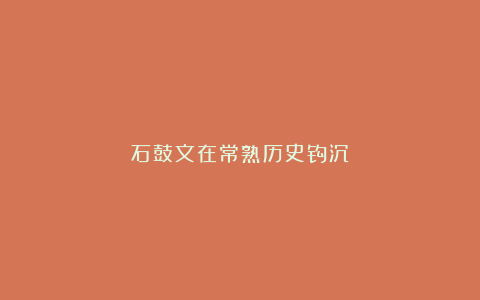|
文 / 归之春
常熟是以篆书闻名的书法之乡,杨沂孙、萧退庵等尤擅石鼓,并对其临摹、研究、传承,今述其往事,以专题补地方史志之缺失。
明代汲古阁毛晋(1599-1659),字子晋,子藏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写本廿卷,中有石鼓文摹钩本,书的前后页均有“汲古阁”及“黼季”印章。毛晋子毛扆殁后家道衰败,书亦散失。
常熟人毛晋,是我国私人藏书和刻书业的代表性人物,他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汲古阁。毛晋穷尽家财献身于书籍事业,出版了大量丛书,使得许多宋元善本赖以传世,刻印的《六十种曲》,使得众多戏曲传奇剧本可以留存,为我国典籍整理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康熙年间,邑人陆亮(字友桐),善抚琴吟诗,尤长于书,临摹众体皆入妙。
偶在市肆中获观汲古阁南宋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写本廿卷,“因索价甚高,贫不能致”,遂与侄晖山“篝灯抄录,凡十昼夜而成帙”。
后在石城(今江西石城县,邻近福建)获髯翁田志山之“燹余旧本”,进行填补,校其伪谬,并录序跋传世。
集中有宋拓石鼓文摹本,及薛之释文。后称《陆亮石鼓文摹校本》。上署“康熙五十八年乙亥(1719)虞山陆亮(友桐)记”字样。
清蒋廷锡(1669-1732),江苏常熟人。字扬孙,一字酉君,号西谷、青桐居士。御史蒋伊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俗称蒋阁老)。
承家学,工书,善画。未第时,与马元驭,顾雪坡游,以逸笔写生,风神生动,点缀坡石水口,无不超逸。为官后,矜重不苟作。因此,流传极少。
家藏《考古图》十卷(宋吕大临撰,元罗更翁考订,明刻本)(见《翁同龢书跋》)。
蒋氏与礼部侍郎凌绍雯等同任《康熙字典》纂修官,历时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成书。字典辑有部分石鼓文注释。惜错误甚多。
清乾隆时,常熟铁琴铜剑楼第一代藏书家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堂,常熟古里人,清贡生,曾署阳湖县(今江苏常州)训导。
喜藏书,精校雠,对版本目录、尊彝古玩、金石文字辩析精当,与常州金石文字家孙星衍(1753-1818)交往颇多,孙氏亦喜藏书与金石文字之学,孙为题“铁琴铜剑楼”篆书匾额,落款为“篆请荫棠师台大人正画,伯渊孙星衍”。
孙星衍亦爱好石鼓,有《石鼓摹刻书跋》,定石鼓为周宣王(前827-前782)说。
在铁琴铜剑楼《碑拓目录》中,有未经割裱之整张全拓石鼓文,是顾千里收校的乾隆拓本,上有何元锡、叶志诜、龚自珍题跋和何元锡鉴藏印。
据《石鼓歌》,称乾隆拓本所载石鼓字:“字传三百三十四,其余齿缺难推详”。距北宋拓本四百五十六字,已远远不及矣。
晚清常熟人杨沂孙(1813-1881)官安徽凤阳知府,善书法篆刻,爱篆籀之学。初师邓石如,后以金文、石鼓、汉碑出,笔画圆润,结体方正。著《文字解说问讹》《在昔篇》等,成为清代杰出书法大家。并作《石鼓文赞》,开常熟临石鼓书法之先河。
余藏有杨沂孙篆书《汉蔡邕书熹平石经记》,后署:光绪三年(1877)五月长至濠叟杨沂孙篆,下钤“子与”(白文)、“吉羊之室”(朱文)印两方。
前有“历劫不磨”朱文起首印,是民国时期的石印本字帖,为徐市板桥居士归凤乔所赠予。归凤乔是余之家叔,他八十岁时还录康有为题石鼓文句为拙书《石鼓文三百字注》题词。
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一字伟甫,号能静居士。原籍江苏阳湖(今常州),后定居常熟。少时有文誉,讲求经世之学。
曾入曾国藩幕府,历任直隶(磁州、易州)知州,后引疾归,爱常熟山水,在城西购得吴氏水壶园(又名水吾园),后称赵吾园,园中有静溪,并筑天放楼以藏书。
嗜金石文字,曾邀苏州古文字学家、金石藏家吴大澂(1835-1902)游虞山,研讨金石。
吴绘有《静溪图》(现藏常熟市博物馆)志记。赵著《畿辅金石略》,以天一阁本为据,集宋薛尚功、郑樵,元阮元、潘迪,清朱彝尊各家石鼓注释,成《石鼓文纂释》。
此书扉页署有“光绪岁旃蒙作鄂(即乙酉十一年,1885年)静圃刊版”(“静圃”是赵吾园之门额题字)。并著《能静居日记》。(注:《尔雅》释干支:“太岁在乙曰旃蒙”,地支酉称“作鄂”,鄂亦作噩。)
常熟虚廓园,今称“曾赵园”,是曾朴父亲曾之撰于光绪七年(1881年)筹建,光绪二十年(1894年)落成的一个私家园林。它的幽深和疏广,曾经成为清未、民国年间江南的一个名园。李鸿章、翁同龢等名人都为它留下了墨宝,吴大澂为之题名。园主刑部郎中曾之撰将数十位当朝权贵为虚廓园的题名题诗,刻石列于园内长廊。
吴大澂辑《说文古籀补》初刊于光绪九年(1883),有潍县陈介祺《序》,书中“济”字处,载绘图币晚周文字,未录石鼓文“济”字。
溧阳强运开在吴大澂、丁佛言之《说文古籀补补》后辑《说文古籀三补》,在“济”字条补录石鼓文“济”,并说“按无锡安氏十鼓斋北宋精拓第一本,’济’字甚为明显”(即《先锋》本)。
说明吴大澂、丁佛言在世时均未见此《安国本》。赵烈文自亦未见。
与赵烈文同时代的赵重撰有集石鼓文楹联赠晚清名医余景和(听鸿)曰:“君子不平则鸣,好花滋雨始放”。其下联误将“济”字作“滋”字用,“放”石鼓无,或是“”(微)字之误。
图1:1913年孟秋,吴昌硕为常熟城区西门致道观右侧的大门作篆书匾额“逍遥游”三字
清末著名的石鼓书法家吴昌硕(1844-1927)常来常熟,与藏砚名家、诗人沈汝瑾(字石友,1858-1917)订有金兰之交。
吴常榻沈处,观看沈之藏砚,共同品砚、作铭、题词。后集拓成《沈氏砚林》一部,前有吴昌硕诗序。
藏砚中有“缶庐自写七十一岁小像”砚一方,下有“昌硕”小印。砚侧有沈汝瑾作砚铭“行方智圆是端友,廉泉一勺千万寿,文字之交可长久”,有“沈”小印。
1913年孟秋,吴昌硕曾为常熟城区西门致道观右侧的大门作篆书匾额“逍遥游”三字(图1),并留有集石鼓文楹联“深渊求魚大罟所载,平原射虎硕弓自鸣”藏常熟市博物馆。(图2)
赵石(1874-1933),字石农,号古泥。青年时经沈氏推介,拜吴昌硕为师学篆刻。得吴之亲授,艺亦精进。赵石在刻砚、习印之间,亦临习石鼓,并引韩愈《石鼓歌》句,刻“才薄将奈石鼓何”印以自歉。其篆刻字法中“人”写作“”,即源自石鼓页字旁的下垂之笔。
赵石与蒋志范(1867-1952)善。赵殁时蒋先为作《赵古泥先生传》。蒋氏号鄦楼老人,好古文字学,受知于长沙古文学家王先谦。受聘于上海同济医工学校,教授十年。著《清朝逸史》《石鼓发微》,释石鼓文为陕字,主张石鼓为“秦昭王时物”。(见钱仲联编《学海月刊》1944年第1、2期)
金鹤翔(1864-1931),字幼香,号病鹤,江苏常熟人。清末参加南社。辛亥革命后发起成立常熟虞社,任名誉社长。也发起组织梅社。
工诗词,著《病鹤诗稿》四卷,《词稿》一卷。并藏有《石鼓文考》抄本一卷(今藏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审其注释,沿袭清代前人旧说,并无新意)。
民国时期誉满江南的常熟书法家萧退庵(1876-1958),四体皆精,尤擅篆书。他说:“篆书贵圆转自如,贵柔中有刚,贵结构紧凑。必须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又说:“大篆中石鼓最难写,因字形方,笔画短,笔画短的难写。”
其所书《石鼓编句》,书体柔而方。有副石鼓楹联“百花开处松千尺,众鸟喧时雀一声”,联中的“花、处、众、时、一”等字均是石鼓文,书体见方。
另一副石鼓文楹联“平子歸(囿)樂我道趍,翰公好古辞如天章”,(图3)却写得略长而刚,大概是因时而异,顺势而为,耐人寻味。
约1950年,我在常熟城内,曾遇见萧退庵先生,他戴着黑边眼镜,留着胡子,身穿棕褐色和尚服。后来他迁居苏州,由于工作忙,无缘拜访。
萧氏家藏清乾隆时拓石鼓文未裱纸本全张九幅(缺乙鼓),下角钤“迦楞收藏”印,无序跋,余亲见之。萧氏著有《小学百问》、《文字学浅说》。
1989年,冷延梅编辑《萧退庵书法选》,前有柳曾符《江南大书家萧退庵》一文,内有萧氏石鼓文编句、楹联及篆隶行楷四体书。篆书释文是冷延梅嘱我所作。全书资料为萧退庵媳瞿明婵女士提供,高鹏摄影。该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我师邓散木(1898-1963),篆刻师赵石,书法师萧退庵,自称“二十七岁见萧退庵先生,始闻书法大道”。
萧氏曾对邓说:“吴昌硕石鼓有霸气”,因此,邓师不学缶翁,所写石鼓书体柔而遒劲,从萧退庵出。
邓说:“石鼓要学《安国三本》”。著有《厕简楼授课稿》(《篆刻学》)、《石鼓斠释》等。
赵古泥的弟子邓散木,中国现代书法家、篆刻家,在艺坛上与齐白石并称,有“北齐南邓”之誉。
评弹艺人黄异庵(1913-1996),亦作怡庵、易安,原籍太仓,定居苏州。是邓散木最早弟子。
并为拙著《石鼓文赏析(初稿)》作石鼓诗“千载高吟石鼓词,字多残缺义难知,归生赏析书成日,安得韩公笑读之”。后钤有黄老晚号“了翁”小印。
常熟市博物馆藏有近现代名人正、草、篆、隶楹联二十多副,其中有集石鼓文楹联四副。
除吴昌硕外,尚有原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字雅辉,1865-1953)作集石鼓文六言联“王右丞多古趣;吴道子夺(获)天工”。(夺是获之误);苏州吴县人吴起(字子云,号云壑,1873-1955)作集石鼓文八言联“右辔左车吾马一出,柳阴花氐(底)多鱼是求”;浙江西泠印人马公愚(号冷翁,1890-1969)作集石鼓文七言联:“执弓鸣勒射麋鹿,载舫维舟写柳杨”(“维”与“惟、唯”通)。(图5)
篆刻、版本学家庞士龙(1899-1987),字云斋,常熟人。其父庞裁,擅画兰,篆刻学林皋。云斋受家学之薫陶,爱篆刻,中年学丁敬、黄易,晚年学赵古泥。唯印章边栏不求残破。家富收藏,亦爱石鼓,曾将1919年上海艺苑真赏社刊《石鼓文甲本》影印本(即《中权本》)给我浏览。庞氏对石鼓年代考之观点,与我有别,他笃信昆山顾炎武(1613-1682)著《金石文字记》引《金马定国传》之《石鼓考论》,云是“宇文周所造”。
言恭达,字公达,一字巩达,常熟人。青年时,师从苏州沙曼翁(沙氏是萧退庵弟子),善篆刻兼篆隶,后以草书出众。巩达篆刻心追秦汉,刀痕较浅,求古朴,篆书有萧氏风,临习石鼓亦遒劲。任常熟书画院院长时,从者甚多。并为我石鼓文著作初稿题词“石鼓文赏析”,有萧氏书风。
余之亲友陈炜湛先生,1957年江苏常熟中学毕业,入复旦大学,毕业后从容庚、商承祚,后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年著《甲骨文简论》,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学术著作三等奖。是甲骨文专家,对石鼓文亦有研究。与唐钰明合著《古文字学纲要》。晚年归里任常熟市甲骨文学会顾问,在甲骨文学会某次学术论坛中说:“在学术研究中是不能不要传统、不要继承的”。他考证《诅楚文》唐以前不载,是唐宋时代之伪文。
此外,篆刻家蔡绍心(1921-2013),号石奴,篆刻私淑赵古泥,1992年任虞山印社首任社长。生前亦写石鼓,唯腕力较弱。(图6)
在常熟城乡,凡学篆刻写篆字的爱好者,均习过石鼓。常熟梅李的老中医王天如(1922-2000),也是常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临写的石鼓,多次参加省市级书法展览,深受好评。
曾集石鼓文楹联有“阴阳之道何硕大,朝夕其中有作为”“余(斜)阳射古柳,微雨湿黄花”“鱼乐渊中阳天嘉日,人游原北流水彤花”(图7)。
王先生与我交流石鼓文书法,盛赞我“石鼓如秦之陶量”之论说。
由徐克明、徐梅勋合辑,张浩元题签《常熟古今对联集粹》,载有集石鼓字联“古人唯大同谓治,君子以中庸为归”;咏柳如是回文联“人中柳如是,是如柳中人”。并辑有余90岁前所作集石鼓字联“康乐人真是康乐,平安里敬祝平安”。
余生于常熟徐市镇,十六岁学篆刻,在小学老师程飞白的父亲程星午书斋中,第一次见到清末冯云鹏辑的《金石索》,共十二卷,《金索》六卷,《石索》六卷。在《石索》中,有《石鼓文》木刻摹本,虽是偶然,却得到启发。此后在读书、拜师、学习书法篆刻、工作与社交活动中,勿忘收集石鼓文资料。
藏品有顾从义刻“石鼓砚”影印本,吴大澂、吴昌硕、邓散木、罗君惕、易越石等研究石鼓的著作,郭沫若著《石鼓文研究》及上海艺苑真赏社《周石鼓文》(甲本)等各种石鼓拓本出版物十多种。
经过多年摩挲著录成《石鼓赏析》初稿,曾取室名为“石鼓赏析之斋”。在此基础上,把前人的研究注释进行比较推敲,纠其误并补其缺,成《石鼓文三百字注》,2004年10月在香港出版。
发行十多年来,却未见有人评述,奇哉!唯西泠印社诗人篆刻家叶一苇(1918-2013)看了拙著《石鼓文三百字注》后作诗云:“大篆从来崇石鼓,其文难读时为苦。归翁力大超九牛,为我驱除纸老虎。”(图8)叶老著《篆刻丛谈》《篆刻欣赏》等,于95岁时逝世,惜哉!但我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等待可有新的出土文物,再作新的论证。
钱仲联老师曾说明刻本《铁网珊瑚》有石鼓文。惜此书难得看见。
脉望馆赵琦美(1563-1624)得无名氏残稿《铁网珊瑚》。据赵琦美跋称:“原从秦四麟家得《书品》《画品》各四卷,后从焦竑得一本,卷帙较多,经两本互校,增为《书品》十卷、《画品》六卷,其先后次序,则赵琦美所隲定,而又以所见真迹续于后。”(书佚)脉望馆在城区南赵弄10号。
归曾熙(?-1936),字止庵,号帚庐,常熟人。性嗜书,喜搜访秘籍。购得汲古阁藏明代朱存理辑《铁网珊瑚》钞本,分《书品》八卷、《画品》五卷、《石刻》一卷,共十四卷。
毛氏收藏时,衬以皮纸,装十四册。两页骑缝及连合处,钤有“汲古阁”朱印,每本首尾均有“毛子晋印”“毛晋私印”“毛扆之印”“斧季”等印。
毛晋曾撰《铁网珊瑚歌》以纪之。此钞本曾被姚宫詹所藏,后为毛氏两代珍藏。
归曾熙获得后即名其藏书室为“宝珊瑚阁”,赵古泥为刻“宝珊瑚阁”朱文印一方。并成《铁网珊瑚歌》一集,有徐翰青等题咏。歌中感叹:“从来尤物多幸得,因缘种种莫揶揄。但祝此书在天壤,水火劫厄永永无!”
1937年日本侵华,常熟沦陷,归氏第三子启丰将《铁网珊瑚》《丁卯集》等书携至沪上,其余藏书均在战乱中散佚。《铁网珊瑚》钞本曾辗转流落香港,后为北京图书馆收藏。
常熟人周文在(1906-1994)将军,1987年将家藏古籍二十余种捐赠给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
其中有《铁网珊瑚》明万历刻本一部,计《书品》十卷、《画品》六卷,包括目录在内,分订二十册。
无书名题签和序,无收藏印(疑已失去卷首与卷尾数页)。《书品》卷一目录有:石鼓文、兰亭定武本、二王墨刻和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真迹条目(无石鼓文摹本)。
开国将军周文在(1906-1994),江苏常熟人,1925年入党,1926年初与李强(曾培洪)一起建立了常熟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同年夏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5年和王志平一起被捕,1938年和王志平在常熟东乡创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六梯团。1955年被授予少将,是常熟乃至苏州地区唯一的(1955年授将衔)开国将军。
《书品》石鼓文刻载明赵古则(1351-1395)撰《石鼓文序》全文,文章较长。序文起句感叹:“乌乎!三代之文字之存于金石者,惟禹之’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三代,指夏、商、周时期。所谓“史籀石鼓”,是说石鼓文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传承了唐韩愈《石鼓歌》“宣王愤起挥天戈,……蒐于岐阳骋雄俊”句的误导。
《容斋随笔》评说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通周宣王事,伟(违)矣”。《左传·昭公四年》把“成(成王)有岐阳之蒐事”,说成是周宣王,实是误也。
评涉石鼓的年代,引北宋郑樵之说:“谓是秦篆,因其以’殹’为’也’,见于秦斤;以’’为’丞’,见于秦权。其次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为帝,亦可为王。秦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以惠王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亦有《金史·马定国传》北周说之记载。
对石鼓诗的解释,均引自《诗经》之《车攻》《吉日》。
如《车攻》曰:“四牡庞庞,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盖即石鼓“六马”“四马其写”之谓也。
又曰:“吉日维戊”“吉日庚午”,即“日维丙申”之谓也。曰“田车既好”“田车既安”,即“田车既安”“我车既好”之谓也。
再曰“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即“秀弓时射,射之族族”之谓也。
《诗经·小雅·车攻》和《诗经·小雅·吉日》是记述周宣王东巡洛邑接见诸侯及沿途打猎的情形,歌颂车马装备精良,纪律良好,射御技术高超,以及此行获得的巨大成功。如《诗经·小雅·车攻》首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石鼓《车工》篇首句:“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完全相同。至以《诗经·小雅·吉日》的“吉日维戊”“吉日庚午”与石鼓《吾水》篇中“日维丙申”,虽句式相同,但不可同日而语。
上文“六马”,是石鼓《銮车》篇“趍趍□马”句,趍(趋)误作“”字,与石鼓《銮车》下句“□如虎”之“”相混淆,或是传抄之误。《诗经·小雅·车攻》“田车既好”与石鼓《田车》篇“田车既安”句式相似,但不是同一篇。《诗经·小雅·吉日》有“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句,石鼓“秀弓时射”在《田车》篇,“射之族族”在《銮车》篇,也仅是诗句语式相同而已。在这种句式诗义的追寻上,主要说明诗的内容是“狩猎”,与《诗经》中的《车工》《吉日》相同。为《序》文开头的“史籀石鼓”的“周宣说”铺叙而已,并无新意。
其后有慈溪孙经荣、荥阳郑桐、鄱阳周伯温及其学生马士彪等多人作观赏后记。其实石鼓文诗篇内容丰富,政治性强,上文所引《诗句》之《车工》《吉日》的讨论,仅为“石鼓为周宣王说”找说词,无可比性。从学术角度看,对当今的石鼓文研究并无裨益。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瓶生,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是两朝帝师的晚清名臣。自小受家学之熏陶,从欧入赵,楷书工整秀雅,自后随着官职升迁,在宫廷朝堂,交流日广,见识更高,喜收藏碑帖,书法转习颜平原。
同治年间,他在《题徐榕全郙藏钱南园画老马》中云:“钱公书体迥出尘,落笔欲与平原亲。横平竖直立根榘,中有浩气盘轮囷”。盛赞钱南园书法之美。时钱沣(南园)尚无书名,翁同龢学钱沣书,极力推崇,名遂高于刘墉、王文治。
翁同龢的门生张元济题《翁文恭公遗像》。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追谥“文恭”。中国江苏常熟人,晚清政治人物、书法家。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著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翁氏学颜书,出神入化,自成一体。沈尹黙曾在《跋翁同龢临颜平原(李玄靖碑)》时说:“松禅老人所临《李玄靖碑》,自是学书遣兴所为,不规矩于一点一画之得失,而神韵自然,于东坡评颜书谓清雄者近之,清代能书,似无有出其左右者”。
《清朝书画家笔录》曰:“其幼年学欧褚,中年用力于颜平原,更出入苏、米,晚年沉浸汉隶,说者谓同光间书家第一”。
但浙江西泠书家张宗祥评翁书:“魄力沉雄天骨张,瓶笙(生)款后更坚苍。但余一事堪惆怅,书法先生未细详。”谓其随意醮墨,时有浮洇涨墨之病。(见《张宗祥论诗书墨迹》,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翁同龢擅诗,生平对书画与各种碑拓所作题诗甚多,亦喜篆隶,藏有汉《史晨碑》、宋拓《礼器碑》、明拓《乙瑛碑》、宋拓《张迁碑》等多种,临习颇勤。
称赞何绍基书法,在临习《汉张迁碑》跋语中说“蝯叟臂灵,入锋中正,故能以篆籀法为八分,……则顿挫轻圆矣”。(常熟博物馆藏有翁同龢节临《汉张迁碑》纸本,计19页,每页纵45.5厘米,横48.2厘米)
翁同龢亲撰铭文,由晚清“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吴昌硕勒像刻铭,为翁同龢自用的“松禅砚”。铭文是:“西蠡得太寧造像以拓本遗余嘱倉石摹之古趣盎然不讓金玉也 壬寅 松禅”
题《何子贞篆册》诗云:“蝯叟篆势天下奇,如藤如铁如蛟螭。直将古意变斯凝,结绳而上追皇羲。……岂知我亦有奇癖,先得一本无参差,呼樽并几发幽赏,相视莫逆穷谐嬉”。
翁诗对秦皇朝的兴亡极有政治家浓厚的史论色彩,作为晚清两代帝师,亦不无忧国忧民之慨,寓意深远。
吴昌硕(1844-1927),近现代书画篆刻大师,海派艺术大师,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被称为“诗、书、画、印”四绝。他成功最早的是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功力最深的是书法,尤擅石鼓文;影响最大的是国画,以篆书、狂草入画,喜作大写意花卉。
时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名世,尤擅石鼓。吴昌硕与沈汝瑾(石友)有金兰之交,来常熟时,歇榻沈处。
某日赵古泥陪同吴昌硕到翁同龢居处虞山鹁鸽峰下瓶庐拜访,适翁同龢外出未遇。翁同龢回忆在京师为官时,光绪二十年(1849)吴昌硕曾持沈石友推荐信来府相访,未遇,留有昌硕刻“翁同龢印”和“松禅居士”印两方,事后翁写过一联“玉德金声寓于石,明窗大几清无尘”托沈石友赠与吴昌硕。
今次又因外出未遇,连忙备好酒菜,派人去沈石友处请吴昌硕与沈等一起来瓶庐一会。谁知吴昌硕已于当晚雇舟去苏州了。为此翁氏又写一联“米老襟怀云山墨,菜公诗句野渡横”,再叫沈石友赠与吴昌硕,以表谢意。在翁同龢《日记》中有载。
辛丑(1901)某日,翁同龢在沈汝瑾的藏砚处笛在月明楼看到吴昌硕写的集石鼓字楹联一副“斜阳怜草秀,微雨湿花阴”(图9),回家后亦写一篆联,题跋曰:“石友招饮笛在月明楼中,见近人吴仓石篆联,虽不及蝯叟拙朴,亦自有一种金石气,喜其联语,归而涂之。”虽偶一为之,亦见其对篆书、石鼓之喜爱也。(录自《常熟文史》第30辑。翁氏石鼓联墨迹载《书法报》1986年2月16日版)
1980年3月,余友沈传甲(沈石友后裔)时在常熟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曾负责接待日本书道会书法家青衫杉雨等一行三十人,对方要求参观沈石友故居笛在月明楼。
沈传甲将《沈氏砚林》拓本和《鸣坚白斋诗集》给他们观赏,并做了介绍。还把他仿作《沈氏砚林》的一方砚台售给了与青衫杉雨同来的日本人。足见《沈氏砚林》的艺术吸引力与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何其深远!(注:吴昌硕写给沈石友的明信片,是日本书法家青衫杉雨所收藏吴昌硕书画、信件之一,上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据推测是在1912年至1917年沈石友逝世前之物。这应是吴昌硕68岁至74岁时写的墨迹。明信片影印件载《西泠印社》期刊2004年3月版。)
翁同龢削职归田后,晚号松禅,居鹁鸽峰,又自号瓶庐居士。偶作画,曾绘《白鸽峰石门图》《斗牛图》。与归田在家的篆书名家杨沂孙(1813-1881,长翁同龢27岁)颇多往来。
杨沂孙师法邓石如,篆书从籀文、石鼓出,书形主方,自成一体。由于爱好石鼓,作《石鼓文赞》。清代杨守敬《学书迩言》中说:“沂孙学《石鼓文》取法甚高,自信为历劫不磨。”盖杨沂孙篆书,常钤有自刻“历劫不磨”印可证。并留有“游文书院”墨跡,至今尚存。
一日,翁氏获邓石如书,即递函杨沂孙,称“咏春大人”,促杨氏来山庐共赏。他在题《杨濠叟诗册》诗首句云:“我爱濠叟诗,又喜濠书迹。”对杨沂孙之尊重和喜爱如此。
常熟翁氏故居里的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殷用霖(生卒不详),字伯唐(一作伯堂),江苏常熟人。少从同邑吴震游,工倚声,小令尤善。
曾署吉安典史。罢官归里,重葺可园,啸傲文史。时杨濠叟负书名,一见即投之门下,由是尽得其传。篆、隶、铁笔,一时称美。所著有《印印》《汉官印略》行世。
苏州市孔子文庙壁间有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姓名砖刻隶书,署殷伯唐书。后殷氏孙女殷漪在香港市肆中获常熟翁枚生藏《可园印印》钤印本一册,遂在香港重印出版,前有常熟李猷癸丑(1973)《序》。
2016年,余游古镇恬庄(现属张家港市),在杨氏故居壁间,见嵌有杨公咏春和其妻赵、张两夫人合葬墓志,是杨氏弟子殷用霖所撰并篆额云“皇清诰授通议大夫选用道安徽凤阳府知府加三级,咏春杨公暨配赵淑人、张淑人合葬墓志”。下隶署“弟子殷用霖篆盖并填讳”(图10)。篆书主方,与杨氏《在昔篇》之篆书一脉相承。(图11)
钱仲联(1908-2003),号梦苕,浙江湖州人,生于江苏常熟。诗人、词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国学大师。是我的老师。他有方铜印“钱萼孙”三字,是我师邓散木刻赠的。还有一方起首印“瓶庐离孙”。“瓶庐”是翁同龢晚年在鹁鸽峰住的草庐,“离孙”是钱老怀念祖母翁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