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经典《伤寒论》中,我们常说“太阴与阳明互为表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简单来说,太阴和阳明都属于“里”的病,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初期的外感风寒那种“表证”,而是病邪已经深入体内了。但虽然同属“里”,二者的性质却完全不同:阳明是“里阳证”,偏向热、实;而太阴是“里阴证”,偏向寒、虚。
你可以想象,阳明病一般表现为体内有热、有实邪,比如高热、便秘、胃肠积滞等,所以治疗上就得用泻下、清热的方法。而太阴病就不是这样,它是虚寒型的,比如腹痛、腹泻、食欲不振、四肢发冷等等。病人可能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脸色苍白,还特别容易恶心、呕吐。
这一篇讲的“太阴病”只是讲它的正面表现,并没有把像“四逆汤”那样的方剂详细列出来。但其实,很多看上去是别的病后来变成太阴病的情况,都离不开四逆汤这类方子的应用。为什么?因为太阴病往往是从别的证型“转化”过来的。比如病人原来是外感风寒,出现了发热、怕冷这些表证,但因为体质虚、抵抗力差(尤其是老年人、身体本来就虚弱的人),病邪迅速深入,变成了少阴证,再发展一步就成了太阴证。
那少阴病又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从表证发展来的“深层病”,和太阳病一样,也是一开始从外感发作,但因为体质太虚,阳气不够,一上来就开始出现“脉微细,困倦、想睡觉、没力气”的表现,虽然表面上看似是“发热”,其实那种发热是虚热,是身体阳气被病邪压着、浮不起来的一种现象,整个身体却是“冷”的。
这时候,如果病情一发展,阳气更加衰弱,就很容易传到太阴。因为太阴病本来就是阳虚阴盛、寒邪内困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太阴病常常会出现呕吐、腹泻、手脚冰冷这些表现,一旦胃气败坏,病人是很容易陷入危重的,甚至死亡率很高。所以《伤寒论》会把这些“太阴病的死亡征象”都归入少阴病一篇,目的就是提醒医生:一旦发现病人有“脉微细,只想睡觉”这种表证,一定要警惕,这是要往太阴病方向发展的信号。处理不及时,病人随时会陷入生命危险。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本书,会发现“太阴病”的条文其实不多,篇幅也很短,但它包含的内容一点不少,只是很多内容藏在其他篇章里,或者通过“类方”表现出来。比如,只要后面条文中出现“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这些“四逆类方”,基本都可以判定是太阴病,不用怀疑。这是张仲景通过“类方法”告诉我们太阴病的判断依据。
再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六经病的理解。《伤寒论》是建立在《黄帝内经》基础上的,是“六经辨证”体系延续。但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太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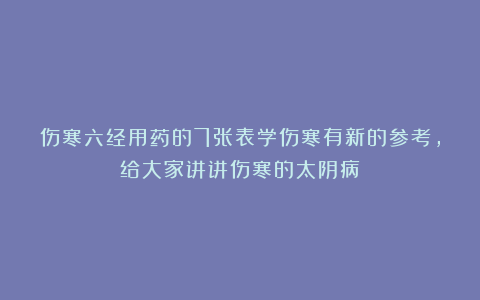
六经在《伤寒论》中,指的是六种不同类型的病机演变路线,比如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它和《内经》中的“六经”(即手足三阳三阴的经络名称)并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会混淆呢?是因为后代注解《伤寒论》的医家,特别是王叔和,他在整理张仲景的遗著时,把《内经》里关于“阴阳大论”的话抄进《伤寒例》一文中,开头就引《阴阳大论》:“阴阳大论曰……”。于是后来的医家们就以为《伤寒论》是从《内经》直接发展出来的,还用经络理论去解释《伤寒论》,这就误导了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其实,《内经》更多是一个理论框架,讲的是人体生理病理的原则;而《伤寒论》则是一部方书,是临床治疗的实战指南,它讲的六经病,是基于外感疾病不同阶段、不同表现而总结出来的辨证方法。如果你硬把它和针灸的经络理论绑在一起,就会读不通书中很多条文,比如同样一个“发热、恶寒”的表证,在太阳、少阳、太阴可能都不同,若不从“病机辨证”的角度入手,根本理解不了用药逻辑。
张仲景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而是他能把古人已有的经验总结得系统、准确,并能在临床中熟练应用。这才是《伤寒论》真正的价值。我们读这本书,最该学的,不是它里面的理论多高深,而是它如何把理论转化为临床判断和治疗的关键。如果我们搞错了方向,就容易“读了半天,什么也没学会”,那才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