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梅洋
雨丝斜斜地掠过车窗,将四月的闽东晕染成流动的宣纸。当柚子花的清香穿透雨幕涌入胸腔时,抬头一看,“沙江镇浿头农业观光采摘园”一下子映入眼帘,这便是浿头村了。推开车门的刹那,万千素白在雨帘中浮沉,柚树枝桠托举着碎玉般的花簇,层层叠叠漫向雾霭中的远山。细看那五瓣玲珑的花盏,蕊芯处洇着淡青,仿佛将整片海域的潮气都凝作花露。“春风十里,不如柚香四溢!”作家笔下令人神往的意境,原是一树树柚花在雨中无声地吐纳。站在观景台上,东吾洋的碧波在远处粼粼闪光,双髻山的轮廓被云雾晕染得极富诗意,而脚下层层叠叠的柚园正蒸腾着清冽芬芳,让人恍惚间成了花海中的玲珑少年。
一
这迷离的香阵诱惑着我们来到了背靠双髻山、面向东吾洋的沿海特色村落沙江镇梅洋村。梅洋村,这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梅洋韩氏先祖创造过辉煌宏大的伟业,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韩氏的第三世先祖韩伯修便是我们今天浓墨重彩的主角。韩伯修,字子长,好晋卿,生卒年不详。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徐元杰榜进士,南宋诗人,官至刺史,为官清廉。退隐归田后,筑庐于双髻山麓,绕屋种梅花数百株,引水成湖,自称“梅湖居士”,后湖涸,湮塞成田。我们径直来到梅花陂,在八百年前韩伯修写下《咏梅花陂》处驻足沉思。二十八亩坡地上,新栽的八百株梅树在雨中吐露嫩芽,青翠的叶尖坠满水珠,比盛放时更显生气。韩伯修的五绝《咏梅花陂》’休问桃源路,寻梅暂往返。梅花有知己,何必定湖山。’每个字的顿挫都似梅枝虬曲,展露风骨,引得游人啧啧赞叹。此刻满坡青翠,恰似韩伯脩少年时初展的眉宇。八百年的光阴在这里沉淀出岁月的印痕,将韩伯修归隐时栽下的第一株老梅的年轮,刻成永不褪色的碑铭。勤劳智慧的村民们,今年一开春就开始谋划在陂顶立巨石纪念韩伯脩,并镌刻韩伯修的五绝《咏梅花陂》,倾力打造沙江镇历史文化的旅游打卡点。
在梅花陂,我们在哗啦啦的雨声中感受着一种朦胧之美,虽然看不到梅花绽放,闻不到梅花的浓香,但却在不经意间看到那满树的嫩芽吐露着希望,昭示着青春,蓬勃着活力。听着韩伯修的后裔韩则官侃侃而谈,韩伯修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渐渐清朗。
当我们穿过历史烟云,驱车来到韩氏宗祠,只见周边冒出一棵棵梅花,向人们展示着翠绿的本色。踏进韩氏宗祠的刹那,我们的心灵被微微震颤。只见’成均雅望’的匾额泛着幽光,明代那位掌教国子监的韩氏先祖仿佛正从漆色斑驳处走来;’慕义堪嘉’匾前的烛台积着厚厚蜡泪,见证过多少寒门学子在此领取义庄束脩。正门的楹联书写着“南阳新世第,北斗旧家声”,烘托出了梅洋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宗祠中一块块牌匾“成均雅望”、“慕义堪嘉”、“词峰挺秀”“济美荆州”等都在讲述着一个个鲜活的求学、励志、奋发的故事,深深影响着梅洋村的后昆们。在韩伯修思想的浸润之下,令人欣喜的是:韩氏后生韩昆一家成为了“教育世家”,一家四代人有七人从事教育工作,两人荣膺省级先进,在“教书育人”的路子上脚踏实地,成为一代楷模!
二
据《霞浦县志》记载,嘉熙庚子年(1240年),韩伯修任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教授时,应友人之邀,写下了《康济庙记》一文,《宝庆府志》有记载。全文如下:
康济俗呼高庙,在城东五里双清崖上,祀五显,宋宣和赐额。五显,五星之精也。祠遍天下,凡邑镇尘聚,犹即胜处祠之,况名城佳府哉!邵为湖湘古郡,今又为圣上初潜藩邸。循府治北而东,资邵汇流,峰峦回缭,实一郡襟抱。旧有祠据其地,地即胜矣,神亦益昌。勅赐额“康济”,展敬乞灵,如响斯答。但地胜,而址不甚拓,江前石后,凭虚凌嶒,架棚植幹,风雨飘摇,未蠧先震,岁时祭享不便焉。邦人欲鼎建,以资诎。邵之茶冈萧君德一,世有阴德,富而好礼。其先文林、君藻,尤崇斯祠。德一克绍先志,授耒阳簿,还自京穀,谒祠耽感。卜日鸠工,选材伐石,尽撤而新之,金碧绚耀。经始于春,立成于夏,安奉于秋。邦人称颂,愿纪更剏,岁月以证,求文伯修。窃谓神之灵者,腾天□(疑为“韵”字),驭云气,游于太虚,非待人之居。以为要,惟其能赐福于人,而人亦将归福于神,必庙貌之崇,斯足以展其敬。然神之福,非私于一人。而庙貌之更新,乃萧君一人为之,岂征福于已哉?盖神心安,则邦人安;邦人安,即吾之安耳。虽然,身心安而邦人安,则萧君之福可量欤!
嘉熙庚子九月吉旦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缓缓溜走,后代为怀念先祖韩伯修,将其安葬地取名为“韩知府塆中”,《霞浦县志》有张光孝诗为证。韩知府塆中的老梅仍在雨中零落,张光孝的诗碑却已然称赞有道:“赋罢道初筑小坡,梅花清丽水涟漪。一阳未复隐非隐,数点天心知未知。万古孤芳谁领会,双峰耸立自超奇。骑驴踏雪人何往,惟有寒香似昔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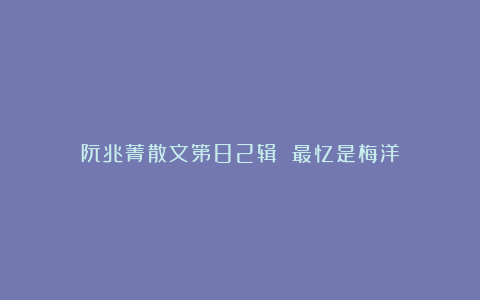
三
梅洋韩氏宗祠碑记曰:参天之木,其根必硕,怀山之水,其源必沛。霞邑南乡梅洋韩氏一脉,鼻祖于唐末随开闽王入闽,官福州太守,北宋其后裔徒长溪县韩庄,至南宋次房迁梅洋,开基衍三房,历三十余世,八百余载,迄今,人丁逾八百,枝繁叶茂。吾梅洋韩氏乃南乡之望族,承先祖之浩德,自古人才辈出,宋绍定五年,伯修公进士及第,历官刺史、大理卿,为宋文学名家;清乾隆年间,朝鼎公一门三太学,富甲一方,显赫南乡;明清两朝中贡生庠生者众,咸丰五年,履云公乡荐中式第一名位列“贡元”,遐途闻名。
…………
吾观新祠之胜,座坎向离,依群山而傍绿水,枕双髻而列九峰;接文武龙脉之迢迢,迎东吾碧水之滔滔;左葛洪拱贵云霓出,右将军揽胜日月还。竹屿岛为案,笊篱屿为印,乃钟灵毓秀、瑞凝祥聚之宝地也!宗祠占地五亩,二进木构仿明建筑,雕梁画栋,翘檐飞阁,气宇轩昂,足显吾族之文化涵养,尽彰吾族之源远流长。
嗟夫!昔宗庙之制,始之于周,传承百世,中华乃兴。今建祠之旨,在乎敦本敬宗,和亲睦族,追先人之恩德,扬祖上之功绩,聚合族之精气,迪后昆以有为。吾族建祠,历尽苦辛,实属不易,后世子孙当奉先思孝、精诚团结,励精图治,丕振家声,再铸辉煌!先祖之德定将泽被千秋,万世昌荣!
我们从韩则官的《梅洋韩氏宗祠碑记》中可以读出梅洋村的历史和文化,读出丝丝缕缕的苦涩和甘甜,读出风雨兼程的期待和希翼,满足大家一颗好奇而虔诚的心。那触目可见的巍巍耸立的教堂告诉了我们一切。梅洋,这个被梅香浸染的村落,连同信仰都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开出一树奇花。
四
午后,我们冒着滂沱大雨驱车往葛洪山,七十二峰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传说葛洪在此炼丹时,’丹井夜鸣,紫气东来’,至今山腰处犹见朱砂矿脉如血痕蜿蜒。我们在山脚茶坪处,抬头忽见半山腰云隙间露出赤色岩壁,嶙峋怪石似万千道童稽首,又似丹炉倾倒后凝固的铜汁。雨丝穿过千年松柏,在《抱朴子》这部由晋代葛洪编撰的道教典籍记载的’石室’前织成珠帘,苔痕斑驳的药臼里,竟有嫩蕨从裂缝中探出,恍若葛洪遗落的金丹生了根。韩伯修的《洪山》七律诗便随颠簸山道流淌:“壁立东南第一峰,问名知道葛仙翁。丹砂灶逼云头近,玉井泉流海眼通。六字籀文天篆刻,数间洞屋石帡幪。我来整屐层巅上,无数群山立下风。”
葛洪,这位东晋炼丹大家在此山结庐著书将’玄’与’素’的哲思炼成不朽文章。摘录一首葛洪的五律诗以飨读者。《涵碧亭》:“雨歇留蒸湿,明来得翳凉。双嬉鱼欲动,万个竹添长。景到烦诗答,叹多厄日忙。兹游端胜绝,不是学高阳。”而韩伯脩晚年经常邀约好友游览葛洪山,应该是在山岚吞吐间,寻到了比功名更为永恒的寄托。
暮色裹着炊烟漫上山道,梅洋的滋味在舌尖苏醒,勾起了馋虫的味蕾。鲟虎鱼居然成了鲟的天敌,尾巴一灵动,便是天下无双。一个小小的甩动,就足以把鲟的双鳌生生地折断,不知不觉间成了鲟的美食。我们吃着长得和弹跳鱼一模一样的鲟虎鱼,你说它的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弹涂鱼也是味美肉鲜,加入酸味的混杂,越嚼越香,激发味蕾的肆意疯狂。海蛎煎饼,让人食之难忘,一块再一块,齿间的香味似乎在不断地蔓延到肺腑深处。霞浦话称为“爹饼”,真的是脆酥可口,闭眼迷醉。小小的沙螺,我们吃起来,苦甘相伴,唇齿生香。当地黄糍粑的米香混着山梔染就的金黄,Q弹无比,加之青菜的裹炒渗透,植物碱的微涩后泛出清甜,恰似这个村庄的岁月滋味。
归程的雨越发绵密,后视镜里的梅洋渐成水墨剪影。梅花陂的梅花正在抽芽、拔节,把浓浓的绿意奉献给雨后的世界。八百年的光阴在这里凝成琥珀,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飘散在炊烟里的、沉淀在族谱中的,都在细雨中舒展成永不凋零的梅枝。
车子在雨中穿梭,满车的柚花香沁人心脾。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关于梅洋的种种,已如那年韩伯修遗落的诗稿,在时光的发酵中成为更醇朴的沉淀。或许每个初遇都是久别重逢——那雨中吐蕊的柚花,可是葛洪丹炉溅落的星火?那祠堂滴答的檐水,可是韩氏先祖穿越千年的叮咛?梅洋用一场滂沱大雨,将八百年的光阴酿成陈醅,让每个过客都成了醉归的游子……
(写于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