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书名:《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作者:吴思
版本信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信息
汪一帆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本文为第三届社科法学书评、影评与翻译大赛拟获奖作品
*为方便读者阅读,在编辑时略去注释
儒家伦理视角下的帝国统治失灵
——评《潜规则》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帝国经历崩塌和重建的轮回。为什么帝国统治会反复失灵?儒家伦理提供可能的视角。当一个帝国建立,儒家伦理的道德准则与人性逐利益的现实产生冲突,迫使潜规则的建立。潜规则之下,帝国官员相对于百姓的权力绝对化。随着帝国统治的持续,绝对化权力产生的压迫不断加重。最终原本顺服的百姓越过临界值,发现做良民的收益小于造反,成为起义者推翻现有的统治的助力。
关键词:儒家伦理、帝国统治、潜规则、圣人理想
自秦王朝确立封建帝国统治以来,帝国被建立和被推翻。在每一个帝国末年,起义爆发。反叛中的胜利者成为下一个帝国的开国之君,接着,新的帝国又被更新的反叛者推翻。这样的黑暗轮回,在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中重复了十余次,而帝国的统治体制不改。
另一方面,儒家伦理自汉朝被提升为官方思想,开始与政治频繁互动。儒家伦理尝试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所有人,最终导致了官场规则的表里分离。皇帝陷入德治的理想,官员内部潜规则盛行,百姓在潜规则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最终,当压迫的程度突破某一临界值,做良民不如起义,百姓就选择了造反。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黑暗不断轮回?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自定立儒家文化在国家治理上的地位起,帝国统治和百姓之间的冲突始终难以得到体制性的解决?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将以《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所提出“崇祯死弯”的模型引入话题,并将陈胜、朱元璋和李自成三个案例代入模型,还原他们三人从良民走向反叛者的路径,进而以他们为轴,搭建起背后帝国崩塌与重建的轮回历史场景。
一、案例:三次帝国的轮回
(一)崇祯死弯
“崇祯死弯”得名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明皇朝覆灭之前,崇祯为镇压各地的起义,向百姓敛财以练兵。敛财之初,“敛财练兵”与“反叛者数量”两个变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随着敛财增多,官兵被训练得更好,反叛者在官兵的强力镇压下减少。然而,当敛财的程度超越某一数值时,良民们发现,帝国不断地敛财已经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面,造反者就意味着不再受到帝国的压迫,更有可能获得生路。此刻,风险的天平两端,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当良民的成本高于反叛者,越来越多的良民开始选择造反,此时,“敛财练兵”在将“反叛者数量”压到谷底后,绕过一个弯,开始呈正相关关系:帝国越敛财,反叛者就越多。
崇祯走向“死弯”的原因在于,他认识到“敛财练兵”与“反叛者数量”之间过犹不及的关系太迟。直到上吊景山前的二十天,他才被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告知,因为过度的敛财,帝国非但没有实现练兵的目的,反倒逼反了越来越多的良民。而此时,为时已晚。最终,到达谷底之后高高扬起的U型弯勒死了崇祯,明王朝随之覆亡。
而将“崇祯死弯”的案例推广至“崇祯死弯”模型,横轴上的变量未必总是“敛钱练兵”,而是由帝国对百姓统治的各种手段构成,在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变量,诸如严苛的法律规定、被挤压的生存空间和过度的摊派税收。但其中一致的是,反叛者们共有的特质是“被逼无奈”。他们并非不愿意顺从帝国的统治或者不安于作为良民,而是从某个时间点起,他们做良民的成本已然高于做造反者。
(二)历史轮回:陈胜、朱元璋和李自成
关于良民是如何被帝国的统治手段压垮,并最终在逼迫下成为造反者的,我们将以下三个案例代入“崇祯死弯模型”中,对此加以考量。
1. 陈胜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农民起义,《陈涉世家》中如此载道: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从这段话中可知,陈涉在正式选择造反之前,做出过一个风险权衡。一面,当时陈胜吴广两人作为屯长,带着一支队伍前往渔阳戍边,但恰逢天降大雨阻塞道路,他们带领的这支队伍已经耽误了期限,依据秦朝严苛的律法,失期当斩。倘若陈胜吴广想要做良民,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规定赶往渔阳,最终在渔阳被处死。换言之,做良民没有活路了。而另一面,“举大计”造反最坏的结局也不过是死。同样是死,做良民不如造反。
由“崇祯死弯”模型观之,原本陈胜等人都处在秦王朝的律法统治之下,他们依照律法要求组成队伍前往渔阳戍边,律法越严苛,他们就越顺从。而使得陈胜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的,是一场突然的大雨。这场大雨决定了即使陈胜保持顺从,也不能在律法统治下顺利生存。于是,他越过谷底,决定造反。此刻,秦王朝向陈胜等人施加的律法统治不再有将他们约束为良民的功效,相反,律法的惩治越严苛,陈胜等人的造反之心就越强烈。
2. 朱元璋
在朱元璋的坐标轴中,横坐标是他的生存空间。最初,元末的年景不好,家里贫穷,养不起朱元璋这个孩子。但朱元璋没有选择造反,他还有退路:去庙里当和尚混饭吃。接着,朱元璋当了和尚,这时,有人告发朱元璋与红巾军来往,有造反的意图。生存空间又一次收缩,但是,朱元璋仍然没有选择立即造反,他犹豫着想: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到底是要束手就擒,还是奋力一搏呢?但很快,他就没有犹豫的机会了:他所在的寺院被官军烧毁了。
至此,朱元璋得以安身立命的空间彻底消失了。他的基本生存需求随着寺院的灰飞烟灭,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官军斩断了朱元璋“束手以待罪”的后路,朱元璋的“崇祯死弯”模型也随之到达谷底。他继续顺从帝国的统治做良民,就在世上没有安身之处了,于是,他别无选择地越过谷底,“奋臂而相戕”,成为上升的曲线中的造反者之一。
3. 李自成
和陈胜、吴广和朱元璋一样,李自成同样是在被逼无奈之下选择造反的。李自成面临的是愈演愈烈的政府额外摊派赋税和大地主要债。越过谷底,做良民的风险已经远远高于造反,他随之走上叛军的道路。最终,李自成等明末叛军扬起的“崇祯死弯”的曲线,成为勒死崇祯皇帝的那根吊绳。
(三)帝国统治与造反者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两件事。第一,千年来,帝国在造反者的出现之下,不断崩塌和重建。陈胜吴广起义发生于公元前209年,朱元璋造反发生于公元1352年,李自成造反发生于1630年。第二,造反者的后代成为统治者,统治者却又被新的造反者推翻。朱元璋和李自成同为造反者之余,他们一个是明朝的建立者,另一个是明朝的终结者。造反者们并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和帝国统治一并在轮回中跌宕。
从陈胜、朱元璋到李自成,帝国在崩塌与重建之中不断进行的轮回,昭示着自中国历史上自定立儒家伦理为正统思想起,帝国统治与底层的百姓之间便存在某种体制性的冲突。接下来,本文将拆作三部分,尝试解释两者间的冲突所在。首先,讨论儒家伦理的内涵,即圣人假设。其次,讨论儒家伦理怎样构建起帝国的统治。最后,讨论导致帝国的统治的黑暗轮回不断循环的原因。
二、儒家伦理的圣人假设
儒家伦理提出的圣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具体而言,对于有权受到教育的士大夫阶层,一个“圣人”由内圣和外王两个部件组装而成的。首先是内圣,《论语·学而》言之: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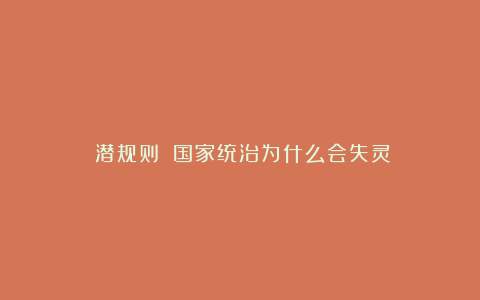
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儒家伦理提出的道德标准:“孝”“悌”“信”“爱众”“亲仁”和“学文”。具体而言,在行为上,要向长辈、长兄和仁者三类对象学习。在品性上,要确保自己谨慎而有信用、博爱大众。如果行有余力,还要学习六艺之文。在这一系列道德标准的内部,还存在一个推而广之的逻辑:“孝”是儒家弟子品性的核心,由在家中的“孝”可以推出在外的“悌”,由在外的“悌”又可以推出“信”。
从为人到治国,儒家伦理沿用这套推而广之的逻辑。《礼记·大学》中言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欲明明德为天下者”可以解释为“想要成为圣人的人”。他们以“天下平”为最终目的,从自我往外推,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步骤。这八个步骤中,实际上存在两个部分,修身之前的所有环节都是内在的环节,限于个人的实践,缺乏具体客观的标准,修身之后的环节则是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是现实可检的[]。内在的个人修养可以推至外在的国家治理,治国就是为人的扩大化,只要一个统治者将自身的道德修炼至出类拔萃的境地,外在的百姓、天下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由“内圣”实现“外王”的圣人理想由此落成。
对于小民百姓,儒家的假设则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因为人性善,所以经由教化,百姓可以形成自律的状态,进而将自己限制在秩序的界限之内,不作奸犯科[]。教化的实施者是士大夫阶层,而所谓“自律的状态”,则是让百姓们无原则地让渡或被迫放弃权利[],最终,和“内圣外王”的士大夫们一起归于一种无私利的圣人状态。
我们发现,儒家的圣人理想以道德为核心,将极高的道德要求加诸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士大夫们和百姓们。然而,现实世界中,真正的圣人是少数,指导着人们做出行动的首要因素仍然是私人的利益实现。儒家伦理对私心存在的置之不理,使得其圣人理想最终沦为一种假设。更为危险的是,当表面的道德要求与内在利益需求的背离在一个社会环境下广泛存在,它将催生出相对于儒家伦理表面规则的另一套规则。
三、顺服的百姓
(一)精英文化与小民文化
等级制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框架。就“三纲”言之,“君为臣纲”规定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则规定家庭层面的长者与幼者、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三者相互统一的是,它们都表现了等级划分的意识:君高于臣,父高于子,夫高于妇。
等级划分意识在儒家伦理中无处不在。是否接受过儒家正统教育,则是政治文化阶层的划分标准。作为在政治上处于上层地位的皇帝和士大夫,他们有权接受来自儒家典籍正统教育,因而形成精英文化。另一端,缺乏正规教育经历的百姓同时在政治中处于下层地位,形成小民文化。帝国的统治建立,就在于精英文化通过教化说服小民文化向自身顺服。
精英文化与小民文化之间,无时无刻发生着不平等的交易。从现代政府理论而言,百姓向政府支付税收,政府向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双方公平交易,有买有还。而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则认为,百姓向政府支付税收是理所应当的。皇帝接过这笔税收,将其用来营造私人的宫室、供养私人的妻妾都是应当的。精英们可以只接受税收,不提供公共服务,有买无还。
(二)皇权的正当性
为什么这样不平等的交易可以被建立?首先在于,精英文化论证了皇权的正当性。精英文化的参与者经由培养获得书写的权力,我们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看到对于皇权来源的讨论。孟子在齐宣王求问“武王伐纣”是否构成臣子以下犯上弑君,孟子说武王贼仁残义,沦为暴君,已经放弃了君主的身份,对之征讨诛杀就是正义的行动。“罢黜百家”的创始者董仲舒说,“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把皇权的正当性和天道挂钩认为君主所推行的庆、赏、罚、刑都是天道在人间的投射,天道不可违逆,是小民们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程朱理学的王道论一方面认可天理的存在并要求“循天理以治国”,一方面更加强调君主的道德品格,认为“内圣外王”。从中,可以大致总结出两点精英文化对于皇权来源的普遍认知:第一,皇权因为与天道挂钩,而具有无需论证的天然正当性;第二,君主应当通过对自身道德品格的要求,来使得皇权被恰当地行使,如果君主肆无忌惮地行使皇权,他就会沦为暴君,并随之失去拥有这一权力的正当性。
精英们通过教化的手段,将他们所持有的精英文化认知加诸下层的小民之身。自南宋以降,朱熹编订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用书,历代科举以儒家经典为考察内容变相地提出要求,一切试图通过学习提升社会阶层的学生们都必须以儒家文化为学习对象。明清两朝民间好讼之风对无讼的传统社会形态构成冲击,康熙帝颁布的以“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善良”(《清圣祖实录》)为内容的《上谕十六条》小民百姓没有反抗权,并要求民间定期集会来阅读这些帝王训诫。我们看到,在强有力的精英文化面前,小民文化是无力的。小民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与精英文化互动,并最终在互动中被教化。由此,小民们拥有了和精英们一样的认知:君王是道德的,皇权是正当的,等级制的划分将他们固定在卑微的社会地位中同样无可厚非。
(三)顺服的百姓
在面对教化时,百姓们选择了顺服,而非反抗。一方面,他们既有低微的政治地位让他们不敢以下犯上、微薄的文章写作能力又使得他们不能回应文人们恢宏的论证。另一方面,教化本身内置的规定就表明,百姓必须接受精英的统治。儒家伦理存在将人的才智德行与社会地位、从事事务并置以划分等级的倾向,《孟子·滕文公上》有载:“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国语·周语》有载:“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左传·成公十三年》又有载:“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大人与小人,亦即精英文化与小民文化,两者能够从事的事务有严格的划分,精英遵从礼而从事国家的治理,小民则依顺精英的管辖尽其力。
此外,精英文化还通过种种手段,阻止反抗权可能的产生。鲁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铸造铁鼎,将范宣子所书写的法律刻在其上。孔子听闻之后,感叹道:“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孟子》)”孔子认为,不应当制作铁鼎,让百姓有权利看到铁鼎上的法律条文,因为这会使得百姓不再像以前一样服从精英的约束,导致“贵贱无序”的后果。固然,孔子想要看到的并非精英对百姓无限制的压迫。在他的圣人理想中,道德可以推出万物,自然也可以制衡皇权。但事实是,“君王的失德”始终缺乏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于是,只有在一个朝代已经被推翻之后,后世的人们才能够基于已有的毁灭结果,给前朝的君主下一个“失德”的论断。换言之,圣人理想没有为保护民权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帮助,百姓之于帝王,始终是无权反抗的。
从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性质观之,百姓的顺服是具有继承性和持续性的。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自前辈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是可以被直接继承被证明有效的,由是,有效的解决方案成为传统,后辈遵从传统,并期待通过这种遵从实现和前辈们完全一致的生活,他们不倾向于去打破已有的生活状态,继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
概言之,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层面,存在着精英文化与小民文化的二分,精英文化为皇权提供了正当性论证,而后运用自己相对于小民文化的统治地位,将自身的认知强加在后者身上。而对此,百姓的反应是顺服于精英。文化互动背后,更深层的是权力关系。德治的理想美化了对百姓构成高度压迫的专制权力,将百姓置于卸除反对权的地位,至此,帝国自上而下的统治建成了。
四、体制性的冲突
(一)潜规则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顺服的惯性被打破的例外。从陈胜、朱元璋到李自成,他们与顺服者的区别在于,稳定的社会环境变成了动荡的社会环境。陈涉背负着“失期当斩”的律法,朱元璋容身的寺院被官军烧毁,李自成面临着政府额外摊派的大额税收。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因循前人的生存经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传统失效了,曾经顺服的百姓越过“崇祯死弯”,成为帝国的反叛者。
于是,在观察帝国的轮回时,可以将每一次轮回可以被拆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旧的帝国刚刚崩塌,新的帝国刚刚建立,社会环境由动荡归于稳定。新的精英们刚刚就位,还没来得及贪污、腐败、编织起内部互惠的利益网络,因此,百姓受到的压迫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他们愿意保持顺服的态度。而在后一阶段中,随着新的帝国不断发展成熟乃至于陈腐,精英中参与帝国行政的那些官员一定会变成贪官,而贪官挤压百姓的生存空间,直至顺服不如造反。
就官员间这种“好官变贪官”现象的普遍性,明太祖朱元璋早有认知,并总结出了一条“新官堕落定律”:“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有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朱元璋发现,他任命的官员,在最初上任的时候,都忠诚又有原则,可是任用的时间久了,就都又奸又贪。
在理想中,儒家培养的是圣人。圣人为人处世依循的是道德,诸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原本,按照儒家文化的理想,当经过考察的官员被投入帝国的运转,他们所受的良好道德教育会自然地被外推并应用于国家的治理,实现国家的善治。然而,这一设想忽略了人性逐利的本能。在现实中,人性会自发计算现实的利害,并根据趋利的本能展开实际行动。此时,出现了根本的矛盾:赋予官员权力合法性的儒家教化要求他们做出合乎道德的行动,而逐利的本能则支持他们做出与之背离的行动。为了弥合这两者间的背离,官员们选择将自己的行为一分为二,创设出一套相对于正式规则的“潜规则”:在表面上,他们遵从正式制度的设定,根据儒家教育的道德标准行事;在暗地里,他们将正式制度屏蔽在外,进行私下的规则交换,以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潜规则的参与者中,包含着先于新官进入现实职位的同僚们,也包含着复杂官场结构中存在着的其他角色:胥吏衙役、土豪和王侯。圣人经典第一次教育了新官,让他们以“并效忠贞”的面貌取得进入官场的资格,接着,官场的现实又用潜规则给予了他们第二次教育,新官们从中窥见了圣贤们不愿意讲的、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并将他们导向“俱系奸贪”的落点。
当然,不免提出的问题在于,新官发现了潜规则,就代表他们一定会选择加入潜规则之中吗?难道世界上一个真正的、能够置身事外的好官也不存在吗?从结果观之,朱元璋已经告诉了我的答案:新官的堕落是一个定律,无人可以避免。朱元璋同样尝试着破除过这一定律,譬如和新任地方官谈话,劝导他们不要做贪官,但情况并无改善。笔者认为,新官堕落定律背后,实则是帝国体制与百姓的冲突,只要帝国的体制不覆灭,新官堕落定律永远都不可能被破除。
(二)复杂的官场
《晏子春秋·外篇七》中,讲了一个齐景公派晏子治理东阿的故事。晏子第一次去治理东阿,不接受贿赂、造福穷人、百姓不挨饿,齐景公却听闻了“二谗三邪”说晏子的坏话,要治他的罪。晏子第二次去治理东阿,调整了自己的治理策略,加重赋税、压迫百姓、贿赂权贵、偏袒恶民,齐景公得到的消息却是晏子治理有方,想要奖赏他。
现实的官场非常复杂,皇帝和官员之间存在着大量中间人物,这些人物能够依据自身的得失,决定皇帝对官员的评价,进而决定官员的命运。在中央,中间人物表现为“二谗”,是权贵和皇帝的左右亲近之人,依据潜规则,他们接受来自地方官的贿赂,向帝王美言大行贿赂的官员,弹劾不行贿赂的官员。在地方上,“三邪”是邪民、懒民和豪强。他们熟悉地方环境,并且已经建立起一个在当地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新官想要做一个贪官,他们愿意将其纳入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之中。如在《红楼梦》中,贾雨村正是在地方胥吏的提示下得知“护官符”的存在,依照贾史王薛的既有利益格局行事,为薛蟠脱罪,最后一路官运亨通。当然,如果新官坚持要做一个清官,拒不接受潜规则的二次教育,那么,他们就会遭到“三邪”的反击。如明代的清官道同,他就是在拒绝了土豪的贿赂之后,土豪与权贵勾结一气向皇帝告假状,最终道同被判处斩首于世。
我们发现,新官在进入官场时,面临的困境很类似于数学上的夹逼定理。在数学上,夹逼定理讨论的是极限的问题。当一个函数的大小位于两个其他函数之间,且这两个外部函数的极限的数值相同,则中间函数的极限值即等于此数值。类而比之,官员遭遇的处境与位于中间的函数是相同的。向上,官员面对“二谗”。向下,官员面对“三邪”。此刻,上方函数无限向下逼近,下方函数无限向上逼近,把官员作为中间函数夹在中间。选择接受夹逼的贾雨村官运亨通,选择不接受的道同则被斩首于市——上下函数希望推出中间函数的极致是唯一的、一致的、不可回避的:加入潜规则,做一个贪官。
在潜规则中,官员和“二谗三邪”是相互需要的。“二谗”们需要官员进献的贿赂来维持奢靡的生活,“三邪”们则需要官员支持他们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则需要“二谗三邪”替自己向皇帝进纳美言。于是,他们之间双向的供求关系达成,潜规则建立。在这套规则中,官员和“二谗三邪”两者是互惠互利的,他们一起既剥削皇帝,又剥削百姓。
(三)官员的绝对化权力
在潜规则的交易者之间,权力是存在制衡的。在正式规则中,儒家文化为权力设置的制衡是道德。在潜规则中,制衡官员权力的是官员和“二谗三邪”议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交易中,双方各出供求,制定置换规则,双方都不能侵犯被划归对方的利益。譬如官员给皇帝身边的权贵送贿赂,权贵收下了贿赂,就有义务去皇帝面前为这位官员美言,如果权贵不这样做,他和官员之间达成的潜规则就被破坏了,他变成了“不当得利”,会遭到官员的反击。
从这里,我们发现“二谗三邪”和百姓在性质上的分野在于,百姓没有可以与官员置换的利益。在皇权之下,百姓是顺服的,儒家文化已经为他们制定了准则:做一个被“大人”统治的“小人”。此外,和“二谗三邪”不一样,百姓不能够对皇帝产生实际影响。正如在晏子前后两次不同的治理中,百姓无疑是支持第一次的清明之政的,但他们的观点并不会被送达中央,因此晏子只要不贿赂“二谗三邪”,百姓们再满意他,他仍然会遭到皇帝的批评。发现百姓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可以被置换的利益的人不仅是我们,还有官员们——于是,百姓被踢出了潜规则的交易。
利益置换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制衡官员加诸百姓的权力?儒家圣人理想的回答是道德。此处的道德,是官员所经历的正统教育向他们提出的自律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确实构成了对于官员的约束:潜规则始终在暗处,没有取正式的规则而代之,在表面上,赞美一个官员的有为,使用的话语仍然是“勤政爱民”而非“善于潜规则交易”。但是,对于面临压迫的百姓而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话语,而是现实的权力运作。当潜规则的存在帮助官员规避了道德的谴责,道德无法构成官员权力的制衡,民权陷落于无所依仗的地位。
于是,我们看到官员相对于百姓,拥有绝对化的权力。在官员加入潜规则之初,他们想要的只是更多的私利,并没有想要把百姓逼上死路。然而,在官员每一次尝试着向百姓加敛加压后,百姓因为无从反抗而继续保持的顺服态度,让官员意识到他们的堕落并不会遭到任何严重的惩罚。于是,私心扩大了,压迫继续加重。最终,帝国体制下的贪官推着百姓一点点逼近“崇祯死弯”,越过谷底,做良民的收益低于起义,这个帝国的造反者们就被催生了。
此后,历史的黑暗轮回进入末期,起义军四起,王朝开始分崩离析,直到新的统治者平定四境,开启下一个王朝。王朝伊始,帝国统治与百姓的关系会再次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上一个王朝末年达到峰值的剥削降回原点,接着,随着王朝的发展成熟,潜规则网络层层建立,剥削程度随之上升,直到下一次越过峰值,将下一批良民逼成造反的起义军。而那,就又是下一个轮回了。
五、结语
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阅读中,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帝国总是像黑暗的轮回一样,经历着不断崩塌与被重建。从社会经济的视角,黑暗轮回持续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能够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而从儒家伦理的视角观之,则能够发现在帝国统治之下,帝国体制和百姓、精英文化和小民文化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儒家伦理提出了圣人假设,妄图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参与帝国统治中的每一类角色。而人皆有私心、皆逐私利,当皇权经由官员之手落实,官员内心的所求与外部的要求之间发生的背离,导致他们建立起与儒家正式规则背道而驰的潜规则。根植于儒家伦理之上的潜规则最终取代道德,使得面向百姓的官员权力彻底失去制衡。当顺服的百姓和绝对化的权力相互叠加,最终,我们见到陈涉、朱元璋和李自成这样曾经的良民,在无限度的压迫中越过“崇祯死弯”,选择揭竿而起。
概言之,推动中国历史的黑暗轮回不断重复的,实则就是潜规则。它因其隐蔽性,不受到正式的规制,在暗处生长,直至无法无天。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对儒家伦理已经予以科学的认知,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然而,儒家伦理作为传统文化,已然养成了我们内敛含蓄的传统性格,在当代的社会交际场合,潜规则仍然无处不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本文在帝国更迭的历史背景下,对潜规则进行分析讨论,以期能够告诫当代人潜规则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不至于重蹈历史的覆辙。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