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夏,我在本刊《当代敦煌》转发了一篇孙志军先生的文章——《被监禁在莫高窟的沙俄残兵》,为了让贴子图片丰富,我擅自将莫高窟第254窟的烟熏壁画加进了贴里,不料孙先生私信说:“沙俄在莫高窟熏黑的壁画并不能确指是哪些洞窟,包括其它破坏,因为没有明确的记录”。孙先生此番道理我认同,但觉得问题不大,因为白俄在莫高窟支锅做饭熏黑壁画、盗刮佛金、破坏佛像等早已铁证如山,很多文章都这么说,即便没有证据那又何妨,所以没有撤回贴子更正。但事后冷静思考后却发现,把莫高窟的被破坏笼统地归罪与白俄,可能会掩盖其它一些真实的原因。笔者因敦煌研究院事业需要,曾对158窟涅磐像和320窟坐佛两尊彩塑进行过临摹复制,而这两尊彩塑也是莫高窟被盗刮最严重的佛像。在临摹工作中,我意外发现盗刮佛像除了白俄另有祸首,然而这个祸首盗刮佛像的目的,却十分奇特,令人匪夷所思!
▲莫高窟254窟因过去有人居住生火,造成壁画熏黑,遭破坏严重
秘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如有采用,请慎重!)
盗刮佛金另有祸首,不只是白俄所为
文:杜永卫
敦煌莫高窟有一些佛像和壁画,在造像的时候都按贴过金箔,有些至今闪烁着耀眼的金光,但也有一些被人为刮残,呈现出斑斑驳驳的刀刮之痕。1978年我刚到莫高窟工作,第一次在老师带领下上洞窟学习,当看到那些被刮过的斑驳塑像时我很好奇,老师解释说:那些刮痕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股流窜到莫高窟的白俄残匪所为,他们因对黄金的贪婪,刮走了佛身上的金子。这个说法似乎铁证如山不容置疑,之后每当发现洞窟中有用刀具刮过的地方,我们便想当然地认为那都是白俄留下的罪痕。然而随着我多年在洞窟上工作时的观察,尤其亲手临摹过两件被刮过的佛像,通过对刮痕的仔细分析,我发现这些刀痕并非使用同样的器具所刮,也并非一次性刮掉的,而且是逐年累月累积的刀痕,也就是说这些刀痕可能是在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里逐渐刮掉的。而且盗刮者并不只是刮金,一些不贴金的佛像和壁画也时有人为的刮痕。种种迹象反映,这种盗刮佛像壁画的行为似乎跟贪婪无关,而是因为某种需要,而且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才驱使他们冒着对神佛大不敬的风险行此恶行。
▲莫高窟158窟泥彩塑卧佛,被刮的刀痕遍布全身,彩绘遭破坏严重
▲莫高窟320窟泥彩塑坐佛,肌肤部位均被刀刮,彩绘遭破坏严重
为了探究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白俄流落到莫高窟的那段历史说起。
1917年十月革命,苏共夺取政权,大批沙俄贵族及旧军队组建了一系列军事组织,被称为白军、白卫军或者白匪军。他们与当时苏共领导的红军武装对抗,失败后逃亡海外,其中不下三四万人的白军残部及难民涌入新疆,这批白军及难民,被我国称为“白俄”。“白俄”不是白俄罗斯的简称,而是专指这个时期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难民,据载当时中国容留的白俄达到二十万之多。那么白俄又是怎样来到莫高窟的呢?
自苏俄内战爆发以来,白俄在新疆驻留达三年之久,不仅影响了新疆的秩序,而且这个庞大的武装难民群成为极其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处理不慎便可能引发暴乱。其中白俄七河省军区司令、陆军少校阿连科夫率残部官兵1400余人马700余匹窜入新疆,企图串联各地白军残部把新疆作为反攻苏俄的基地和后方。
▲苏俄十月革命之际,苏俄红军以及后来的苏联红军多次入疆作战。图为1921年苏俄红军入疆围剿“白俄”
1920年阿连科夫率残部七百余人进入新疆塔城,在袭击奇台时被当地中国军队缴械,时任新疆省长兼督军的杨增新为防止阿连科夫部横生祸端,请示北洋政府“以分其势,而免意外”,将其一部分安置在新疆,一部分近五百人,与甘肃省长公署协商安置于敦煌。
▲ 民国十年八月十三日甘肃省长公署关于俄旧党官兵安置甘肃敦煌的呈文
时任敦煌县长陆恩泰和当地驻军统领周秉南一起接收了这批白俄官兵。然而把这支虽被缴械但参加过一战的骁勇善战的白俄军队安置到哪里才能即便于监管又不会生乱扰民,却成了棘手的问题。陆恩泰费尽心思,想到了离城25公里的莫高窟,于是莫高窟便成了白俄残部的收容所,这一住就是半年之久。然而谁都未曾意识到,四五百号东正教异教徒住进佛窟,在石窟里生火做饭,生活起居,会给莫高窟艺术带来多少损害?
▲ 1921年6月11日,白俄残军阿连科夫、伊拉列耶夫等469名,乘马488匹、驾马车18辆,由新疆营长徐谟率所部骑兵180骑,执行解送俄兵任务,6月10日,从安西到敦煌,被安置在县城北门外大校场。
▲ 为防止这支残兵发生变故,也为了敦煌县城的安全,甘肃督军陆洪涛命令敦煌县长陆恩泰将白俄安置在远离县城的莫高窟驻扎,听候上峰的最后处置。
▲ 肃州(今酒泉)巡防三营营长周炳南率一个营的步兵,会同押解白俄到敦煌的新疆军徐漠骑兵营驻扎在莫高窟,监视阿连科夫残部。据孙志军先生说:“按照官方档案,当时沙俄在莫高窟被限制在九层楼以南活动”。
▲ 阿残部驻留莫高窟期间,对佛窟艺术很不尊重,他们在洞内支锅做饭,把寺院中的门窗、匾对当柴烧,还薰黑一些石窟精美的壁画。
▲ 莫高窟第196窟甬道被刻划的旧俄文,内容为一低级军衔
关于白俄残兵对莫高窟的破坏情况,在该事件二十年后的1941年敦煌士绅吕钟编纂的《重修敦煌县志.编年志》中的一段文字:
“乙丑,十一(十)年夏四月,白俄阿连科夫至敦煌。先是,苏联革命军起,白俄军事首领阿连科夫与赤军交战,节节惨败,退居伊利及奇台县。新疆督军杨增新命陆军旅长蒋松林、教育厅长刘文龙前往交涉,解除武装,复将阿氏拘留省城,以白俄人多势重,携带马匹恐发生意外之虑,思有以分其势。因念甘、新唇齿,谊同一家,与甘肃督军陆洪涛叠次电商,陆允敦煌安置。令敦煌县长陆恩泰、防军管带周炳南妥办招待。陆恩泰遵照省府指定地点,安置阿部500人于千佛洞,计人一口日给麦面一斤半,其阿氏残部所带马匹另设牧场。复向省府请准旅费,分三起解送进关,分赴上海、天津,所幸地方安谧,惟千佛洞古壁画、佛像不无损坏,至匾对、器具被白俄斧薪者更无论矣(《补过斋文牍》、杨增新《行状》)。”
据孙志军先生说:“按照官方档案的《俄旧党官兵安置甘肃敦煌》的记载,当时沙俄在莫高窟被限制在九层楼以南区域活动”。另有当时监管白俄残兵的肃州巡防三营营长周炳南,发现沙俄残兵对莫高窟的破坏,呈报甘肃省政府将他们迁出[注1]。
上述记载和呈报中虽没有更详细记录白俄破坏的细节,但可以说明,除了白俄在壁画上刻画的俄文字迹以及将寺院中的门窗、匾对当柴烧的记录是破坏的铁证外,九层楼以南区域的一些洞窟中留下的因支锅做饭薰黑的壁画以及对佛像破坏的痕迹很有可能与白俄有关,但也不是全部有关;而九层楼以北的这类型破坏就很可能与白俄无关。由于县志记述的“古壁画、佛像不无损坏”一句过于笼统,以致后人很容易把洞窟内人为损坏甚至自然损坏的原因张冠李戴统统归咎于白俄所为。事实上在白俄到达莫高窟的十四年前,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中[注2],就已经有不少烟熏过的洞窟、残损的塑像、被盗刮过的斑痕甚至被挖目毁鼻的情形,这图册里所有破坏的痕迹肯定与白俄无关。
▲ 在伯希和1908年的敦煌图录中,九层楼以南156窟有灶台和明显烟熏痕迹(摄影:努埃特),这说明九层楼以南因居住生火熏黑壁画的洞窟并非都是白俄所为,同时说明白俄之前就有人在洞窟中生活起居的事实。事实上在洞窟中居住并生火熏黑壁画的情况,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发生过,比如榆林窟25窟前室。
▲50年代莫高窟四月八庙会。据敦煌张启农老先生说:“过去敦煌人每逢四月八都要上莫高窟烧香拜佛、许愿还愿,常有人睡在洞子里,去时都带了棉衣未见有生火的。那时香火盆都在洞里,难免产生烟渍”。但是明代两百多年莫高窟香火中断缺乏管理,少数流落到此的人以洞为家也是很可能的。
▲ 在伯希和1908年的敦煌图录中,莫高窟74窟照片中的供养人被人为刮毁了鼻子和眼睛(摄影:努埃特)
▲ 在伯希和1908年的敦煌图录中,莫高窟259窟照片中的好几尊佛像断臂残破(摄影:努埃特)
如果说上述破坏跟白俄无关,那究竟跟谁有关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推断竟让人大跌眼镜!
民间盗刮佛金古来有之。由我国佛教徒辑录的一部《造像胜德灵感录》,在其“破坏佛像恶报感应”章节里罗列了70种毁佛的报应,其中有“盗刮佛身金箔,用以谋生,生皮癣,自刮皮肉而死”的故事:
“凤州城南边,有座明相寺,寺里有几尊佛像,都用金子装饰着;当地遭乱以后,有个贫民去刮金子,卖了来供给自己的生活;等到社会安定了,佛像的金彩也都刮光了;于是这个人遍身生皮癣,痒得不能忍受,常常须用东西自己往下刮,皮都刮光了还是痒,直到把肉都刮完,只剩下骨头而死了。(出自宋代《太平广记》)”
这则故事和“破坏佛像恶报感应”中列举的其它种种毁佛行为说明,民间确实存在盗刮佛身金箔、破坏佛像的现象。这个依据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在莫高窟刮佛像者,除了白俄还会不会有当地百姓参与?如果说当地个别百姓因贪婪而盗刮佛金,那么佛窟中一些没有贴过金箔的地方为什么也被盗刮,而且盗刮的非常疯狂,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驱使人们甘愿冒着“被自刮皮肉而死的”恶报去破坏佛像呢?
▲2015年杜永卫临摹复制320窟佛像工作现场
带着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在一次彩绘320窟佛像的时候,我一边描绘那些刮痕一边琢磨,人们刮这点金箔太不合算:1克黄金能打造半平方的金箔,够贴这一尊佛像的;为1克黄金冒死盗刮佛像太不可思议。从刀痕上看却不像是为了刮金,因为有些刮掉金的地方又被刮了一遍,而明显有金的地方却没有挂取,既然贪图黄金又为什么对那些明显的斑斑快快的黄金视而不见?我又蓦然想起小时候见过人家刮老墙土做药引子,突然我觉得这种刮佛金的举动会不会也是为了做药引子?如果真是为了做药引子,那就很好解释158窟卧佛像明明没有贴金,却也被刮得斑斑驳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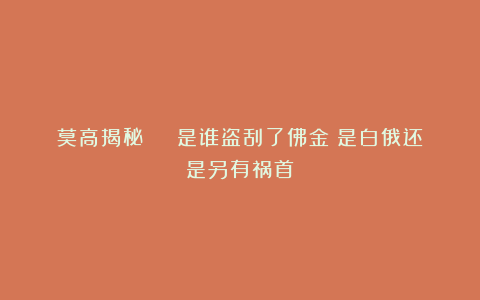
▲莫高窟320窟现佛像现状(杜永卫摄)
▲莫高窟158窟卧佛现状(孙洪才摄)
谁都知道盗刮佛像是要遭恶报的,在封建迷信时代,如果不是要紧要命的事,人们恐怕不会胆大妄为去刮佛身做药引子吧?终于有一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人血馒头是指人血浸泡的馒头,旧时民间迷信认为,人血可以医治绝症肺痨,因此处决犯人时,便有人向刽子手买蘸过人血的馒头治病[注3]。我小时候见过公审大会后拉犯人到郊外枪决的情景,曾亲眼看到有人用馒头沾脑浆的情况,当时听大人说,热馒头蘸脑浆治疗癌症。人恐怕为了活命的时候才可能不顾一切,为了活命夹边沟的知识分子可以盗食同伴的尸体,那么为了活命刮佛做药又有多难?
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江涛博士:我怀疑盗刮佛金是为了做药治病。江博士当即就回答我说,金箔在中医药方面具有广泛而深远的药用价值。并且马上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 唐朝的《药性本草》中载:金箔可”疗小儿惊伤、五脏惊病失志、镇心安魂魄”;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尤以箔入丸散服,破冷气、除风,疗惊痫风热肝胆之病”;该方传入日本后也被载入日本医学籍《增订和汉医考》,述有”真心安神、润颜,惊癫痫风热肝胆之疾”。我国著名的中成药同仁堂的”牛黄安宫丸”、”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大活络丹”等名贵中成药均采用金箔入药配方或金箔裹药。
如此说来莫高窟佛金被刮也有可能是当地百姓为了配药,就不只是白俄所为,而那些没有按金而仅仅被刮了颜色的佛像,例如被一直认为系白俄罪证的158窟卧佛刮痕,就应该跟白俄扯不上关系了。
中医取药引和采药本身就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单就古旧建筑上就有很多很做为药引子,如:老土坯 、老墙土、老墙皮、灶心土以及锅底灰等等。后来我还进一步了解到,过去人们于佛窟、寺庙找取药引子的情况司空见惯,例如寺庙里的香灰、佛像上的浮尘、佛像和壁画上面的颜料等都能做为药引子。偶尔读到一篇《从韩国佛像的鼻子谈中国的鼻祖》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韩国古都庆州附近的佛像许多都没有鼻子,不是工匠偷懒,而是佛像的鼻子被当地人割去做了药引子……虽然笃信佛教,但还是有大胆的人用刀刮下佛像的鼻子,用来配药’’。其实在中原,甚至敦煌也有一些被破坏佛像鼻子的情况,其中有没有跟韩国相同的原因有待研究。[注4]
▲鼻子被人刮去做药材的佛像,佛像正面所有突出的部分都保存得很好,唯有鼻子不见了(摄于韩国庆州博物馆)。关于很多佛像的鼻子损毁,有人说这个部位因突出而容易损毁。其实只要是雕塑专业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部位反而不容易掉落。
关于我上述推测,已多次与同仁探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专家丁淑君老师也认同我的说法,她说她早年当讲解员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当地的游客将佛像上的尘土和掉落的皮灰收捡起来,并告诉她说这是很好的药引子。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专家华亮先生也告诉我说,他们在西藏布达拉宫修壁画时,就亲眼看到藏民们把脱落的壁画碎屑精心收集起来,喇嘛告诉他说,佛像和壁画上脱落的颜色和金箔都是非常好的治疗顽疾的药引子。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中国国家地理》特约记者王心阳先生发表的一篇《一个意大利壁画修复师在木斯塘的14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寺庙里有一幅佛陀与侍从的壁画,在两个侍者的脸上能看到很明显的刮痕。费尼开始以为是人为的恶意破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当地的藏医刮取了神圣画像上的颜料用来做藏药中的药引子,他们坚信这样的物质带有医治恶疾的功用。”这段描述和华亮先生所述情况竟完全一致。
▲意大利壁画修复师费尼修复强巴寺壁
▲ 在伯希和1908年的敦煌图录中,莫高窟74窟照片中的供养人被人为刮毁了鼻子和眼睛(摄影:努埃特)这与上述意大利壁画修复师费尼看到的情况是否同一种原因?
其实早在2013年,我因调查敦煌民国彩塑传承情况,请教过被誉为敦煌文史活资料的88岁的张仲老先生。当我问到莫高窟佛像的刮痕时,老先生不加思索地告诉我说:“那是刮药引子,敦煌人过去有用佛像的皮灰做药引子的习俗,这种药引子都是用来治重病的。”我当时因为先入为主的白俄盗刮的认识根深蒂固,竟丝毫没有在意张老先生的说法。
▲笔者于2014年采访88岁的敦煌文史学人张仲老先生
下面这张图,出自伯希和1908年的敦煌图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白俄被监禁在莫高窟的十四年前,158窟就已经存在刮痕,而这些刮痕处根本没有黄金。
▲伯希和1908年的敦煌图录页面(摄影:努埃特)
后 记
就158窟卧佛被刮情况,不只是我,可能不少人都认为是白俄所为。1994年我临摹这尊佛像时,其实就已经知道该像身上没有按金,也已经对那些刮痕产生疑问,但就是缺乏探究的兴趣。如果不是孙志军先生的认真,如果不是跟老同事们聊侃,我或许永远不会做这方面的思考,依然会想当然地按照刚来敦煌之初,从前人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种固定的认识看待问题。笔者在此由衷感谢张仲、孙志军、张启农、华亮、丁淑君、江涛等先生的不吝赐教!
此外,拙文中难免存在主观臆断和错误之处,诚请诸位网友批评指正!
[注1]:1921年11月,甘肃省长公署决定,每人发给路银六两,分批解送沙俄官兵回国。至1922年3月,全部沙俄官兵离开敦煌,陆续资解天津、上海。部分留居兰州者,当时称为“归化族”,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俄罗斯族”。
[注2]:【伯希和敦煌图录】伯希和率领的法国中亚调查队于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图录。自南向北,将数百石窟编号,拍下石窟内雕像与壁画。此图册为敦煌的最早综合性记录,可追寻莫高窟在白俄破坏之前的旧貌。
[注3]:参见(清)袁枚《子不语》“还我血”篇;鲁迅 作品《药》
[注4]:http://aoment.blog.163.com/blog/static/172875929200925656057
2017-11-25写于敦煌
▲1994年杜永卫临摹复制158窟涅磐像工作现场
笔者为金塔博物馆创作《王子牧羊图》
杜永卫 曾用名:杜一田。非遗敦煌彩塑技艺传承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高级环艺设计师,教授。历任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副所长、敦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东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东京艺大客座研究员;中央美院雕塑系传统课兼职导师;兰州交大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师大敦煌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客座教授;酒泉职业学院特聘教授;江南石窟艺术指导专家。敦煌中国画研究院学术院长,《当代敦煌》总编辑。
作品曾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并赴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展出。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国驻澳大使馆、埃及开罗市政府等机构收藏陈列。敦煌菩萨银币设计获美国世界硬币大奖赛最佳奖;龙门石窟卢舍那银币浮雕获新加坡国际钱币博览会金奖。其他美术作品屡获国际、国家和省级各种奖项。雕塑作品《水月观音》获云冈国际佛教艺术大展最高学术成就奖。
品读之后
愿享同感
以 往 期 刊 推 荐
– END –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