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痕深处见春秋
砚台里的墨香总在黄昏时分漫开,像一缕穿越千年的时光密码。案头的宣纸上,墨迹未干的“永”字尚留余温,点如坠石,横若千里阵云,恍惚间竟与千年前兰亭序的笔触悄然重叠。书法于我,是流动的诗行,亦是凝固的山水。
漫步碑林,指尖抚过斑驳的石碑,能触摸到颜真卿的雄浑、柳公权的劲峭,还有怀素醉后狂草里飞溅的月光。那些刻痕里藏着盛唐的风、大宋的雨,藏着文人墨客或激昂或低回的心事。敦煌藏经洞的残卷中,无名书手的字迹带着西域风沙的粗粝,却又流淌着佛偈的慈悲,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丝路的文明脉动。
真正的书法家,当如游走于时空长河的摆渡人。他们深谙“师古不泥”之道,像黄庭坚观船夫荡桨悟笔法,像吴昌硕从石鼓文中汲取苍茫。他们笔下的线条,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与古人的隔空对话。在临摹《石门颂》的岁月里,有人突然懂得,汉隶的风骨不在碑文的棱角,而在书写者坦荡如砥的心境。
书法从不是孤立的艺术。苏轼挥毫时,胸中自有“大江东去”的豪迈;赵孟頫落笔处,晕染着江南烟雨的温柔。文心滋养墨韵,诗词的平仄、绘画的留白、古琴的余音,皆化作字里行间的灵气。启功先生强调“不读三百首诗,休提羊毫笔”,正是道出了文学底蕴对书法的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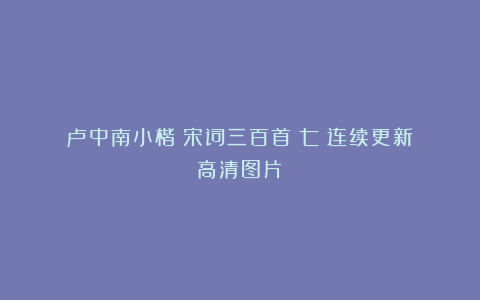
时代更迭,书写工具从狼毫变成数字笔,宣纸化作电子屏,但书道的本质从未改变。就像齐白石刻下“一息尚存书要读”,那是对文化传承的赤子之心;就像孩童在课堂上追问“捺脚为何如刀出鞘”,老者笑着回答“因你心里住着位少年将军”,这一问一答间,传承的火种便生生不息。
暮色中的砚池泛起涟漪,新研的墨汁倒映着满天星斗。那些在宣纸上游走的线条,终将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让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岁月长河里永远焕发着生机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