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CSSCI中文核心期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报《装饰》2024年第9期,标题“时代语境下传统工艺的思变、破局与新生——以“南京绒花”为例”,本号调整并增加插图)
南京绒花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三大绒花之一(其余为扬州与北京绒花),自明清时期的兴盛发展,至建国后的大规模生产,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技艺的濒临失传,这门传统手工艺历经了多次起伏与沧桑变迁。直至2007年,南京绒花被列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的技艺才逐步恢复了传承。南京绒花的众多制品样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满足了社会各阶层人群的生活需求,从鬓头花至动物绒制品,再到绒花摆件;从国内市场至国际市场,再到以内销为主,这不仅是制品样式和消费群体的迭代更替,也是不同时代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变化的积极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南京绒花的发展历程投射出我国“非遗”项目传承中的共性问题:尽管有政策助力,但制品创新、市场融入、梯队建设、破圈拓展等方面依旧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近年来,在传承人赵树宪的带领下,南京绒花展现出蓬勃生机,不仅成为江苏传统工艺品类中全国闻名甚至走向世界的代表,还积极与影视剧组、国际奢侈品牌密切合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力量。综观南京绒花数十年来的传承与演进,值得深入探讨,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传统工艺应如何适应并持续发展。
影视剧《骊歌行》人物绒花头饰 赵树宪作
一、溯古及今:南京绒花的发展历程
南京绒花,又称宫花、喜花,寓有吉祥、祝福之意。它的原辅材料是蚕丝与铜丝,制作时,蚕丝裹于铜丝之上,艺人双手拧住铜丝两端,同时向反向轻捻,迅速形成螺旋状绒条,随后再进行毫厘之间的精修打磨,直至形成栩栩如生、灵气逼真的花朵。一朵绒花的制作过程涉及十余道工序,对工匠的耐心与细致程度提出很高的要求。
制作“仿点翠”绒花饰品
追溯历史,南京绒花的起源已难以精确考证,其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五个关键阶段。
初始阶段为南京绒花雏形期,随簪花风俗的兴起而出现,唐代宫内盛行佩戴新鲜簪花,因鲜花保鲜期短且不易保存,质地柔软、色彩艳丽的绒花作为代替品,成为宫廷女眷偏爱的发髻处妆饰。第二阶段为南京绒花发展的繁盛期,由官府和手工艺人主导。明代南京地区丝织业蓬勃发展,为绒花工艺提供了富足的原料,清康熙、乾隆年间更是达到鼎盛,官府设立七作二房,绒花作坊和店铺聚集于南京城内的三山街至长乐路一带,形成了著名的“花市大街”,民国时期,城内更有绒花店铺四十多户。[1]第三阶段为南京绒花发展的起伏期,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政府主导的“改造”、“创汇”、“体改”的集体培育阶段,南京绒花先后历经了成立合作社、规模化生产、绒花厂关停、艺人离散等一系列行业起伏。此期间,南京绒花制品除少数传统产品外,大多为外销西欧地区的动物类绒制工艺品。其中仅生丝小绒鸡一个品种,在1973至1982年的10年间,外贸出口额就达百万美元,为国家换回了宝贵的外汇。[2]但批量生产的动物类绒制工艺品的标准化特性,限制了艺人进行个性化创作,在大集体、规模化生产模式下,绒花制品无法适应时代变迁引起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改变,于是国内市场萎缩,制花厂生产经营衰退,绒花技艺濒临失传。第四阶段为南京绒花发展的抢救期,在政府引导、民间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推进下,2007年南京绒花技艺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内设立了绒花坊,聘请艺人赵树宪制作传统绒花头饰与摆件,依托博物馆平台,以及工艺美术博览会等展会的推广与宣传,南京绒花技艺的传承逐渐复苏。第五阶段是南京绒花正在历经的转型期,经过十数年的不懈探索,在以赵树宪为代表的传承人引领下,南京绒花制品实现了诸多创新性的转变和创造性的发展,为这项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传承团队壮大,产量稳步提升,业务日益繁忙。2019年,“梧翊凰绒花”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应运而生,更为南京绒花的未来发展开辟了高质量、多元化的全新路径。
传统绒花小摆件 赵树宪作
二、思变创新:传承人的自我更新与突破
自2006年12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以来,虽然诸多传统技艺作为“非遗”项目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但部分手工艺项目至今仍面临着创作理念陈旧、市场萎缩、传承乏力、生存空间异化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传统工艺品与消费群体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美学价值存在不匹配的矛盾。身处时代洪流,受社会变迁对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冲击的影响,南京绒花也曾面临以下问题:传统制品难以激活现代市场、现有的传播空间参与度与互动性不够,导致年轻人对南京绒花的文化认同度较低、从业者与学艺者日渐凋零等问题。但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南京绒花现阶段已经摆脱市场疲软、传承乏力的困境,不仅在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热销,还突破原有界限与影视剧制作频繁合作,更聚焦国外时尚奢侈品牌融合创新,实现了“活态”传承。取得如此成就,首先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在此基础之上,凭借传承人自身精湛的技艺和勇于求变的精神,以及对市场机遇的敏锐洞察力,适时引入跨界力量,为传统绒花工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绒花制作步骤图之一
南京绒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树宪,尽管因左腿高位截肢而身体受限,却因此锻造出坚毅执着的个性。虽身有残疾却善于思考。自1973年进入制花厂,赵树宪先后在设计室和各道生产工序上工作过,曾担任绒花生产车间主任,创立并管理绒花外加工点,90年代下岗后他主要从事文化产品设计与管理工作。多样化的工作经历让他深谙绒花的生产流程,展现出强大的设计与创新能力,熟悉代工点与成本核算,亦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2007年重回绒花坊后,赵树宪亲历了行业的起伏,深感自我更新与突破的必要性,结合过往经验,他开始基于设计、市场、传承等多重维度深入探究:南京绒花技艺层的创新、营销层的开拓、以及传承层的优化。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赵树宪在绒花坊内制作绒花
1、审美观更新
南京绒花复兴的契机出现在2009年左右,正值汉服文化的回归热潮。汉服妆造在年轻人中日渐流行,尤其发簪配饰,可随季节更迭,适应不同场合、各色衣裙搭配,演绎不同风格。但金银、珠宝玉石做成的发簪价格昂贵,与年轻群体的消费能力不相符,这是南京绒花对接市场的一次宝贵的机遇。绒花作为古代女性发髻的装饰,如今用以取代珠宝,既解决了价格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冲突,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多样化审美搭配的需求。
赵树宪敏锐的把握住这一机会,但绒花发簪的现代设计并非简单的复制或替代,一方面不能直接沿用古代的式样,传统题材类绒花制品已背离大众审美,另一方面若不能在保持传统工艺特质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那么绒花制品又会重蹈上世纪80、90年代集体化生产的覆辙。在深入研究绒花发簪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后,探寻绒花制品与现代消费需求的连接点成为了产品设计思考的重点,即从生产者视角转换为消费者视角,基于消费者喜好与需求进行设计创作。在设计上,赵树宪将旧时女子鬓头绒花中抽象的花型设计转为以具象花卉题材作为主要对象,如百合、桂花、菊花及果实类样式等。在配色上,尝试冷色调和低饱和度色系,增强现代设计感,带来新的感官体验。通过这样的创新,传统绒花制品被赋予了新的设计表达,既保留了绒花本身的“非遗”内涵,又迎合了现代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充分展现出绒花独特的优势和价值,改版后的绒花发簪一经推出,便深受欢迎,迅速适应并打开了市场。
绒花发簪 赵树宪作
2、工艺观更新
赵树宪认为南京绒花的原材料及工艺并非一成不变,适度的开放性和融合性是推进该技艺存续与创新、培育该制品适应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绒花的主要材料包括蚕丝与铜丝,其中蚕丝因光泽度高、呈色性强,使得成品绒花色彩鲜艳、流光溢彩。而铜丝遇热后易于塑形的特性,使其能够根据绒花样式制成不同规格的花骨,生成千姿百态的绒花制品。为了更好地展现绒条的色泽,他萌生了研制“仿点翠工艺”的构想,点翠工艺原是古代金银饰品制作中的一种特殊技艺,以孔雀、翠鸟等禽鸟的羽毛为料,剪裁成不同形状,粘贴于头饰、冠饰等之上,因其精艳绚丽的色彩深受宫廷喜爱,然而由于原材料获取过程中的残酷性,这门技艺已经销匿。近年来,有人用鸽羽、鹅羽等羽毛代替“翠羽”,但光泽与色彩相差甚远,无法复刻原貌。赵树宪深谙蚕丝的材质特性,通过反复试验,采用特殊方法对蚕丝进行修剪和熨烫处理,使加工后的绒条和成品既柔软纤细又光泽华丽,色彩、明暗、饱和度均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具备了翠鸟羽毛的质感。这一创新不仅重现了传统点翠技艺的效果,还突破了翠羽颜色种类的限制,炼染后的蚕丝色彩更加丰富,为色彩搭配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点翠”绒花佩饰 赵树宪作
此外,制作过程中还融入了掐丝工艺,使“仿点翠”绒花饰品达到最佳效果。“仿点翠”妆造首饰工艺品集绒花、点翠、掐丝三种精湛的工艺为一体,不仅优化了绒花技艺本身,更彰显出不同“非遗”工艺间的融合,是工艺创新与突破的重要体现,展示了绒花制品丰富的潜在发展空间。
3、营销观更新
为了更好的对接市场,南京绒花传承团队制定了三大营销策略,一是消费分级。有针对性地对绒花制品进行精确的市场分层,面向不同顾客群体提供多样化产品,涵盖服装秀饰件、橱窗装置设计到妆造首饰、案头小品等多个领域,既有对标奢侈品牌的高端定制品,也有专为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与汉服爱好者设计的中端制品,还有面向一般人群的大众工艺品。消费分级策略丰富了绒花品类,拓宽了市场与消费人群。不但拓展了南京绒花的发展空间,也为国风文化的复兴贡献了力量。
“点翠”绒花佩饰 赵树宪作
二是创建多元化消费场景。传承人团队在绒花坊内向顾客展示绒花工艺的同时,也进行传统文化的输出与传播。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师傅们精湛的技艺和优美的制品直观地吸引消费者,营造的实践消费场景不但能够刺激消费者对绒花工艺品产生消费愿望,还会吸引他们去体验造物过程中的仪式感,塑造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此外承人团队经常受邀参加各地举办的联展与传统文化节日活动,如西塘汉服周、香港南京非遗展、米兰世博会“南京周”等,以节日为媒介,利用特定场合下衍生出的消费情境,调动参观者的互动热情,激发他们主动参与传播,吸引更多的游客消费者。
三是迎合年轻人的消费偏好。近年来,“短视频电商”模式迅速崛起,以抖音、小红书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 + 电商”模式,已成为众多年轻消费者购物的主要途径。[3] 传承人团队意识到这是传统工艺与现代消费方式对接的契机,并迅速在抖音APP上开设了南京梧翊凰绒花店铺,并由专业团队负责运营,定期发布作品视频,吸引粉丝关注与互动。目前已拥有1.6万粉丝,同时淘宝上也开设了旗舰店,拥有1.49万粉丝。南京绒花敏锐且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网络媒介,对品牌与产品进行宣传营销,开拓线上渠道进一步扩大了消费市场。
线上线下营销渠道的融合共建形成了共振效应,突破了传统传播的层级和认知范围,实现了裂变式的传播效果。这不仅开启了传统工艺与现代市场对接的新思路,还构建了南京绒花消费场景多样化、消费选择多元化的新兴模式,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可行性营销路径。
2024迪奥夏季男装无檐便帽帽花 南京绒花团队设计
三、破局纾困:南京绒花的传承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间工艺多采用个体或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相应的传承方式多为师徒或家族传承。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机制,师徒相授过程中易出现目标不确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此外,部分项目的传承体系仅限于家庭内部,这些都易导致传承队伍的单薄和不稳定。还有一些“非遗”项目易依赖扶持政策“保护”,不愿尝试创新与转化。传承方式主要表现为活动式展演与教学性授课,实质上是传播而非深入传承且范围相对狭窄。此类普及性的文化宣传活动并未真正激活市场形成生产性保护,这些现象反映出“非遗”项目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传承梯队构建存在的局限性和传承形式固化导致的依赖性。这些问题亦曾对南京绒花的传承方式构成困扰,但现今南京绒花已完成破局,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传承路径。
1、优化传承模式
得益于政策的扶持、民俗博物馆的平台以及多方面的资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得以蓬勃发展:2011年第二届南京名城会开幕式定制了200件绒花胸花,知名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以南京绒花为元素,为影视明星姚星彤打造了参加2012戛纳电影节的礼服,从而开启了南京绒花订单量激增的序幕。但2013年赵树宪开始带徒授艺后,一些徒弟中途放弃,未能坚持到底;另一些虽掌握了一定技艺却独立门户,因学艺不精,同样未能持续。这些现象引发了赵树宪对南京绒花传承模式的思考,他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南京绒花传承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以下改变:
一、组建职业团队。只有通过规范化管理,才能形成有约束力、凝聚力、创新力的传承队伍。严格的管理体系,明确的职责和任务,以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协作精神。从而确保高质量且稳定的生产链,保障技艺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形成梯次结构。为了解决现阶段传统工艺创作主体日益老龄化与需求主体普遍年轻化的矛盾,赵树宪搭建起以专业院校本科、大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团队架构,让年轻的设计师直接参与创作中,与经验丰富的师傅携手合作,激发创新设计灵感。老中青传承梯队的建立,系统地聚集了优秀的传承人才,解决了传统绒花制品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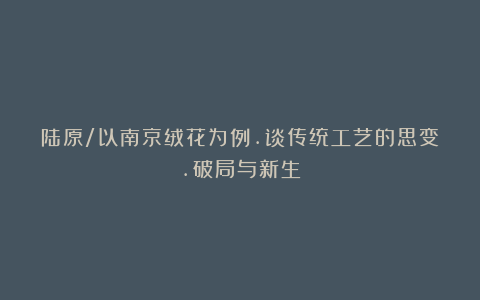
绒花肩饰 赵树宪作
三、提升队伍质量。南京绒花团队中的青年骨干传承人,包括南京非遗学院绒花班的教师,以及南京艺术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具备专业的设计能力,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绒花技艺抱有浓厚的兴趣,是增强团队核心竞争力的知识技能型人才,为南京绒花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共同致力于推动南京绒花的高质量发展。
2、创立自有品牌
2017年,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颁布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旨在鼓励传统工艺从业者合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注册产品商标,并提出培育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知名品牌。这是国家通过宏观政策,一方面倡导创建“非遗”品牌,激发传统工艺创新生产模式,使之适应现代市场,另一方面,这既是保护生产成果的举措,也是对知识产权和技艺可持续传承的保护。事实上继组建高质量传承团队后,南京绒花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期,但随着“汉服热”兴起带来的销售商机,绒花市场突然出现了大量仿制品,有的甚至冒称由赵树宪设计制作,一时间各类制品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这使得南京绒花团队意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然而,打造“非遗”品牌、创建公司对南京绒花既是机遇亦是挑战。2019年8月赵树宪团队募集资金创办了股份制企业,同时为南京绒花注册了“梧翊凰”商标,开启南京绒花的品牌化的新方向。鉴于外地绒花的实例,团队经过深思后明确了几点:
一、坚守“非遗”品牌的核心要义。传统工艺的市场化发展固然重要,但其技艺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更不容忽视。在传统工艺中引入现代经营理念,利用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是一种新的融合发展模式,但是新旧业态的互嵌共生,[4] 必须建立在工艺品与品牌特色相契合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品牌赋能,提升传统工艺的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绒花案头小品 南京绒花传承团队作
二、构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公司运营模式既不是“家族作坊”式的单一生产,也不是工厂流水线的标准化加工,而是采取多元化的组合方式:“工作坊展演+高端定制+专业代工”。根据顾客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对订单进行有效分流,绒花坊专注于展演活动,公司本部负责高端制品的设计与生产,同时将部分大众化制品的生产任务交给代工点。这里的“专业代工”并非绒花的简单复制加工,而是由团队核心成员常驻加工点亲自指导生产,进行技艺传授和质量监督,公司的质量专员不定期进行抽查,以确保所有上市制品均达到质量标准。这样既保证了品牌制品的品质,又有利于培养新生的传承力量,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实现精准的人岗匹配。“梧翊凰”绒花团队中每位成员均精通绒花制作的全部工艺和流程,并根据各人专长进行明确分工。市场策划、生产计划制定、设计制作、质量检验、线上服务、门店销售等,皆由专页人员负责。大家各司其职,通过多手段、多方面的协作,共同打造“梧翊凰”绒花品牌。
赵树宪接受VOGUE时尚杂志访谈
四、另开生面:“非遗”圈外的多元共生
随着传承人观念的更新、绒花技艺的守正创新、生产传承模式的优化以及非遗品牌的建立等措施的实施,南京绒花在传统工艺美术界逐渐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得益于工艺品市场上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南京绒花引起了不同行业的高度关注,服饰、影视剧、奢侈品牌这些生产经营中从未涉足的圈层,如今被南京绒花一一触及,逐步实现了传统工艺与跨文化领域的深度交融,在满足年轻消费群体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获取了他们的深层认同和情感共鸣,体现出文化自信的情感表达与消费诉求。当下,南京绒花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化象征意义,成为时尚界的一个元素,并在追求跨界创新和多元共生的过程中,不断精进技艺,另开生面,焕发出新的生机。
1、跨介续生
2010年,一位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在参观民俗博物馆期间,对南京绒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返京后,他积极推动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了赵树宪创作的32件绒花头饰,并在服装设计领域中大力推荐,迅速提升了南京绒花的知名度,同时也开启了南京绒花跨媒介融合与转化的的新契机,实现了从非遗传承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的演进。由于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近年来,南京绒花相继为众多热门影视剧提供了定制化服务。2017年《延禧攻略》影视剧组慕名邀请南京绒花团队为剧中人物制作头饰。面对这一未曾涉猎的领域,赵树宪深入研究了相关史料,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团队为剧组定制了19款精美的发饰。该剧热播后,剧中富察皇后所配戴的蓝色系头饰迅速成为消费者争相购买的热门商品,随之带动了线上线下店铺的销售繁荣。2024年5月热映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女主角杨幂的佩饰——一只栩栩如生的九尾狐也出自赵树宪之手,这部剧基于漫画改编,本无需溯源历史,但在主要配饰上依然选择了南京绒花,可见影视界对其的高度认可。更值关注意的是,在该剧宣传海报的设计中,九尾狐绒花制品作为主图形元素,成为版面的中心,这突破了过往以人物为主的设计惯例。绒花不再是辅助角色,而成为了传递信息、宣传剧情的关键媒介。
影视剧《延喜攻略》人物绒花头饰 赵树宪作
南京绒花之所以在影视界获得认同与成功,归因于自身传承与外力传播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这种结合对南京绒花的扩布与延伸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保持自身技艺价值和核心优势的基础上,南京绒花通过与多个影视作品的合作,利用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覆盖面所产生的长尾效应吸引到更多受众的关注,而这些受众的主体多为对时尚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年轻女性观众,非遗文化和国潮文化的叠加与融合,更加速了他们对南京绒花的文化认同与共情。
由此,借助现代媒介的力量,南京绒花跨越了传统与现代、“非遗”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原本集中于传统工艺品市场范围的消费活动,在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的推动下,触及不同领域的潜在观众群体,形成了传统文化的积极输出,实现了时代语境下的传承与新生。[5] 这种跨介的方式,不仅解决传统工艺专业性强,传播面窄等普遍存在问题,也为南京绒花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为其创新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如今,南京绒花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已然成为传统工艺与影视产业深度融合的典范。
影视剧《狐妖小红娘》人物绒花头饰 赵树宪作
2、破界共创
长久以来,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庞大消费潜力对国际奢侈品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品牌相继采取在地体验、文化共鸣等策略,试图进一步融入本地文化语境,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便是其本土化策略之一,南京绒花在一众传统工艺品类中已具备一定影响力和认可度,作为历史文化悠久,同时又在技艺传承中持续创新,不断探索适应市场、迎合现代审美、展现内在文化价值的传统工艺,刚好契合了国际奢侈品牌寻求本土化合作的需求。
2017年,奢侈品牌爱马仕邀请南京绒花团队共同参与主题橱窗展示设计,此次设计突破了绒花既定形态、尺寸及工艺的限制,是赵树宪与品牌方设计师共同探索绒花工艺边界的积极尝试,绒花不再局限于花卉、动物等造型的陪衬,而是化身为一根栩栩如生的巨大彩色羽毛,作为陈列设计中的主体,和蓝色飞鸟共同营造出爱马仕丝巾随风飘扬的生动场景,绒花羽毛的质感、飞鸟的灵动与丝巾的华美相得益彰、完美融合。此次设计的每个环节都体现出我国传统工艺中主张“因材施艺”的巧思与创新。制作过程中,长度1.3米左右的绒花羽毛对工艺要求极高,传统的以铜丝为骨架,固定小体量绒花制品的方法无法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和支撑力。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赵树宪秉承“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的观念,与设计师多次沟通、反复试验,最终突破了绒花骨架的材料与工艺的瓶颈。采用木头取代铜丝制成羽毛的主茎,并在四周打孔,细羽以铁丝为骨骼,与蚕丝缠绕制成绒条后进行熨烫,再插进主茎侧面的细孔里。这一方案确保了绒花羽毛的生动逼真和持久不变形,使得合作设计顺利完成。
这次合作是手工艺人与品牌设计师在技术与艺术领域的交流与碰撞,是传统工艺与国际奢侈品牌之间的联动跨界,也是“非遗”文化与现代时尚潮流的有机结合与共同创新。它拓展了南京绒花与高端定制市场的合作新途径,开辟了南京绒花传承与发展的新视角。之后,南京绒花又与迪奥、阿玛尼、帕尔玛之水、“Whoo”、周大福珠宝以及问道手游等品牌成功合作,消费者对南京绒花的消费逐渐从功能与形态转向了对其象征意义的认同。23年底,赵树宪还接受了国际时尚杂志VOGUE的采访。从“非遗”领域到服饰领域到影视剧和时尚领域,南京绒花真正做到了破介跨界的交叉融合,让人们看到了它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同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传承。
与爱马仕合作的橱窗设计–绒花羽毛 南京绒花传承团队作
五、结语
历史的长河中,每项传统技艺都曾在人们生活中发挥其价值,闪耀其光辉,但时过境迁后大多日渐式微,这成为许多“非遗”项目和其传承者必须正视的现实。“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并发展与传承,关键在于其物质载体能否在保持原真性基础上与时代语境融合,并成功对接现代消费市场,通过创造经济效益,确保传承人的技艺得以延续,从而形成一个长期的良性循环,这亦是对“非遗”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的可行性路径。南京绒花作为现阶段“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典范之一,其传承团队擅于利用平台和资源,敏锐把握市场脉动,注重传承人观念的自我更新,不断求新求变,勇于打破技艺、传承、生产的“藩篱”,实现跨界共生,使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在当下焕发新的活力,体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核心要义。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中提出了“实施传统工艺品牌扶持计划”,南京绒花的传承之路恰好印证了通过建立品牌来激发“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和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也为其他传统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轻工》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24
[2]陆晔:《南京二轻工业志·工艺美术》[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66
[3]董蓓:非遗+短视频,让传统老手艺“破圈”[N],《光明日报》,2021年9月12日,第5版
[4]吴立行:《从技术更新到多元共生——山口村“青田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前世今生》[J],《装饰》,2024年第1期,第18—25页
[5]郝丽丽:《现代媒介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J],《青年记者》,2017年第9期,第19—20页。
采访对象:
南京绒花传承人赵树宪
作者简介
陆原:女,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传统工艺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