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布达佩斯Mücsarnok博物馆
GB 戈特弗里德·勃姆 Gottfried Boehm
HDW 这些作品是同时创作的么?
LT 不,我从不同时画两幅画。我需要高强度的集中。首先,作为画家,我画画的快感来源于此。这对于图像的强度也至关重要,我要是在两幅画之间来回切换就无法达到那种强度,尤其是当这些画同属一个系列的时候。
GB 而湿盖湿的画法意味着这个过程不会持续太久——也许一到两天?
LT 在这个展览里的画都是一天完成的,每一幅!
GB 就连那些大画也是么?那肯定是满满当当的一天。
LT 大画也是。漫长的一天,确实。
GB 肯定有失败的瞬间吧,画坏的时候。
LT 这经常发生,这样我就涂掉重画。我过去常常把画涂掉因为当时没钱买新画布,现在我干脆把画坏的扔掉。对画的不确定是一直有的——它到底够不够好?我会保留一两个月,如果两个月后再看它还是不行,我就扔出去。早年我画了大量作品,也毁了很多。有一些遗憾,因为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有些画不该毁。那时我有一种超强的自我审查,因为我32岁才有了第一个个展,进入画廊圈。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孤立中工作,这意味着你真的会反复检视自身。同时你当然也会犯错误,因为你是在孤独地进行这个过程。
HDW 艺术家应该是,或继续是自己全体作品(oeuvre)的裁断者么?
LT 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很多画家有大量二三流作品传世,比如前面谈到的塞尚——我不想重蹈覆辙。对我来说,一幅画行不行有一条基准线——如果不达标,就该走人。
GB 所以你有一个检验的时间?这段时间这些作品是在你工作室放着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LT 在工作室。
GB 在我的印象中一幅画如果脱离了它产生的空间到了别人家里会有一些变化。
威尼斯格拉西宫“皮肤”展(2019)现场
LT 是的,有时候效果非常糟,尽管也有好的例子——比如本纳德·汉洛瑟(Bernard Hahnloser),他在我的伯尔尼艺术馆个展上买了一幅抽象画,挂在一幅雷东(Odilon Redon)和一幅马蒂斯中间。他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效果很引人入胜。如果你看到作品在一个藏家家里单独挂在墙上,在沙发或其它什么家具上方,它就变得有装饰性了。我不介意是挂在别人家里或者是这样的展厅里,只要空间是完全中性的。
GB 沙发对艺术来说成了一个严肃问题!它总想伸张自己。
Luc Tuymans, Der diagnostiche Blick II, 1992
Luc Tuymans, Der diagnostiche Blick IV, 1992
LT 比如在“视诊图”系列中,一个藏家把《视诊图2》退回来了,现在收藏在克雷菲尔德美术馆。他说:“我没法跟它生活在一起。”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他还说:“我觉得画真的很好,但我无法直视它,它太有对抗性了。”
GB 我们终于说到一个重要的点上了——像这样的绘画如何介入日常生活,介入社会进程,它们如何对产生它们的社会发生一种反哺的效应。
HDW 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么?
GB 是的。我经常觉得这个效果是皮下(subcutaneous)的。最开始什么也没有,然后它开始在岁月长河中缓慢地改变感知和行为,就像一种顺势疗法(homoeopathic dosage)。
LT 呃,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自己就受不了。首先,我自己家里没有挂任何一幅我的画——我们有挂别人的画但没有我的,因为我能看到自己的错误,它们总是在场。看我的画挂在别人家里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我被邀请去用餐,我总是背对着画而坐。对我来说,我的画总是一个异质性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干扰。
HDW 这把我们带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全体作品”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意味这什么?比如,你会成组或成系列地画画,对么?
Luc Tuymans, Mwana Kitoko, 2000
Luc Tuymans, Leopard, 2000
LT 不经常。有时会有一个初始的主题,比如在《瓦纳·科图克》(Mwana Kitoko,2000[刚果语“漂亮男孩”])那个系列,几乎是新闻性的。或者在“视诊图”系列中,有两三幅在这次有展出。但是如果你能整个系列一起看的话会更明白。我一直都想以他者的目光看一遍我自己的展览。这是不可能的愿望,但是哪怕有一瞬能以完全疏离的眼光看看自己的作品也是好的,这是个挑战。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在一定距离外感受绘画,让绘画自己发声。比如,一个来自火奴鲁鲁的人就从来不喜欢我的画。他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看了我的展览,还是不喜欢。大约一个月后,他开始梦到那些画,它们又回来找他了,然后他就变得满腔热情——就像改信宗教一样!画可以在时间中发生作用。当年我看《前厅》时,它的复杂性我还看不清,现在才能看清。绘画是没法走回头路的,我可以制造一幅纯技术意义上的复制品,但那只会是个赝品。
HDW 而且那么做也没什么意义,不是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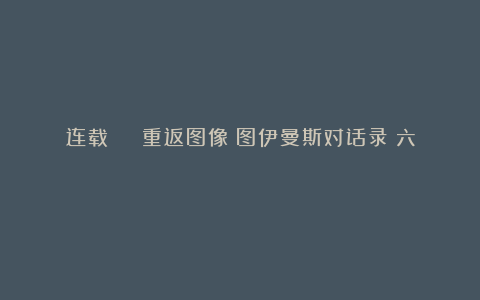
LT 这就要回到我们前面的讨论,我当时说有一张画是假的格列柯,你马上就能看出有点异样。
GB 你会保留自己的作品么?有很多理由去维持对自己作品的控制,因此我很好奇你会不会留下那些你认为还有问题悬而未决的作品?
LT 我没有像里希特的《地图》(Atlas)那样的东西。我确实会保留所有视觉素材,但不成系统。我一直不断在搜索图像、画素描——这些我全都留着。可是我从不保留自己的绘画。正如我说过的,我觉得那很烦人,我不想迷恋自己的作品。当一幅画真正完成时,它就完结了。我觉得展示它,在美术馆的语境下运用它很有趣,可是在那一刻我已经从它身上剥离开了,已经开始画新的画了。从前,我还会为自己创造了点什么新的东西而沾沾自喜一两周。现在我完成一幅新画,幸福感只能维持两天!纯真消逝了——我训练了自己,获得了知识和技术,对自己在做什么了如指掌。
GB 不过你也抵达了更高的高度。
LT 是的,你作为画家成长了。我逼自己去面对新的挑战,在尺幅上,在视觉复杂性上,但是现在我的工作无可挑剔——跟早年那些浪费时间的日子很不一样。我想,到了某一个节点,当你达成了无论是事业还是人生上的目标,作为一个画家你应该往后退一步,往更深处走……或者尝试迈出别的方向。
HDW 你是说日常习惯会让魔法消失么?
LT 不是,而是你变得越好,那些压力和期待也会抵达非人的地步。当我完成一个个展,能够退回自己的世界,只是创作——这些是最幸福的时刻,这时我感觉最好。当然画画一开始都是折磨,可是当完成过半的时候,它就开始看着对劲了,这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个画家能做到什么了,这些是观众看不到的。
HDW 所以,对于开始有一种恐惧?
LT 是的,就像怯场一样。
GB 你希望观众更深入了解你的作品么?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觉得有趣么?
LT 是的,我认为这种讨论很能激发我。我们一起聊我的画对我来说更难,因为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摒弃了艺术史和参考资料,直接审视画面中哪些部分有冲击力,哪些部分画得好——这很重要,尤其从长远来看。儿童面对绘画时的反应意外地敏锐,意图完全清晰。比如,我在根特有一个儿童项目,当他们看到其中一幅娃娃肖像时,他们笑了——作品一下子“击中”了他们。
GB 在艺术史和批评领域,很少有人尝试理解能够支持绘画的那种具体的智识。
LT 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像乌尔里希·卢克(Ulrich Loock)这种人,试图深入绘画的表皮之下,围绕它建立起一整套话语,但是这在艺术批评领域里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现在艺术批评已经在自我繁殖了。策展人们不是艺术家,但他们几乎把自己当做艺术家那样来塑造艺术家。一种去视觉化的趋势也在发生。
GB 很难对抗这种趋势,图像越来越泛滥,而深入图像的能力越来越稀有。
LT 而且也正在变得同质化,注意力时长也很有限——如果你算一下人们平均在一幅画面前停留的时间,通常是十五到二十秒。也许他们真的有被吸引,但通常还是看得很匆忙。
GB 我在一个博物馆里对着原作跟我的学生开讨论课,我们在一幅画面前呆两小时。我用五分钟就交代完跟画有关的信息。我不允许他们掉艺术史书袋或者回过头去参考——那些知识都是现成的。我讲完就完了,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再回到画前,我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尽管课程长达两小时,学生们都接受了,并且最终这门课变得很受欢迎。慢慢地,这培养了他们发现事物的能力。
LT 鲁本斯的画属于那种在创作中就考虑观众的绘画,从尺度就可以看出来。我很清楚在他之前没有哪个画家在这么大的画布上作画。他实际上是他那个时代的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iMille,1881-1959,美国电影导演,好莱坞奠基人之一),从一开始就利用一种预设好的图像,在巴洛克时代以一种向心(concentrically)的方式组织画面,以便在一定距离外被感知。这就是鲁本斯和他的工坊做的事情,慢慢地这一概念成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面向。绘画效果被用来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毕竟,那时候的教堂内部基本是空的,他把它们填充起来了。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
HDW 保罗·委罗内塞呢?
GB 他也是,还有提香1518年的《圣母升天》(Assunta, 或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挂在威尼斯的弗拉利荣耀圣母教堂。那幅画足以跟教堂巨大的空间竞争,成功让空间得以聚焦。不过我认为在他之前这样的例子很少。
Theodore Géricault, Raft of the Medusa,1818-19
左滑查看《美杜莎之筏》部分研究草图
LT 后来面向观众、大众的理念一直贯穿到席里柯(Géricault),他的《美杜莎之筏》(Raft of the Medusa,1818-19)也是一幅巨作,一幅失败的大师作品。在这幅画里,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背过脸去,而行动看起来更加退远。尽管席里柯是个大画家,但《美杜莎之筏》不是一幅特别强的作品。我觉得他为这幅所谓的“失败的巨作”所作的研究底稿实际上更有意思。
HDW 他为这幅画做了殚精竭虑的准备工作……
LT 这恰恰是画失败的原因。
HDW 我记得他甚至在工作坊里复制了那艘筏。我们知道很多大师作品就是因为花费了太长时间去准备研究而失败的。比如我就不认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是杰作。
LT 它一直让我无感。
HDW 《格尔尼卡》有几百幅研究稿和草稿,跟罗丹(Auguste Rodin)的《地狱之门》(The Gates of Hell,约1880-1917)一样。罗丹做了二十年,但我想最终他失败了。
LT 在这种情况下是野心的无边无际导致了失败。我认为最好的存世作品是那种你未能完全把控的。
GB 是的,你在那类作品中能感受到一种肌肉紧张和野心,好像在说:“现在我一定要搞出点什么名堂。”
LT 我也曾经在这方面尝试过,不过就像我说的,“奇观”永远不会是赢家,看看自己到底走多远会走不下去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当我面对类似主题公园、迪士尼、耶稣会这类题材时,它们都跟某种意识形态有关,对此类图像容易有一种不假思索。对我来说,只存在对图像的质疑,并且从宗教切换至娱乐也很有趣——你能看到它们是如何交战的。最大的画未必是最好的画。
Luc Tuymans, Wonderland(2007)
慕尼黑艺术之家“当春天来临”展览(2008)现场壁画
“布达佩斯对谈”已完结,请期待“巴塞尔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