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守护未来,一切必须重新开始。——雅克·德里达(1994, P175) 非人力量建构了人类,并为人类提供了藉以超越自身的条件与手段。在我看来,通过承认非人力量塑形与生产的功能,我们可以推进反人本主义的进程。——伊丽莎白·格罗兹(2005,P186)
人类世的诊断提出了一种新的地质纪元,它将人类定义为具有地貌形塑能力的存在,其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可与非人力量相匹敌。在石炭纪化石燃料的驱动下,这种社会地质学标志着非人的行星力量正在崛起,其物质—能量催生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如果说晚期资本主义的人类生活以安全化的生物政治、广泛渗透的经济与文化商品化为特征,那么人类世的命名则提醒我们关注:生命的生物政治具有更广阔的矿物地理学维度。在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中,社会与自然因果交织,加上人类作为地质存在的“再自然化(renaturalising)”,这些都表明了在人类世地缘政治及其主体化模式的语境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非人自然与地质能力。此外,这种关于地质存在的新理解重构了对人类能力的时间与物质想象,它超越了化石燃料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化,转而思考社会如何通过地质被构造(并因此在政治上它以政治和极端非政治的方式被建构)。然而,目前没有任何地方将地质主体化的地球物理、基因组学和社会叙事放在一起考虑,来质询这些地质能力。它们不仅仅是影响地球的力量,更是主体共享的力量,也就是构成并分化身体与集体生物政治形态的地质力量。
通过将地质视为人类世语境下当代主体性的基本层理,我们开启了对“地质生命以何种形式支撑主体性”的探问;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这种地质生命如何孕育出更为广阔的非人思想潜能,并揭示那些与化石燃料(进而与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结的主体性生活形态如何被毁灭。进入这种地质生命的长时段感知方式之一,是回望古人类化石的遗存与证据基础。这些化石支撑起人类物质与概念的考古实践。实际存在或想象中的人类化石展示并见证了灭绝与生存的形式,为我们思考“作为地质力量的生命(life as a geological force)”以及人类世的“地质逻辑(geo-logic)”提供了关键线索。
本文探究了我称之为“地质生命”的概念,它强调了人类构成中的矿物维度。这一维度在当前社会思想中尚未充分理论化,但对化石燃料的物质、时间与身体概念至关重要。通过将化石视为人类生成叙事中的物质与话语节点,我主张一种“地质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严肃对待我们的生物(或生物政治)生命,也将我们的地质(或地缘政治)生命纳入人类世主体化模式的关键考量。
尽管“生物政治转向”已引发了对身体完整性、分子层面以及多种安全机制的关注,但“地缘政治”(作为地质生命的体现)尚未被充分确立为一种理论取向。在人类世及其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动员下,它必须直面新形式的地质效应和行星变化。人类世将人类定义为一种地貌力量,从而承认了化石燃料开采和晚期资本主义形态对地球的影响。然而,我们该用何种语言来描述这种地质生命、以及它的辖域化和(无)形体显现?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些地球力量的背景下谈论“深层时间”与“非人开端”,以提出一种生成性的矿物政治(a generative politics of minerality),而非单向的破坏性政治?换言之,我们需要将地质视为一种差异化的行星栖居与身体认属的实践(praxis),而不是一种外在性(externality)。
虽然在许多学科里,“地质”正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支撑这一集体地貌事件的“地质主体”仍是一个未经充分探讨的概念,其建构常带有隐喻性(例如将地质纳入现有的生物政治模型)。这种地质主体化的模糊性在可持续性话语中尤为突出。这些话语虽然试图寻求更持久、对地质影响更小的生活方式,目标可嘉,但往往忽视了“我们”对化石燃料所欠下的地缘政治与进化债务,甚至忘记追问:为何对化石燃料的利用会成为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协作性工程?化石燃料的地球化学特性如何支撑晚期资本主义主体的地缘政治生命(或说,如今已成为人类世的新地质主体)?我们有许多方式可以切入化石燃料及其地质物质“生命”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以人类世为启示,将自身视为地质主体——不仅具备地貌行动能力,还与被动员内化的地质力量存在共性——便能辨识出那些支配并激发从属关系的协作节点,进而揭示身体和行星层面的(去)沉积作用((de)sedimentations)。
结合新的地质主体化模式,人类世给作为地质时间存在的人类定义了一种新的时间性。人类世将地质时间纳入人类的身体之中,重新聚焦于主体内部非人力量的时间性:关注地质纪元的存在、进化与终结的阈值,以及由于全新世(the Holocene)的终结而被重新定义的新人类(humanity)。人类世的概念是理解人类作为集体存在及地貌行为主体在时间、物质和能动性方面的新真理;人类不仅是影响地质的存在,更是地质内部一种无节制的力量。它促使我们将自己想象为地貌能动者(geomorphic agents),并将我们的存在方式视为地质性的,而非纯粹生物性的(一种超越生物或非人的生命活力),进而在物质生产与人类政治身体的维度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向。作为地貌能动者,人类明确与其他地球及地外力量并置。这些力量通过利用和内化地质力量,具备了灭绝和行星效应的能力,从而将先前化石化过程中的的“地质权力”(geopower)据为己有。如果按照格罗兹(Elizabeth Grosz)的说法,地质权力是被资本化的物质潜力,那么地缘政治便是这些资本化模式的政治形态。因此,政治问题始终与地质力量及其矿物化过程深度交织。
人类世为人类提出了一种史诗般的行星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兼具物质性、象征性和虚拟性。然而,相较于一味思考人类所造成的“影响帝国”,我们不如从全新世终结的主体出发,开启另一种思考路径。与其接受“人的时代”(age of man)中主体的单一命名,不如深入地质生命的史前史,通过一种受地质生命差异化力量影响的身体性(corporeality)释义,来抵抗同质化的殖民视角。地质生命的深层历史或许能为更具生成性的气候未来提供阐述,打破“化石燃料主义(fossil fuelism)”的灾难性再生产,并为人类内部的非人力量提供另类想象。
为此,我希望安排一场两种化石主体的适度对话,这两个主体分别定义了人类世叙事弧线的起源与终结。如果说,起源保存在被遗忘的终结地层之中,那么新的起源叙事就有可能扰动终结之现实,并发掘出地质主体性的其他理解路径,这些路径会质疑人类世关于全球地质能动性的统一主张。正如本文开头引述的德里达所言,对未来及其政治可能性的关注,需要以对原初条件的理解为前提。德里达认为,继承需要对继承之物及其传递方式保持警惕:“我们继承了它,就必须守护它。”如果起源是重构未来可能性的潜在扰动点,那么守护未来就需要与化石的交替时空对话,它们召唤着地质生命的过去和未来。化石作为地质记录的物质结构组织者,不仅承载着地质时间的形塑过程,也可能成为我们反思自身所处地层时间性的一个关键入口。
第一部分:跨越时间的化石对话——论地质生命
想象一下两种化石之间的对话——一种是人类世的未来化石,另一种则是人类起源的史前化石。这场对话旨在开启关于地质能动性、时间性与非人生成的讨论,这些议题虽潜藏于生命之中,但往往在生物政治或地缘政治的理解框架中被掩盖。
山脉和火山的长剖面图,展示了地层和各种动物。(Colored engraving by J. Fisher after T. Webster and F. Buckland. Webster, Thomas, 1773-1844, courtesy Wellcome Collection, public domain)
化石一号:人类世,未来的“人类化石”
人类世将人类框定为一种地质力量,为人类赋予了一种在地质尺度上的集体身体性。这是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所称的“人类密集构造板块”(the dense tectonic plates of humanity),具备改变行星地质过程的能力。人类世化石是人类作为未来化石的幽灵,是一种统一的地层,并命名了一种以其痕迹或终结为特征的地质纪元。这种框架对主体性生产有双重效应:一是将人类命名为一个以人口或地层为单位的集体存在;二是将人类置于地质时间之中。作为一个地质集体,他们的影响被简化为同质的单一力量——一种地貌生成机制——将环境变迁框定为“人口问题”。在这种统一的地质框架下,地质人文的政治身体看似超越了国界与差异,却同时在性别、种族与地域分歧中固化“人口问题”这一认知(如全球南方女性的身体)。显然,我们在理解行星变化时,关于如何定位人类的叙事是绝非中立的。
早在“人类”成为气候科学显性议题之前,“人类维度”研究已通过特定因果逻辑框定人类:他们既是气候变化的承受者,又是其成因;既困囿于集体人口与个体化的两极,又受制于与地球系统建模相同的量化机制。这些主题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和人文学科)被纳入气候变化科学政策的时间较晚,因此人类被简化为地球物理地理组织模式的产物,而这种模式明确要求统一性的人类(与地球)。无论人类世是否被正式认定为一个地质纪元,它的重要性可能更多体现在它所释放的地理想象力上,而不仅仅是其科学主张。在以二氧化碳作为人类世物质痕迹的运用中,隐含着一种19世纪以来碳资本主义事件(the event of carbon capitalism)构建的政治地层学(politicised stratigraphy)。这一地层痕迹无意间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地球灭绝性地层的终结可能。由此窥见,人类世预设的真正灭绝并非总体生命,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体。这提示我们有必要思考社会地理学,既要通过地质力量与流动的差异化,也要通过社会条件的差异化来进行思考。
作为一种时间装置,人类世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将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嵌入到多个历史气候变化的“地基”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将人类定位为新的地质基础的特殊创造者。换言之,人类世通过将人类命名为地质力量,既将“我们的”气候变化重新自然化为地球与古人类历史中诸多气候变迁的一环,又突显了人类在行星尺度上前所未有的能动性。斯泽尔辛斯基(Bronislaw Szerszynski)对此双重困境评论道:“人类世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犹疑:这到底是人类作为自然主宰和终点的顶峰时代,还是人类被抹除的时代?”人类世在动员并自然化一个普遍主体——即人文主义奠基性主体的“人”时,同时也否定了因化石燃料消费不均所导致的(本体论的、政治的、性别的和生物学的)差异。或许,这一问题可如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所主张的那样,被更有建设性地重新表述为地质本体论(geontology)的问题?即地质生命的不同形式,通过这些历史性的地质本体配置(geontological configurations)来描述主体性并产生辖域效应(territorial effects)。
这种对单一本体论起源(即“人”)及“人的终结”的诉求,遮蔽了责任归属与地质生命形态(从高强度化石燃料消费到生物燃料消费)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动员了塔里克·扎基尔(Tariq Jazeel)所称的“一连串单调乏味的‘前批判地理既定’(pre-critical geographic givens),它们将普遍性正常化,使其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延伸”。扎基尔最终指出:“这个星球是统合人类的地基,是所有人的地质公地(geo common),但它只能在人类主动超越这一地基的瞬间才得以一瞥。”关键在于,地质既成为特定主体性建构的合作者,同时,它又是一个良性实体(benign entity),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中立之地。
人类世所涉及的主体性地质形塑,本质上是化石燃料资本化的产物。尽管人类世看似是一种记录地貌力量的中立提议,但这种地质生命的想象却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感官,并营造出一种特定的政治图景:它将化石燃料消费的遗产与责任普遍化,同时掩盖了地质生命构成中差异化的物质与时间地质本体论安排。然而,人类世通过叙事建构了一种物质主义,将智人与化石燃料耦合为属级别的地质力量轨迹,暗示了一种单一古人类的个体发生学(ontogeny of a singular hominin),并延伸到地理学与历史学。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地质主体,以19世纪使用化石燃料特征,其强化阶段被称为“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若要将人类世视为一种事件,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化石,将自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遗存的物质耗费(material expenditure),将化石遗迹视为地球与社会历史的地质见证与拟态记忆装置,将晚期资本主义的地质主体自然化为地层记录。然而,真正促使我们向地貌变迁力量过渡的,是另一个灭绝事件的物质复活(material reanimation);是一个灭绝事件以另一灭绝事件为燃料的发展轨迹。
死物质(dead matter)——如石油的有机体、天然气的生物与热成有机质、煤炭的石炭纪植物物质——在人类世的引擎中激活生命。这些支撑晚期资本主义的燃料,不仅提供能源与转化的热量,也驱动了石炭纪的强制性物质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主体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化石化的物质性并不外在于主体性,而是活跃于其再生产、创造性、技术可能性及终结;它是一种地质内在性(geologic immanence)。正如斯泽尔辛斯基评论:“如果我们的碳代谢正在破坏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的稳定气候,那么处于这一代谢机制核心的人类特定符号装置或许也会面临风险”。建立在石炭纪死物质之上的人类,不仅受制于这种物质主义,更是其表现形态之一;其后果是,人类在地球上进行地理扩张(即一种行星殖民),并侵入大气与地层。化石燃料是当代地缘政治生命的实体状态(material condition)。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丧失,最直白地表现为对地理空间的争夺,这些斗争确保了当代地质形式下生命再生产的实体状态。焦油砂、水力压裂、深海钻探等非常规矿产开采所涉及的物质交换形式令人日益绝望,这也印证了这种新政治地质学的广泛生物性妥协:在挖掘一层化石地层的同时,我们又创造了另一层镌刻着人类之名的当代化石地层。
人类嵌入地质时间,不仅表明了人类起源的再矿化(remineralisation),也标志着人类时间尺度从生物生命历程转向纪元和物种生命历程。这一点在“未来世代与灭绝”的气候变化话语中最为明显。对气候长时段的思考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并非是人类专属事件,它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着明显的祖先痕迹(尽管这种人—地协作是当代地质生命的特定实现)。存留于现代人类构成中的祖先痕迹表明,“我们”不仅追随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气候事件制约并激发了人类的进化);而且还追随化石燃料,因为化石燃料为地质力量(及地缘政治的可能性)提供了潜力和动力。
若将我们自身视为嵌入地质时间的存在,而非仅仅是地质力量的“创造者”,则有可能突破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狭隘的叙事路径,迈向非人的起点,并超越生物唯物主义,进而更好地思考不同的地质唯物主义。这意味着“我们”的地质力量从来不是专属的,它必须借力于对其他地质物质的动员——尤其是化石燃料。因此,如果仅聚焦于“人”在“人类世”中的位置,我们就有可能忽视那些地质力量成为可能的物质开端,并最终将地质拟人化(anthropomorphising the geological),而非将人类地质化(geologising the anthropos)。同时,也无法对此类场景的时间与物质逻辑给予充分重视。如果在意义生成与物质效应中,把我们优先视为一个物种,并弱化化石燃料组织生命形式的力量,就有可能忽视化石在这一等式中的积极力量。这种疏忽会影响我们从主体化、未来导向的实践,以及非人力量角度来思考与化石燃料的关系。
化石二号:人类起源理论(HOT)
从化石碎片中书写地质,被视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一次新发现的化石出土,都可能使已有的叙述被修正。然而,直至2010年,关于智人(Homo sapiens)起源的核心论点仍基本保持不变。正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述:“经过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只有一个类人种存留至今:智人。我们遍布各大洲,适应了多种多样的环境——在此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几千年间逐渐产生了微小的差异……但人类DNA研究表明,所有人类在遗传上惊人地相似,我们的基因有99.9%是相同的。”史密森学会也指出:“当今数十亿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智人。”
然而,随着年代测定与线粒体DNA测序技术的革新,近年来发现的史前古人类(或称祖先化石)极大地颠覆了人类历史和人类起源理论(HOT)中的既有叙事。这一科学冲击恰逢人类世概念被具体化的历史节点,使得“一个物种,一个世界”的自信宣言——即所有人类共享物种生命与地质共性——遭遇挑战。从“出非洲说”(out of Africa)的单一地理起源与单一遗传物种(智人)的范式出发,人类属(Homo)的表述正迅速被重构为多地域分布与遗传差异化。这些新化石使“人类故事”的谱系叙事趋于复杂化,推动学界关注辖域化进程与物种存在(species-being)中的地理与生物差异。
这种关注少数派生存(minoritarian survival)的古人类化石基因组学方法,或许可被视为一种底层流动(subaltern move),它生成的新谱系叙述表明,我们所成为的人类在属层面上或在种族、性别、地理身份等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我们”。正如遗传学家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所言:“我们需要修正人类起源的标准模型”。同样,提出“出非洲说”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在其2012年出版的《孤独的幸存者》(Lone Survivors)一书中承认,基层混合确实发生,并转向“主要出非洲说”(mostly out of Africa)的立场。我之所以强调人类起源理论(HOT)领域的这一根本性转变,并非意图以某一新的起源故事替代原有叙事,也并非认为基因组方法本身毫无问题;相反,我想指出的是:人类属的身份认知正在发生转变与重构,这种转变正在以新的方式动摇人类(anthropos)这一集体概念的固有预设。
直到2010年,智人通常被视为“最后的人类”,是在另外二十二种已灭绝的古人类之后延续下来的唯一人种。这一关于进化的线性进步叙事,在与气候背景结合的重述中,因遗传学研究揭示的“拉撒路效应”而变得复杂:非洲以外的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基因组存在基因贡献。事实证明,“其他二十二种”古人类并未完全灭绝,而我们也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纯粹。所谓“我们”是唯一幸存者、其他古人类均失败的叙事,以及这种叙事对“人类例外主义英雄故事”的刻意塑造,实则暴露了我们未能认识到那些在我们之前或之内的“他者”,也未能看到起源故事中“非我”的部分。
2010年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也许就是尼安德特人DNA的成功测序,以及对长久以来人类与尼安德特人是否存在基因混合这一问题的解答。古生物学家克莱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精妙地指出:“综合现有证据表明,人类形成了一个由不同群体构成的交织网络,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基因流动。一些人群的外貌差异可能源于对局部环境的适应与遗传漂变,但这些差异似乎尚不足以阻碍基因交流。”随着尼安德特人基因(在现代欧亚人基因组中占比高达4%)被纳入“我们”的遗传史,连同人属(Homo)之间在地理与基因组差异的交织网络,彻底重构了关于人类起源、性与地理交流的叙事,并揭示了具有不同时间尺度的生存与灭绝模式。
在大众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叙事中,智人常被定义为尼安德特人的对立面,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智人的幸存被视为通过文化与生物能力克服困境的证明。相较之下,尼安德特人则被塑造成“未能进入未来”的非幸存者,尽管他们曾在气候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生存了20万年。作为“我们”生成过程中的贬抑性对照,尼安德特人的原始史前形象为智人的动员提供了对立的依据。这种叙事与历史上诸多种族理论(与人类进化论同期发展)如出一辙:通过贬低差异来建构优越性。尼安德特人曾被描绘为史前时代的粗鄙之徒,而智人则逐渐被重构为气候时代自我形塑的主体,其适应性与创新能力(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神经结构层面)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科普作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的表述颇具代表性:“克罗马农人(Cro-Magnon)展现出变幻莫测的适应性,正是这种能力让人类成为无与伦比的成功物种。”然而,当“我们”被发现携带尼安德特人基因、以及其他可能的幸存形态逐渐显现时,这种智人与尼安德特人对立的叙事框架便随之瓦解。
2010年的第二项重大化石发现是X-woman。据报道,她可能是一个新的人类物种。《自然》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宣称:
“冰河时期的世界开始显得国际化。当尼安德特人主宰欧洲、现代人类开始向全球扩张时,另一支古老亲属——通过西伯利亚南部洞穴中一块指骨提取的基因组测序确认其身份——生活在亚洲。通过与现代人类基因组的对比分析表明,这一鲜为人知的古人类谱系的痕迹至今仍在,但仅存于部分巴布亚人和太平洋岛民的基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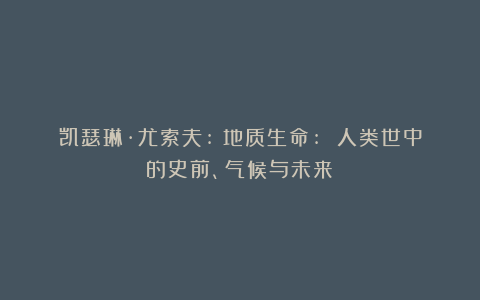
尽管1.7万年前的佛罗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俗称“霍比特人”)的发现已打破了“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存在其他共存物种”的固有认知,许多考古学家仍将佛罗勒斯人视为一个特例。而X-woman及其丹尼索瓦亲属(据称丹尼索瓦人在现代美拉尼西亚人群中约贡献了4%至6%的基因)则进一步表明,多物种共存与多态性可能比单一类人属的命名所暗示的更为普遍。
近年来的这些“发现”将人类重新概念化为一种跨物种存在,将古人类进化重构为在迁徙与辖域化形式上具有时间、性与地理差异的过程。尽管这些新发现的古人类联合体尚未形成定论,亦存在争议,但它们确实动摇了人类生命的生物学统一性,质疑了人类作为单一力量向未来自我再生产的假设。这里的目的并非要以某种起源叙事替代另一种,而是指出人类世中岌岌可危的创世形式。对起源与身份的固有认知的质询,以及对解读人类确定模式的扰动,足以撼动“人类”这一概念本身,而无需重新诉诸遗传学的推演能力或人类本质主义。这种衍射(diffraction)打破了单一人类概念的统一性,粉碎了生命构成的起源条件的平面——无论在地理、基因组,还是地质层面的。这些在灭绝事件中的幸存表述或许也提醒我们,如果将注意力过于集中于“人的终结”,可能会遮蔽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即谁,或什么,将可能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主体化过程中得以幸存。
Walter van der Velden 和 Aart Kuipers 为荷兰拉肯哈尔博物馆展览制作的“未来化石”
第二部分:化石理论
人类化石作为一种物质遗存,不仅揭示了沉积过程如何围绕“人类”概念不断累积并被历史化,也提醒着我们地质生命的长时段与非人的矿物起源(亦或未来)。上述两种化石既作为人类在物质与时间维度上的叙述装置,也作为人类时间起源与终结的地质证据,参与了人类世语境中对人类概念的建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生命形式(主体性的普遍或复线模式;“人”(man)作为人类的主导能指;地质生命的差异化模态);(2)责任与继承形式(人类概念的谱系及其向未来的传播);(3)地球的辖域化与地貌变迁形式。化石不仅诉说人类的谱系、继承与存续方式的问题,也召唤我们沿着地质实体的时间边缘展开思考,跨越“活”物质与“死”物质。它们展示并历史化人类的地质境况,还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构成既源于原初的矿化过程,亦归于化石化的终结。正如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所言:
“例如,在有机世界中,直到5亿年前,软组织(胶体、气溶胶、肌肉和神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那时,构成生命的某些物质—能量聚集体(the conglomerations of fleshy matter–energy)突然发生了矿化,一种新的构建生命体的物质出现了:骨骼。这仿佛暗示着,作为生物诞生的基底,矿物世界正重新确立自身地位,印证了地质远非地球进化中原始阶段的遗存,而是与柔软、胶质的新来者(newcomers)始终共存……然而,尽管骨骼使我们作为脊椎动物的动物门类得以复杂化,但它从未遗忘自身的矿物起源:它是最容易石化的生命物质,最容易越过界限,重归岩石的世界。”(DeLanda, 1997)
这种物质/矿物起源的进化谱系叙事深植于人类身体之中,却在以“生命体”或“社会身体”为核心的研究中鲜少被承认(即,那些将生命被视为物质的驱动者和变革者的研究)。相较于关于生命主义(vitalism)与生物政治的大量研究,地质维度往往是我们生成过程中被遗忘的地层。作为生物生命出现与分化的底层基质,地质的时间性与矿物从属关系尚未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被充分概念化。
从活骨到矿物的化石化临界转变,标识了地球与身体作为共同地质辖域的相互铭记过程(尽管这是完全不对称的)。通常的假设是,某种矿物成分传递到其他生命体,但这种跨越是单向的,直到死亡将生命体化石化,最终回归矿物。因此,死亡成为阈限及其实现的能动者(the agent of the threshold and its actualisation)。但若这种关系并非仅限于死亡所介导的路径呢?若地质不仅仅在制造化石时与身体交织,而且在动员地质生命的特定模态时,也通过物质—能量的力量引导身体的生成?如果这仍显得抽象,我们只需思考化石燃料资源丰富与匮乏地区间的预期寿命差异,就能理解:身体成为其本质的潜能,受限于其所能整合的化石燃料。但我们又该如何描述这种身体的地质运作(geologic work)在某物(aliquid)与化石化形态中的显现?
化石骨骼只是更大矿化过程中的微小碎片,这一过程既体现了生命对矿物的利用,也回归了构成地球物质主体的地质尘埃。这同样也是一种撕裂时间的运动,它将一个原初的身体粉碎成碎片,使任何考古实践在从碎片“推演”至更宏大的谱系叙述时,始终带有推测性。化石始终是一种不对称的知识对象,它是一个更大的生命所留下的微小骨骼记录,而那个生命早已无迹可寻。然而,化石之所以具有某种力量,恰恰因其作为拟痕迹实体(trace-like entity)。它是一个能激发叙事集蔟(narrative constellations)的碎片,能够动摇(甚至“分裂”)事物的类分式秩序(classificatory order)。
为了应对化石的碎片化特性,考古学家们分化为“统合派”(lumpers)与“分裂派”(splitters)。前者依据既有的广义分类框架对化石进行归类;后者则相反,他们利用新的发现来生成新的分类。无论是扰乱还是重塑知识的认识论,那些被挖掘机、采矿活动或冰川从地层中翻出的化石,始终与当下环境格格不入:谁将拾起它们?它们又如何突破我们认知的表层,或是证实我们以为已知的,或是彻底颠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将人类想象为人类世地层中的未来化石,就是将自身交付于地球的时间尺度与混沌变动之中;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自身矿物性中那些更少生命性、却更为持久的形态。这一想象隐含了“将地球作为地层“的模型:垂直而非水平的疆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强化,层层叠压,限制着那些在时间与物质完整性中碎片化的形式可能性。因此,化石是一种被遗弃的存在,却在当下的某一刻突然重新配置了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可能性。它如同一道从史前世界或想象的未来抛出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为思想与生成提供了一个此前难以想象的方向——我们作为尼安德特人,而他们作为丹尼索瓦人、人类地层、地质主体、灭绝与幸存。这就是化石发声的时空场景。
但它们的言说本质是什么?如果它们能“说话”,它们会说些什么?说话!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幽灵?一个沉默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失语,使我们对生命这一地质维度的语言如此匮乏?问题或许不在于“化石如何说话”,而是这种化石化的遗产在为未来说些什么?在这些地理、时间和物质的言说中,能动性位于何处?为何人类世中隐含的这种地质存在,却在我们的讨论中如此沉默?
化石燃料的作用无处不在。但奇怪的是,它在身体中的能动性和历史性却鲜少被概念化;与此同时,政治地质学过分依赖于研究化石燃料对地球的影响。这种将化石燃料外在化为商品、地缘政治权力或政治经济结构的方式,忽略了地质谱系中的一种继承,从而遮蔽了人类世遗产中完整的有历史意义的物质性。通过将主体性的地质维度理解为人类内在但未被言说的存在,我们的关注焦点便不再停留于化石燃料“说了什么”,而是转向它们的能动性如何在当前对大规模行星变迁的叙述中被否认。若将化石燃料视为活跃于当代身体性中的存在,我们便能构想在“死亡”化石与“鲜活”身体之间,在人类世的地缘政治主体之间,一场流动的、被动员的物质性对话正在进行。
目前,关于化石燃料运作的叙述依然以人类主体及其实践为中心,而非发展一种地质哲学,以探究化石燃料所允许的可能性及其对非人力量作用的言说。真正难以理论化的是,化石燃料如何在地球和身体性中看似“沉默”的同时,却差异化了生命形体。正如奈杰尔·克拉克(Nigel Clark)指出:“对非生命物质的明确探讨仍然罕见……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与元素物质的相遇中,人们反而强调了无机物的‘活性’,却牺牲了那些构成已知宇宙主体的矿物或化学结构的更特定属性”。如果物质在生命作用于它之前是沉默的——生命割裂物质(或者说物质的力量只有在生命中才得以实现)——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我们与化石燃料的差异化生成方式。这种方式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由这些引人注目的匿名物质的地质力量所驱动。
化石燃料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休眠期”(约3.6亿至2.86亿年前),在此期间,化石逐渐积累了作为燃料的高能量物质特性。然而,从理论角度看,它们在这一阶段始终保持沉默,只有当它们在社会世界中开始发挥生产性作用时才变得重要。德兰达评论道,过度推崇生命生物政治实则是一种“有机沙文主义”(organic chauvinism),“这种倾向使我们低估了现实世界其他领域自组织过程的活力。它也让我们忘记,尽管有诸多差异,生物体与其无机对应物在本质上都依赖于高强度的能量与物质流动”。通过将“力量的运作”作为分析单元,我们可以理解力量如何引导、创造并为生命形态提供可能性。正如格罗兹所言:“必须从超人(superhuman)与次人(subhuman)的共振中理解力量——这种非人属性既使人成为可能,又将人置于力量的作用场域:在人类之外、环绕人类、甚至内在于人类的力之网络中”。
化石燃料之所以是引人注目的主体/客体/力量,正因其跨越身体与状态:它既是化石又是燃料,既是物质又是能量,既属于深层时间又蕴含变革潜能。化石解开了生—死、时间—非时间、身体—非身体的方程,提示我们需要一种地质理论,并正视沉寂物质在鲜活身体中的力量:一种由非人力量驱动的身体性。化石燃料是“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回返,它以新的生命形态重现,并塑造新的地缘政治主体性。虽然自19世纪以来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开采催生了人口激增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步增长,但这些地质生命的独特性却在人类世的普遍化逻辑中逐渐湮没。
究竟需要何种物质理论框架,才能赋予化石燃料在其分化与持续分化的地质谱系中应有的能动性?或许答案在于:一种不低估地质关联性、身体性,以及化石燃料作为生命内部活性要素(而非外部附加物)所蕴含的潜能与承继性的阐释路径。化石燃料为理解非生命物质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另一条进路,即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所称的“被动生命主义”(passive vitalism)。具体而言,化石燃料与身体之间存在某种契合或耐性,使当代生命与石炭纪生命得以在生物和社会层面扩展,吸收并转化物质,同时也被物质所转化。这种承继关系或许不如基因组学意义上的遗传那样显著,但它却深刻地塑造了身体所能成为的各种可能性。思考这些地质生命形式(化石与燃料)如何彼此触碰(并通过触碰相互感知),正是我们开始理解矿感(minerality)之间相互穿越的一个重要起点。格罗兹建议我们思考:“物质与生命如何生成与消解。它们转化并被转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新物质主义,不如说是对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物质与非物质力量的新理解”。将地质力量理解为主体所共享的一种存在形式,要求我们重新建构人类世的地缘政治形态——一种承认化石力量及其在地缘政治生命中的身体位置的形态。这种地缘政治必须将其思考根植于地球之中,视其为世界—物质与亲密身体性的复合体。
这种地质协作可能呈现何种形态?火焰史学家斯蒂芬·派恩(Stephen Pyne)曾提出,我们对火的感知(pyric sensibility)已经深植于人类进化的过程之中;他认为我们因火而生,而非相反。尽管人工用火拓展了人类适应的气候范围,但化石燃料驱动的高强度能量流将这种拓展提升至行星尺度。理解如何与火共处——不是控制它,而是引导它进入不同的存在形式——在原住民文化中意味着学习火的意志、倾向与能量,这即是派恩所称的“火耕”(fire farming)。若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化石燃料,我们是否也应思考:它们的需求与倾向是什么?我们骨骼中回响的矿化之灵又在低语着什么?这种化石生物质(fossil biomass)为何如此执着与诱人?想象一种负责任的“化石燃料耕作”(fossil fuel farming)可能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留在地下的和被开采的资源。可行的路径之一是考察化石燃料实践(如同许多能源与可持续性研究所做的那样),但倘若依然假定人类主体控制着这些实践——作为“生产者”而非实践中的“协作者”——那么化石燃料所特有的物质—能动性强度就被抹除了,化石燃料的动员力量也被剥夺。通过比较依赖“活的生物质”与“化石生物质”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就足以揭示这种强度所表征的地缘政治形态所蕴含的极端地质权力。同样,在可持续性文献中,研究重点往往是对资源极限的认定与行为模式的规范,而非去探讨这种地质动员在生命力及其再生产(作为身体以及身体所依附的情感)方面所开启的可能性。那些试图在物质经济中平抑能动性(flatten agency)的研究进路,或许能更好地揭示化石燃料的活性特性,但它们很难触及代际之间所积累、被资本化的地质继承与地质力量——这一切皆是通过人类进化史与深时历史的偶然性而沉积下来的。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化石燃料留在地下,而不是实现其能量物质性,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化石燃料对地质权力形式的开端,而不仅仅是在地缘政治和民主安排的层面,还包括由这种强化所驱动的地质身体性,作为一种特定的主体化模式。延续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思路,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化石燃料去介入集体主体性的构成,从而实现跨领域嫁接(transversal grafts),切开通向地质生命的开口,进而生成新的主体性地质形态。唯有在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才可能做出一个反直觉的转向:拒绝化石燃料的“馈赠”,也拒绝作为其继承者的人类(即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缘政治主体),转而探索其他能量关系,以同样可感的方式重新引导、重新想象乃至美学化地质权力的力量。
如果在主导性的灭绝形式中,摆脱化石燃料的生活之术是一种生存方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发展出某种非参与(nonparticipation)的伦理形式,主动阻断那些即便诱人却必须拒绝的化石燃料协作关系。这一切都依赖于我们对地质之能的理解与实验——既作为承继,也作为未来力量。拒绝这一承继的再生产需要一种牺牲性的责任(sacrificial responsibility),这种责任在“馈赠”与“牺牲”的张力中得以展开: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去解除对既有地质身体性的认知与依赖,同时培育出新的地质主体性形式。
女性主义身体研究为如何解释标记和差异化身体的继承关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路径,这些研究极大地复杂化了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并指出了生命构成中潜在的协作形式。这也呼应了瓜塔里提出的“精神生活中主体性的集体生产”概念,即不存在自给自足的主体,只有由不同的共生与禁制形式所主导的主体性生命可能性。在这些研究中,关注点在于责任的集体可能性及其分布式理解,而非新自由主义主体的孤立逻辑——后者认为个体完全“自由”地独立于社会与集体继承,自行决策并承担全部责任。强调义务与责难的主体性观念,将某些此前被视为“良好生活”(good life)一部分的行为病理化,使个体独自承担责任的重担,而忽视政府在建立有效制度、以减缓化石燃料在集体身体与社会身体中积累方面的失职。
在可持续性文献中,“行为”被奇怪地从主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可供操作、优化与训练的对象,却很少承认人类生命在何种程度上是与化石燃料共同构成的(仿佛这一传承无关紧要或没有引导生命与身体的生成)。也就是说,仅仅从文化或社会学角度解释化石燃料消费,不足以说明化石燃料作为生命构成物质在生物与社会层面的交织依赖。
因此,追随化石燃料不仅需要将其视为社会实践中的卑贱之物,或建构一种限制性的话语,更需要一种宽容的视角,承认化石燃料在社会实践和生命形式中开启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能量作为一种同时具有身体性和行星性的承继所给予的馈赠。如果否认化石燃料的这种给予性(givenness),对“使用”的理解将永远停留在身体性、欲望、生命形式的再生产、以及生成过程之外。这种对地质性继承的有意识拒绝,将以阻断我们理解未来所承载之物为代价。如果地质性是地质生命形态的责任主体与物质指引,那么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我们尚未发展出一套充分成熟的“地质哲学”,或一种真正将“地”(geo)与“政治”并置并重的地缘政治学。
在本文中,我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存在(being)在概念、本体论与物质层面始终与地质性紧密交织。当代人类世主体性,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命形式,都与化石燃料密不可分。因此,若要设想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以及人类世的潜在终结,需要解构与化石燃料共同建构的生成形式,同时重构可替代的能量物质性。这要求我们建立新的集体主体性与物质性生活形式,以审视并超越人类世的地缘政治遗产。
本文所讨论的“物质”——即化石燃料——并非外在于生命,而是具有能动性,能够导引、塑造并差异化人类世中的地质主体。我们无法对抗地球与气候,人类只能顺应能量流动,并与地质演变及非人力量协同。就化石燃料而言,人类只能选择是增强其流动、释放其能量,还是让其沉寂不动。问题不在于“我们”对地球的责任,而在于我们对地质生命内部协作形式的担当。这既关乎接受新的主体性形态与地球本体论,也涉及创造新型能源形式。
本文所探讨的化石,本质上构成了一种祖先性陈述(ancestral statement)。它们不仅是骨骼长链中的一环,更承载着符号与想象功能,它们被卷入起源故事与终局叙事之中,既编织着历史图景,又勾勒未来想象与身份认同。本文主张,人类起源的语境性关联对于理解人类世现象的人类主体性至关重要:这种主体性既体现于地质时间秩序、科技与社会实践,也显影于排斥机制与过剩生产的运作模式。尽管起源可能被遗忘,人类的终结看似遥远,但进化模型和作为特定形式的人类想象通过气候科学中的人类框架(人类因素、适应实践与政策、可想象或可实现的未来构想),以及作为未来地貌能动者(人类被“锁定”于化石燃料消费和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定模式),持续浸染当下现实。
“新人类”化石的幸存,进一步促成了他者在“智人之我们”中的内在化,从而扰乱了一个将当代智人“奠基”(grounds)于地球谱系中的史前原史时期(protohistory),这一过程将人类自然化地铺展于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这种奠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将起源深埋于现代人类的史前史,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预设(即“人类之我们”);另一方面将晚期资本主义塑造的人类主体性(作为地球表面全域支配权的宣称者)自然化为地球固有产物。讽刺的是,当前所提出的“人类问题”恰恰源于这种根基性预设的动摇——地球不再是被预设为宽容的地球。这使得“人”与“地球”的未来关系成为一个受动态地球过程影响且作为其能动者的不稳定概念。因此,这两种古人类化石共同昭示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类作为地球辖域化力量在史前、当代与未来取向中的统一性。
如果“人”(man)作为人类世的统一而等级化的能指开始瓦解,成为一个因其起源的“污染”而丧失不稳定的概念和身份,那么,人类世未来的可能性是否也会随之改变?直到最近,史前史一直维持着一种共同地理和基因进化的叙事,使人类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共享“出非洲说”遗产的集体。但若起源不再被视作一种集体性继承,人类的名称便反转自身,通过反对自身的名称,来命名即将到来的人类(超越该名称界限,且不源于此名词的存在)。新发现的祖先化石释放出新生的主体性模式:部分幸存和差异化的历史地理,其中“地质”不再被预设为共同基础。
在“人类”(anthropos)这一符号下,“我们”都对世界负有同等责任,但并非所有人都被这一符号充分代表。人类、地球和时间性的概念如何以看似协作的方式共同发展,同时又掩盖了这些概念形成的谱系与叙事结,这在人类世语境中仍是一个有待提出的问题。在迈向普遍地质生命的进程中,也抹除了作为集体走向行星地缘政治(planetary geopolitics)所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种地缘政治不应建立在暴力排斥、等级结构的形式之上,也不应忽视不同的地质资本化或地球的地质本体论形态。
动员人类起源的叙事,就是在追问:什么事物将被带入未来?在“人类”(human)概念下继承什么?哪些形态又因为过剩或排除而得以幸存?谁又能预见我们对化石燃料的集体实验将引发何种后果?这类动员将催生哪些新型地质生命形态?然而,在我们思考人类世中人类的“位置”之前,我们更需思考这个问题本身所调动的思想、框架、继承和再生产世界中所动员的内容,尤其是地球在身体性和本体论上的辖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