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790名订阅者负责,期盼切近人生的好稿,期待作者关注,期待读者回应
记体小说《童年》连载(九):17-18章
文/董质良
十七、鱼和猫
1962年的秋天,大地早早呈现出了一派丰收的景象。河垻里的水稻籽粒饱满,一片金黄,一阵微风掠过,稻田里就滚动着层层波浪。坡地上的花生一片翠绿,芝麻密密匝匝的挤满了茎杆,硕大的包谷蹲在高处向人们轻摇着它们骄傲的胡须。社员们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比集体大
田里更胜一筹,南瓜有筛子大,红苕把大地都涨得裂开了条条缝隙。人们已彻底摆脱了三年饥荒的阴影,自信的笑容堆上了人们的脸庞。自从麦收开始,我们家就摆脱了饥馑的魔影,几个月下来,已忘记了饿肚子的滋味。自古道: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逸。这几天下起了绵绵秋雨,我在家百无聊赖的看着糊墙的几张旧报纸,这时,隔壁二莽子跑来约我去钓鱼。我砰然心动,可是用什么钓啊?我一无钓杆,二无钩线,二莽子提示我:你用你妈做衣服的针在火上烤红了一折就是一个钩,线就用做衣服的白线,杆子好解决,晾衣服的竹杆都可以,挖几条蛐蟮作钓饵,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我听了好生兴奋,即刻依计而行,花了半天功夫才把装备做好,自己看着那根笨拙的钓杆,在心里嘀咕着,这能钓到鱼吗?吃过中饭,二莽子来约我了,我扛上竹杆(实在不好意思称之为钓杆),跟他来到赵家湾刘义伯门前的一口堰塘边,我忐忑的问道:“这是人家私人的堰塘,准许钓鱼吗”?二莽子不以为意的说:“不要紧,刘义伯是我姑爹,他不会说我的”,于是,我就放心的同他约起魚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钓鱼, 刚把钩丢下水,就涌上来一群鱼儿抢食鱼饵,我马上提起鱼钩,一条银光闪闪的鲫鱼活蹦乱跳着被我抓住丢入脸盆。我惊呼,这里鱼儿
这么多呀!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钓到了二十多条鱼,不过鱼儿都不大,总共也就一斤多。看着盆里游动的鱼儿,我还是很担心堰塘主人会来干涉,便催二莽子回去,他说我们每人再钓一条了就走。于是我耐下心来陪他再钓一会,谁知我竟交上了好运,只见我的用芭芒梗做的浮子突然一下沉入水底,我料知这是一条大鱼,双手抓起竹杆一举,我的天呐,这哪里是鱼,这是一条二尺长的蛇,我吓的心口乱跳,尖叫一声:“蛇,我钓了一条蛇”。二莽子闻听叫声,瞄了一眼,对我喊道:“你个暴暴,(宜昌方言傻瓜之意)这不是蛇,是黄鳝”。他丟下钓杆,跑过来帮我把黄鳝逮住,这条黄鳝好大,足有八、九两重。
我满载而归,母亲收拾鱼儿,当晚做了一炖钵香喷喷的烧鱼,饭还没熟,我就先把墩钵放在灶旁的木炭火上温着,心里好高兴,今晚要吃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免有些得
意洋洋。谁知乐极生悲,大哥突然从灶旁经过,裤腿把炖钵擦了一下,炖钵滚翻地上,眨眼间一大钵珍馐美馔就泼翻在地,付之东流了。我心疼的连忙去抢,复钵之下,岂有完卵?最后也只将未曾煮烂的鱼块捡起一碗,在清水中淘洗了几遍已滋味全无,意兴阑然,唉,我也不敢埋怨大哥,一顿美味就这样化为了乌有。
有了第一次钓鱼的成就和感受,我自然是爱上了钓鱼,以后又同二莽子去钓了几次,巧的是每次都没撞见过堰塘的主人,这样,我就以为鱼是可以随便钓的,别人都会不以为然的。谁知有一次二莽子不在家,我独自一人扛上竹杆跑去钓鱼时,刚钓了一会儿,就见从赵家跑出一个人来,恶狠恨的高声叫唤着:“你好大的胆子,谁叫你来钓的?难道没有个你的我的了”!我一看此人正是赵家的男主人刘义伯(入赘赵家的女婿),他凶神恶刹般跑到我身边,一把抓住我的钓鱼杆,往膝盖上一磕,我的可怜的钓鱼杆就变为了两截破竹杆,他又抓起我的脸盆把里面的几条鱼儿倒入堰塘中,口中恶毒的咒骂道:“还不快滚,再敢来偷鱼,我打断你的狗腿”!我狼狈地逃了回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钓过鱼。
初冬时节,我跟大哥当帮手拉边绳到宜昌报社用粪车拉粪,因为一天要拉两趟,所以起的很早,走到东湖(现
在葛洲坝一公司位置),天才刚麻麻亮,我朝早已干涸的东湖瞄一眼,却发现在湖心稀泥里有一条银白色的鱼在翻腾。我立刻同大哥停下车脱掉破烂的鞋子,也不管湖面的稀泥已结上了一层簿冰,跳入稀泥向湖心那条鱼挪移而去。到跟前一看,哈,是一条重达两、三斤的胖头鱼,我上前抓住鱼,心扑通直跳,既高兴抓了一条大鱼又害怕被人发现,低下头大步返回岸上,腿上被坚利的冰块划出好多血口子却全然不知,我们把鱼放进车上的草包内,拉起粪车大步离开了是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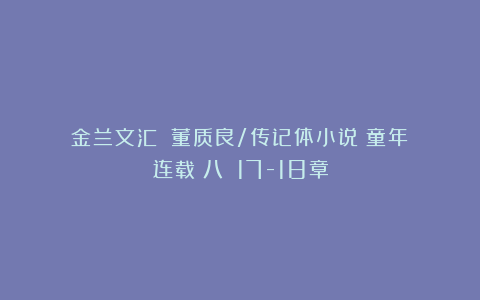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把那条鱼拾掇干净了放进碗柜里,准备第二天好好打个牙祭。谁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柜门大敞八开,地上有一条吃得只剩下一个鱼头的鱼骨架,我心疼不已地埋怨母亲没有关好碗柜门,更是把那偷吃的猫恨死了。我们最终没舍弃那个吃剩的胖头鱼的鱼头,晚上,将那个鱼头做了一大钵美味的鱼头汤,我们一家人围在用几块红砖围成的火笼边,就着那盆鱼头汤吃饭。这时,那只偷吃了鱼的大黄猫又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我们的屋子里,我用吃剩的鱼骨做诱饵,将那馋猫一步一步诱到身边来。
看看到了一手可及的地方时,我突然伸手一下把牠按在地上,那猫一愣,随即乱蹬乱弹,拼命挣扎,我顺手抄起一块火笼红砖,朝黄猫的脑袋狠命拍了一下,只听得咔的一声响,黄猫头骨破裂了,但牠却并未死去,还在挣扎,我一不做二不休,举起砖头一连拍了牠十几下,最后才没有动静了。我们当即将那猫剥皮开膛,好大一只猫,足有三、四斤肉,但是我们却都没有勇气吃牠的肉,只得弄点盐腌起来,冬天烤火时又把牠挂起来燻腊了。第二年春天我们家城里亲戚来做客时,我们谎称是兔子肉,拿出来招待客人,大家吃了赞不绝口,都夸好吃,我也尝了,确实好吃。不过我这一生也就吃了这唯一一次猫肉,要不是为了报那一条鱼的仇,我也不会干那缺德事,愿猫的灵魂饶恕我吧!
接近年关的时候,天更冷了,一阵朔风吹过,冻得人把头都缩到脖子里去。一天徬晚,我们从五队放工后回小峡家里去时,路过铁路边的一口长年不干的堰塘时,发现
浅浅的水面水草下面有什么东西一拱一拱地移动。对鱼儿情有独钟的我们立刻意识到那是鱼,而且还是比较大的鱼。我们几兄弟一商量,妈的,今晚干一票大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来个竭泽而鱼。等天一黑定,我们悄悄地潜来堰塘边,合力摇松了堰塘的底剅(水塘的泄水闸),然后回家去等待塘里的水泄光,因怕水响声太大被人发现,所以不敢把剅桩全部拔起,只是摇松了让水慢慢泄掉。这一夜我们夜不能寐,等一会又去看水还有多深,去了多次水尚太深无法下手,也就上床睡了一觉,到三、四点钟又醒了过来,外面寒星闪闪,遍地一层白霜,寒气逼人,实在舍不得热被窝,但是即使不能抓鱼也要去把剅桩按还原,否则天亮就会被七队的人发现而怀疑到我们头上。我们抖抖索索摸黑到堰塘边,放眼一望,我的天啦!只见塘里水
已放光,塘底淤泥面上一片白光在翻腾闪耀,那都是干了水的鱼呀。我们心里兴奋的朴通狂跳,也顾不得塘边浅水都已结冰,可能划伤腿脚的危险,争先恐后的跳下塘去,向在泥水中挣扎的鱼儿扑去。可是在抓到几条七、八两重的大鲫鱼后,才意识到没带东西来装鱼,我们派一人回家去拿水桶,其他人则继续抓鱼。我们在稀泥里挖了一些坑,把抓到的鱼儿暂时丢到坑里,一会功夫,我们就把塘里的鱼儿基本抓完了。这时水桶也拿来了,我们把坑里的鱼捡到水桶里,哇,装了干干的一桶鱼。我们速战速决,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迅速撤离现场,抬着丰硕的战离品,一骨遛的回到了家中。我们把一桶鱼藏于床底下,然后洗脚上床睡觉,可是心里太兴奋了,哪里睡得着?躺了一会,见天还没亮,于是又起身去塘边看看。这时天已蒙蒙亮了,我们清晰的发现,我们先前踩下的脚印里灌满了清水,每个脚印窝里都有一条黑色的鱼儿的脊背。我们喜不自禁的一手一条,一会又抓了一、二十条鲫鱼。这时天己亮开,实在不敢再逗留,便都匆忙跑回了家。果然如我们所料,天亮后,七队的人便发现了堰塘里的鱼儿都不翼而飞了,有人告诉了七队队长苏良新。苏队长便独自进行了破案侦察,我们家离事发地最近,必然是怀疑重点。上午十点钟,苏队长来到我们家,问我们:“你们早上去抓鱼了吗”?
母亲知道瞒不过去,而且天亮后我们几兄弟为了打掩护做样子,随大批人踊到塘里去抓过鱼,便回答:“是的,苏队长您请坐”,苏队长问:“那你们抓了多少鱼,能给我看看吗”?母亲一迭声地说:“抓了不少,有一大钵呢”,说着从碗柜里把早就准备好的一钵子小鱼端出来:“苏队长,这怕有两、三斤呢,我来生火,苏队长您坐一会,中午就在这吃鱼吧”。苏良新一时语塞,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他也没有证椐说我们偷了鱼,便讪讪地说:“算了算了,我还有事呢”,说完就匆匆离去了。我们呼出一口长气,终于可以安稳的享受我们的劳动果实了。
十八、居无定所
翻过年进入了1963年,这年的春天,我们家又陷入了缺粮的恶性循环,不过较之头一年已有一些减轻,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増长,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多一些了,工分粮就多少增加了一点,另外我们种的自留地也能收点瓜菜类的东西,多少帮衬了一下。但是这时,又一个巨大的困难降临到了我们家,二月间,房东赵XX对我们说:“你们要赶快找房子搬走,我要喂猪了,你们不能老占着我的猪栏屋”。其实房东早就想赶我们走,只是因为我们家是大队安排来住的,他自己是五类分子,不敢和大队对抗而勉强屈从。后来他知道了我们也是有政治污点被赶下乡的后,就再也不愿让我们安稳了,他老婆经常对我们恶语相加,直接赶我们滚开,先前我们还同他们对抗、吵架,好歹不理他们,同他们耍赖。后来他买回一头小猪,拴到我们门外喂养,晚上和下雨天就拴到我们房沿下,让猪拉屎拉尿、成天叫唤来恶心我们,谁知这一切我们都忍受下来。赵XX见这样还不行,便又生一计,他以我们屋上的瓦是他借别人的为由,趁有一天我们家无人时,突然上房把瓦片全揭走了。这一下我们傻眼了,但仍继续赖下去,事实上我们也无处可搬。怎么办?在满天星光的屋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五队有人为我们出主意,叫我兄弟们把稻草弄些去把房子盖上救个急。于是我们依计而行,几兄弟挑回几担稻草,借来一部长梯子,半天时间就把房顶盖上了。这样的乱稻草盖的房顶,白天挡挡太阳避避风,晚上遮遮露气是可以的,但一下雨就不行了。我们仅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就下起雨来,而且是连阴雨,这一下就让我们叫苦不迭了,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外面雨住了,屋里却淅淅沥沥的滴个不停,床上的被子、衣服及屋里的一切都泡在水里,无法做饭,无法睡觉,这回我们束手无策了。
世上还是有很多好心人,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五队副队长刘XX借给我们一间屋子暂时栖身,屋子太小,我们几兄弟又分别到其他几户好心人家去借宿,好歹暂时安顿下来。从这时候起,我们的内心就产生了三大愿望,愿望一:不缺粮食,吃饱肚子;愿望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住;愿望三:不受政治上的压迫和岐视。但是,这三个愿望我们竟等了十七、八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部实现。
我同二哥这对双胞胎弟兄借住的是店子上的钟家,这家的女主人陈妈是一个面慈心善的好人,且在当时的农村妇女中,她又是不多的识文断字、知多识广的人。一般四邻八户但凡大事小情,总是要来向她请教和求助,象什么娶亲及丧葬看日期呀,小孩取名和算生辰八字呀,总之乡下缺少文化和见识的人们都把她奉为先生一般。她也总是热心快肠的帮人化灾解难,尽力帮助,因此她在四邻乡里颇受尊崇而德高望重,我们弟兄尊称她为陈妈。
陈妈家并不宽敞,她家有老伴、儿子媳妇及两个孙子共六口人,却只有两间正房和一间偏屋。她家堂屋里放着他们俩老的两口没有油漆的寿木,我们在那上面放上一合铺板,小俩兄弟睡在上面感觉很是安逸。当然,有的人是很忌讳和害怕寿木这类东西的,但是,前面我讲过,我们既在小峡公墓锤炼过胆量,而又有在没有顶盖的屋子里淋雨受罪的痛苦经历,如今能在陈妈的呵护下住到干净明亮的房子里,睡在干燥温暖的床铺上,只有满足惬意的感觉,心中充盈着对陈妈一家人的感激之情。
在这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里,我们兄弟俩从市内表哥那里借回了一本《西游记》,以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开始艰难地阅读此书,大量生涩的繁体字和古词语,使我们读得十分艰难。但我们有十分顽强的求知欲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犟劲,每天坚持在工余时间里读一小段,有时也向母亲问询一些生辟字,渐渐地便能够进入书中丰富而精彩的故事情节了。当然,书中也有大量确为我们初小文化无法领悟的章节段落和生辟古字,我们就只好先简后繁,把不认识和看不懂的字、词拈到一边或跳过一段,不求甚解的往里硬钻,功夫不负苦心人,十天半月后,我们竟然在晚上乘凉时能够向隔壁三家的乡亲们兜售我们的西游大话了。当然,并不是天马行空的瞎说。我们有什么
特殊本领,能吸引乡亲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实在是六十年代的社会太落后,除每户有一个木头的有线广播喇叭外,再无任何资讯媒介,连官媒的《宜昌日报》也只有公社一级才有,当时的老百姓可用天聋地哑来形容毫不为过,故此,往往在晴热的晚上,我们的原始评书《西游记》故事能吸引来许多听众,我们粗浅地对这部神话巨著的故事情节的描述,常常让大家听得如痴如迷、情思神游。在阅读中学习,虽然有大量文字不认识,(当时我们还不会使用字典,况且也没有字典)靠了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还是逐渐阅读了大量可以弄到手的书籍。例如《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苦菜花》《晋阳秋》等一批革命斗争小说,故事性强,浅显易懂,生辟字不多,对于迅速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说到大量阅读书籍,其实也是很艰难的,首先是书籍的来源,除了在表兄处借些书外,我们也以交换的方式同本队如汪大和、杨培伦等人手中得到一些书籍,反正对书籍的渴求仅次于空气和粮食,往往为得到一本小说会用尽心思,既得之而后快。得到一本书后,总是挤出一切时间尽快读完,因为常常是限几天时间要归还别人的。白天在队里劳动,抽一早一晚或中午休息的一点时间突击外,实在来不及就夜晚通宵达旦的读。幼年时精力是旺盛的,但是物质条件太差,那时除了一床被子外便再无他物,也没有电,晚上照明是煤油灯。我俩寄宿在陈妈家,虽然主人很和善,但我们也有自知之明,不能用主人家的煤油灯熬夜长时间看书。于是,我们只能动脑筋自己想法解决照明的问题,我们用一个墨水瓶子安上一根布带作灯芯,在母亲住处弄来一点煤油,然后晚上便兄弟两人凑到被子的一头,通宵达旦的共读一本书,直到熬干了一墨水瓶煤油,才心犹不甘地睡觉。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知识,也逐渐提高了阅读能力,在随后的数年中,四大名著也都粗浅地浏览了一遍,打下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认识基础。尽管如此,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少年,对社会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例如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个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次,我俩在店子上丁宝臣家门口外墙上的墙报栏里,看到一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农业时事的文字。似懂非懂的浏览了一会,便拿起粉笔在下面空余的版面上写下了亩产万斤几个字。写这几个字其实就是一般的少年儿童得瑟出尖的做派,并无什么特定的思想意识支配,起源是前些时我们看过一些大跃进时期的旧报纸,上面赫然吹嘘的某某公社亩产若干万斤粮食的报导。谁知这一无意之举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也可说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无妄之灾。就在我们已经淡忘了黑板写字这点小事的时候,有一天,队长忽然叫我们两兄弟跟他到公社去一下,说是公社秘书黄文喜找我们有事。真是天方夜坛一样,我们十多岁的小孩只知道公社秘书是好大个官,小孩子与生俱来就怕警察和当官的,今天不知何事,突然传我们过堂,不由得油然而生一种惴惴不安和畏惧之感。怕归怕,还是不得不以沉重的步履跟着队长来到公社,队长把我们俩交给脸色阴沉的黄秘书后就走了。黄秘书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后就坐到他的办公桌后的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公文纸和一支自来水笔,一付审讯的架势更让我们茫然不知所以。然后他一本正经的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年龄,又阴沉的加一句:“什么成份”?这一问使我们顿时心如雷击,
我们的家庭早已被打入了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因为我父亲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但又都沾一点边儿。
这时二哥倔强的说:“我们是城市贫民”。黄文喜眉毛一竖,正准备发作,但他也弄不清我父亲的准确定性,便只好作罢。但他仍故作威严地问道:“铁路边上的反动口号是你们俩谁写的”?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事。我嗫嚅着承认是我写的,他拍着桌子狠恨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这是反动口号”!二哥强辩说:“怎么是反动口号?我们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的,难道《人民日报》会是反动的吗”?黄文喜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二哥竟敢顶撞他,他窘迫的咆哮道:“你们这就是反动行为,今天一定要写悔过书,不然我就要把这事记入你们的档案”。我一听档案二字,浑身一震,以为就是公安办案,二哥还是坚持说:“又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照《人民日报》写的还有错?就不写悔过书”!黄文喜看二哥如此强硬,气得吹胡子瞪眼,他本想小题大作地把我们弟兄弄来嚇唬一顿,给个下马威的,哪想碰上了二哥这颗硬钉子,倒把他自己搞了个不好下台。这时,我怕事情搞僵了,便说:“我们不知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我们承认错了,以后再不写了”。黄文喜见我服了软,赶忙借势下台:”“那你们既然认识到了错误,以后就要好好做人,不得再搞这样的反动事情”!说完便匆忙把我们打发走了。从此以后,此人便与我们结下了梁子,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老是在背后使用十分阴险的手段整治我们家,是我们十分仇恨和厌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