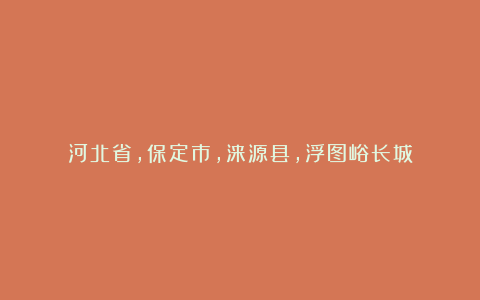|
第一次走张石高速感觉隧道多,尤其是以浮图峪命名的六个隧道,就好像走进了隧道的结界。
把车直接开到长城跟前,甚至那还有个小型停车场。停车场旁边有个冷的缩头缩手的大叔,很热情和我们打招呼,而且告知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四连珠的路段,还安慰说这边长城敌楼也很密集,而且就算到了那边,山顶大风也能吹走人。
就近登上了第一个已经半塌陷的敌楼,虽然是断壁残垣,依然气势不减,像个征战一生的暮年将军,不管岁月几何,我自气势磅礴。
沿着城墙登了两个敌楼后,第三段城墙地势险陡,就沿着长城下面的路走了一段,走在可以行车的现代路段,除了抬头看着蜿蜒的长城,还在琢磨目前的方位应该是长城以外,如果回到明朝是不是已经算出境了。
走过了险峻的路段重新登上城墙,凭高远眺,大山连绵,奔驰浩荡。东南望虽群山重重,亦有平原河流,西北望北长城盘垣,穷山巅之萦回,即冈峦之体势,远处亦有雪山晶莹。
敌楼内非常宽敞,正午的太阳透过窗户投影在地上,在这深冬虽不温暖却很明媚。当年,驻守在这的士兵们,沐浴着这样的阳光也会暗自思念故乡亲人,期盼日常安稳吧。
连绵叠嶂的群山,看不出疆域的划分,几百年的城墙,却标记着曾经的内外。 现在让更多人惊叹的应该不是这条长长的边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是它作为人类建筑奇迹的本身吧。
奇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付出和消耗,在机械和物质都相对匮乏的时候,普通人所承受的东西就更多。每一块长城砖的筑造,每一米长城上的巡视,都是千千万万无名的普通人,究其一生撑起来的伟大。
从北向敌楼出来时,正午的阳光将自己的影子投向深谷,有种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苍凉感。曾经这里的影子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标点,虽然每个瞬间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但对于个体来说这过程又何其短暂悲壮。
听一下塞北来风的呼啸,之前停车场那个大叔说的对,这风真的能把人刮走,而且是我这种能经受住8级风的体重标准。
巨石真的能挡住狂风,躲在石头后面,感受了一下造山运动的杰作。三块大石相搭,整体又独立,壁如斧削,坚毅不屈的屹立于长城旁默默相守,难怪有人把浮图峪称为巨石长城。
一块圆润平滑的石头,依稀绘有图案,其实只是大自然留下的符号。仿佛需要被破译的密码,也许根本不用破解,只是敬畏和尊重就够了。
返程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换个角度又间隔了距离,巨石温婉了很多。诗人诚不欺我,果然远近高低各不同。
风大、低温、但是石头缝里依然能长出树木,生命原本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遇强则强才是最初设置的生存密码吧。
大风吹洗过的天空碧蓝,一弯弦月悄然相伴,不由想起那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只是不知那彩云归处,是胜利凯旋,还是阵殁还乡。
其实长城从未真正阻挡过什么。胡骑照样南下,清兵依然入关。它不过是一条长长的墓碑,刻着”此地曾有人无数”。而明月冷眼旁观了这一切,既不阻拦,也不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