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陶器在生活中大量运用,当时各大诸侯国的主要城市都有陶铭出土。有资料表明,在陶器上用尖器刻划文字的时代大约在商代早期,要早于殷商甲骨文,字形也比甲骨文古朴。战国陶铭的特点在于其文字大多是用陶玺在陶坏上钤印而成,由于它的特殊表现手法,与古玺相比,更显得活跃而富有情趣。齐国故都临淄就是古陶铭出土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从字迹观察,齐国陶铭线条质朴凝重,起伏并不是很大,通过其圆转流畅的用刀,其笔势墨态得以再现。
“陈搏三立事岁右禀釜”(图47),既有刀锋的圆厚流转,又有泥质的憨态,整个印面线条润涩交错,或断或连,或虚或实,大片的残破因有一些“灰面”的协调显得并不突兀,整体和谐自然,为古陶铭经典之作。
“陈□立事岁安邑毫釜”(图48)可与齐系古玺相互印证,古陶铭的制作手笔比古玺更加大开大合,恣肆不拘。刀在陶上刻画的自由度比在铜质上更轻松,可发挥的想象余地更大。
“璋□□选信玺”(图49)风格很特殊。首先在章法上作横向两行排列,字与字之间左右相连,而上下之间拉开一些不规则的距离,看上去生动别致。虚实的变化除了靠字形侧倚之外,气脉的贯通全靠“留红”获得。线条呈锲刻状,局部有类似的单刀线条,犀利流转,外框的残破与文字漫滤相映成趣,使整方印看上去轻松活泼,在古巨玺中是很难得的。
“右选文口信玺”(图50)文字紧通边线,“印眼”是在中间的不可识的那个字,中间的圆圈笔画与上下各三条竖线,极具岩画的味道。上三条线向右倾,顺应了“文”字的走势,又与“右”字相揖应。下三条竖线与“玺”字的三竖构成两组块面,排叠的线条具有相对稳定感,与其他字合谐地构成动中寓静的印面。
“长金之玺”(图51)朱文是齐系古玺中的代表性作品,在有条不紊的环境中对线条加以梳理,四个字非常悠闲地摆放在并不规则的方框中,十几个大小不同的“点”运用得十分考究。点多易散,尤其在篆书中,“点”化为短线是方法之一。“点”如山水画中的皴法,纵有千种变化,也离不开线形的控制。所以几处微微向右上抬起的横画显得很重要,尤其不能缺少的是“长”字下面的那一笔,飘逸灵动,少了它章法将溃不成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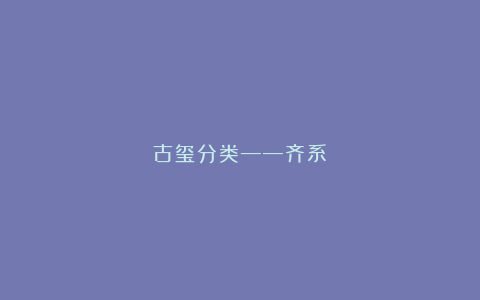
“长金之玺”(图52)白文感觉刚好与朱文相反,四字向中间靠近,线条苍茫生涩,古铜印的特点很明显,此玺以朴茂见长,而灵动不如朱文。
“司马之玺”(图53)“司”字作反写,为其巧妙处。
试想如果把“司”字正写,势必会影响“之”字右侧的空间,“之玺”二字的气势会遭到破坏,而“司马”两字也不能浑融一体,在气势上也不如现在来得落落大方。此种章法须配上荒率不羁的冲刀线条,方能相映得趣,缺一必将流于做作。
“口口玺”(图54)的线质很特殊,如同刻在木质上,全无铜印的苍茫锋利,转角处以圆润为主。曾见清代用木板翻刻的印谱,气息与之很相似,而精彩者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异趣。
“右闻司马”(图55)的在齐系官玺中有此一类似,线条细劲婀娜,很精致。
“左司马”(图56)和它属于同一风格,因“左”的险势,此印较前者显得更为灵动。
齐系古玺的特点比较明显,如“马”字下垂的长线,“陈”底部加“土”旁,最为怪异的莫过于印面顶部有凸起部分,为齐系古玺的标志性符号。此方“鹿之玺”(图57)有多种版本,在此一并录出(图58-60)、其他齐系古玺见图61-62。
【声明】:本公众号转载的所有内容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如若不宜转载,请及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