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得长如此
年年物侯新
1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
唐史青《应诏赋得除夜》
【赏析】:史青在宫灯摇曳的除夕宴席上写下这十个字时,定是听见了长安城此起彼伏的钟鼓声。
奉诏而作的诗歌里,藏着诗人对永恒时间的参悟,更流淌着盛唐气象特有的从容气度。
这看似简单的时序更迭,在诗人笔下成为天地间最庄重的生命仪式。
“今岁今宵尽”五字如暮鼓沉沉,将三百六十五日的时光浓缩成一片薄薄的夜色。
诗人站在年岁的门槛上回望,望见的是大明宫中蜿蜒的烛光,是曲江池畔消融的积雪,是千门万户守岁的剪影。
这个”尽”字并非终结的叹息,而是将过往岁月收束成礼盒的绸带,系着无数值得珍藏的吉光片羽。
而当”明年明日催”的清音响彻宫苑,晨光中的长安正抖落星辰的碎屑,朱雀大街的青石板开始苏醒,准备迎接新岁的车马。
这个”催”字不是仓皇的鞭策,而是生命之流永恒的涌动,是春天在冻土下舒展筋骨的萌动。
在这首应制诗的肌理中,流淌着超越皇权颂歌的哲思。
诗人将时间的流逝转化为天地运行的韵律,让君王的宴席与百姓的灶火共同沉浸在宇宙的节拍里。
宫墙内外的守夜人,都在等待同一个黎明;未央宫的铜漏与终南山的积雪,都在丈量同一种永恒。
这种将个体生命纳入天地时序的豁达,让诗句褪去了应制诗常见的脂粉气,显出浑朴的生命质感。
当诗人说”催”,不是催促皇权永固,而是催动万物生长的春信;当诗人说”尽”,不是终结盛世华章,而是将过往的吉光片羽酿成滋养未来的美酒。
史青用极简的笔触,在宫廷宴席的浮华中辟出一方澄明之境。
他把新岁的祝福寄托在星辰运转的轨迹里,将帝王的年号消融在永恒的时光长河中。
那些在宫灯下举杯的君臣,那些在寒夜里围炉的百姓,都在此刻成为时间洪流中平等的旅人,共同接受着岁月最庄重的祝福。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应诏”——不是应和帝王之命,而是应和天地之道,在辞旧迎新的门槛上,为所有生命献上最深的祝祷。
2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唐·李世民《守岁》
【赏析】贞观七年的除夕,李世民提笔写下”共欢新故岁”时,曲江池畔的渔火与含元殿前的宫灯正连成星河。
这位缔造盛世的帝王,在守岁的更漏声里褪去冕旒,将万里山河的祈愿融进墨香。
“共欢”二字如春雷滚过冻土,震碎阶前残雪。
朱雀大街的商贩在暮鼓中收起幌旗,灞桥驿道的游子顶着北风叩响柴扉,戍边的将士传递着温热的酒囊——这些细碎的声响都化作”欢”字的笔画,在君王笔端流淌成金丝银线。
长安一百零八坊的炊烟里,既有未央宫膳房飘出的驼峰炙香,也有寻常巷陌灶台上蒸腾的黍米甜香,却在守岁的暮色中缠绕成同一缕人间烟火。
“迎送一宵中”的时空折叠,让永恒与刹那在铜壶滴漏里达成奇妙和解。
子时的钟声未至,太极殿前早已铺满朝阳般鲜红的爆竹碎屑,仿佛提前铺就通往新岁的红毯。
李世民凝视着沙漏里坠落的时光之砂,看见的不仅是帝业永祚的祷祝,更是渭水河畔解冻的冰凌,终南山下返青的麦苗,丝绸之路上重新启程的驼铃。
那些在”迎”与”送”之间流转的光阴,不是单薄的年轮刻痕,而是整个帝国吐故纳新的呼吸。
这位马背上得天下的帝王,将剑锋般的锐气化作砚中春水。
当群臣举着夜光杯恭贺”万寿无疆”,他的笔锋却轻轻掠过个人的寿数,在”共欢”处洇开浓墨。
太极宫高悬的明灯,此刻与陇右老农门楣上的桃符达成某种默契:守岁不只是皇家的仪式,更是万千生灵对时间的集体盟约。
那些在寒夜里绽放的爆竹,既送别了过往的烽烟,也迎接着黎明的犁铧,将帝王的祝福化作播种在冻土下的春信。
3
韶华常在,明年依旧,
相与笑春风。
宋·张先《少年游》
【赏析】:垂拱殿外的杏花第三次飘落时,张先在汴京酒肆的阑干上题下这阙词。
暮春的风掠过樊楼飞檐,带着新科进士们的簪花余香,把那些醉倒的玉杯罗帕都染成了流动的胭脂色。
这位以”云破月来花弄影”惊艳天下的词人,却在觥筹交错间捕捉到了时光永恒的密码。
“韶华常在”四字落墨时,檐角铜铃正惊起一群白鸽。
词人望见金明池畔的秋千架上,去年系着的红绸尚未褪色;听见州桥夜市的叫卖声里,分明混着去岁元夕的笑语。
那些被世人哀叹的易逝流光,在他笔下化作绕指柔的丝线,将记忆中的春色缝缀成永不凋零的锦缎。
这声”常在”不是虚妄的挽留,而是看透聚散后的顿悟——当我们在某个瞬间真正活过,刹那便成了永恒。
“相与笑春风”的邀约里,晃动着大宋最动人的生命图景。
词人或许正想起洛阳牡丹花会上,白发翁媪携手指点姚黄魏紫;念及江南贡院放榜时,落第举子与高中者共饮的浊酒;瞥见虹桥下的船工,把汴河的粼粼波光舀进粗瓷大碗。
这些此起彼伏的笑声穿透朱门蓬户,在四月的空气里交织成抵御岁月侵蚀的经纬。
当张先说”相与”,不是在许诺具体的重逢,而是将人间烟火凝成琥珀,让每个春天的笑容都成为时光长河里的航标。
汴京的暮鼓穿过三百年的烟雨,至今仍在叩击着现代人的窗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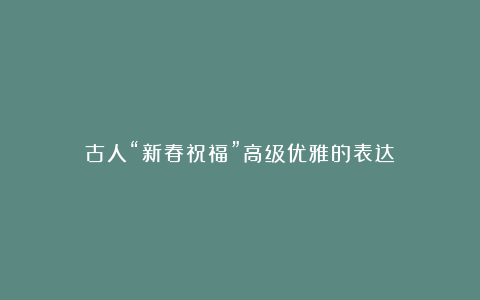
当我们吟诵”明年依旧”,或许该看见词人藏在醉眼中的澄明:真正的祝福不在对抗流光,而在确认此刻即是永恒。
那些与至交痛饮的春夜,与爱人漫步的樱堤,与稚子放飞的纸鸢,都已在发生的瞬间镌刻进宇宙的年轮。
来年陌上花开时,我们迎向春风的笑容里,永远住着所有不曾老去的往昔。
4
愿除旧妄生新意,端与新年日日新。
宋·詹初《新春》
【赏析]:建炎三年的雪落进砚台时,詹初正在武夷山麓结庐而居。
南渡的烽烟在千里之外明灭,这位弃官归隐的理学家,却在破碎的山河间窥见了永恒的春信。
墨汁晕开的涟漪里,”旧妄”二字渐渐沉底,浮起一簇照亮整个南宋的莲灯。
“愿除旧妄生新意”,笔锋如犁铧剖开冻土。
诗人不是在清扫门庭前的爆竹碎屑,而是将整个时代的沉疴置于解剖台上:汴京御街的脂粉金迷,党争漩涡中的口蜜腹剑,北望王师时的怯懦犹疑——这些堆积成山的”旧妄”,在理学家眼中皆是蒙蔽心性的尘埃。
当他说”除”,是持一柄寒铁铸就的刮骨刀,要剜去寄生在士人脊梁上的精神沉疴;当他说”生”,则是捧出濂溪先生窗前那株新荷,让儒家心性之学在战火焦土中重新抽芽。
“端与新年日日新”七字如晨钟破晓,震落瓦当上的冰凌。这声祝福里没有烟花彩胜的喧闹,却藏着《大学》”苟日新,日日新”的幽微光亮。
诗人望见武夷云雾深处,采药人将陈年腐叶埋作春泥;听见九曲溪畔,樵夫把钝斧磨出新月般的锋刃。
那些在”日日新”中翻涌的生命力,既是天地不言的大道,也是匹夫有责的担当。
冻僵的墨条在砚台徐徐化开,仿佛看见南渡衣冠正褪去旧时华服,在江南的杏花雨里重获赤子之身。
5
共祝明朝属日好,梅花满眼踏新年。
明·吴与弼《除夜次唐诗韵》
【赏析】:宣德八年的雪落在鹅湖书院檐角时,吴与弼手中的《朱子语类》正翻到”格物致知”的章节。
远山传来除岁的爆竹声,震落了窗棂上的冰花,这位理学大儒忽然搁下朱笔,任墨迹在《除夜次唐诗韵》的笺纸上洇开梅花状的涟漪。
“共祝明朝属日好”七字破空而来,惊醒了沉睡的砚池。
这不是汴京瓦舍里商贩的吉利话,而是浸透着鹅湖学派特有的宇宙观——当诗人说”共祝”,不是在邀约书斋里的三五知己,而是在唤醒蛰伏于万物的天理:
南亩的冻土下有麦种在倾听,北窗的竹简里有圣贤在低语,甚至赣江上的冰裂声,都是天地对黎明的唱和。
这个”共”字如同冬至后的第一缕阳气,将庙堂的钟磬与阡陌的耒耜,都编织进同一张春的经纬。
“梅花满眼踏新年”的奇绝处,在理学家的笔锋里化作知行合一的宣言。
山门前那株老梅的虬枝上,积雪正簌簌抖落朱砂似的花苞,恰似程门立雪时飘落的冰晶,又像鹅湖之会上飞扬的唾沫星子。
当诗人以”踏”字连接梅花与新年,暗合着”即物穷理”的治学精魂——那些落在草鞋上的梅瓣,不只是春的信使,更是通向天理的阶梯。
儒生们踏过的不是寻常落英,而是王阳明尚未说破的”心外无物”的禅机。
吴与弼把程朱理学的森严法度,酿成了可以共饮的屠苏酒;将唐诗的丰腴气象,锻造成能照见万物的格物之镜。
当爆竹声再次摇动书院梁柱上的积尘,那些纷飞的梅瓣与雪片,已分不清哪些是前朝的月光,哪些是今岁的春信。
唯有”共祝”的余韵在山谷间回荡,将理学家冷峻的思辨,暖成了人间最温厚的祝福。
6
去岁千般皆如愿,今年万事定称心。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释义】:景德元年的雪落在汴京大相国寺时,香积厨的茶汤正煨着岁末的余温。
释道原将这两句偈子题在《传灯录》的边页,笔锋扫过之处,千年前的灯花忽然爆出惊雷般的暖意。
“去岁千般皆如愿”的机锋里,藏着禅宗最深的慈悲。
老僧望向香案上渐短的灯芯,看见的不是世俗愿望的清单,而是众生在因果链上攀爬的轨迹。
那个”愿”字如春蚕吐丝,将贪嗔痴慢都裹进晶莹的茧房——去年的桃花为何灼灼?去秋的霜叶为谁而红?
当他说”皆如愿”,实是在说娑婆世界的每一片落叶,都精准飘向命定的沟渠。
这声祝福里没有分别心,既许给朱门酒肉的信众,也渡着茅檐霜鬓的樵夫。
“今年万事定称心”的断言,恰似达摩洞前的晨钟穿透岩壁。
禅师不是在预言吉凶,而是为众生点破”应无所住”的真谛。
那些在香火中翻飞的祈愿笺,那些在佛前叩首的锦袍客,若懂得”称心”原是心头月,又何须向外求取水中影?
大雄宝殿的积雪正消融成檐角清露,每一滴都映着三千世界的圆满。
这十二个字在灯录的海洋里,犹如迦叶尊者拈起的那朵金婆罗花。
当后世僧众在岁末围炉参话头,或许该听见雪落青灯的密语:真正的祝福不在改易外境,而在证得”日日是好日”的禅心。
你看那茶釜里沉浮的松针,不正是去年今日飘落的同一片碧翠?
若是喜欢,点个在看或点赞,再走吧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