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医阿乌雷列奥、理发师瓜迪奥拉和希拉尔多大夫,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各有特色。
一、牙医
牙医和堂萨瓦斯曾经并列游击队之首,为人和口碑截然相反。牙医为人低调,跟外人交流不多,形象正面。
关于他的最大疑问是,他当年怎么幸免于难的。
他和几乎会跟全镇打交道的大夫、理发师也不一样,小说没写过他“上门送医”,去他诊所看牙的人只写了镇长这个大仇人和“知心好友”本哈民。
1、家庭生活
他正面出场只有4次:给镇长拔牙,给镇长检查牙齿情况,给本哈民换假牙,宵禁后叫女儿回家。
他的外貌不太起眼:干瘦、身材矮小、秃头,浑身的腱子肉——非常符合游击队员的外在形象。
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餐厅家具基本都是旧货摊买的,花盆里种的是药草,20岁的女儿安赫拉还得补袜子。
但家庭氛围很温馨。
安赫拉是这个家“对外交流窗口”,她会跟父母说小镇的“新闻”,比如谁谁要搬走了,镇上来了马戏团,还详细描述了其中一个节目。
牙医对搬走的人发表一点看法,并期待女儿的见解。他眼中的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瘦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听完女儿的描述,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
收音机是牙医另一道接收外界信息的窗口,他平时没事就听收音机,听到过新闻和科普知识。
他能发现妻子闷闷不乐,并认真听她的烦恼,安慰她。妻子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她也要离开。牙医的话信息量很大:
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别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的。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
妻子说“知道是谁贴的就好了。”他说“谁贴的谁知道。”
这段透露了过去的情景,也暗示了现在的情况——有些匿名帖是他和大夫等人贴的。
2、幸存者
牙医一家是名副其实的幸存者:
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能逃过这一劫,很不可思议。镇长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有几,把枪,都是什么样的枪。
但他和镇长还是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小镇,俩人之间保持一种诡异的和平。
镇长应该是想尽量避免跟牙医碰面,但因为牙疼,这两个“大仇人”共处一室,牙医一对四,表现毫不逊色。
对镇长来说,他确实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3、发传单
小说正面描写发传单,只有牙医和理发师。
两个人都是从对面说话的语气里感觉到,这应该是盟友,然后拿出了秘密传单。
理发师对法官还带点引诱的意思,牙医和本哈民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
牙医坦承“我这个人胆小怕事”,本哈民马上说不是,交谈的最后,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这句话打动了牙医。
中间本哈民还抱怨“从这里(匿名帖)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
牙医给本哈民传单,都不用多说什么: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还在干?”牙医点头。
二、大夫
看起来大夫算全书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大众对医生的印象是救死扶伤,默认医生有慈悲心肠,大夫符合这个形象。
作为小镇唯一的医生,他和所有人都关系融洽。
1、观察和思考
大夫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善于观察和思考。他见过蒙特罗岳母的次数不会太多,但能一眼认出来,还提醒镇长。
7年前,罗莎利奥第一次来到小镇,现在,罗莎莉奥跟着母亲离开小镇,大夫都是见证人之一。
他一边刮脸一边思考:
到小镇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她步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开始。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阄,中了彩。
一眼认出别人家亲戚,还能清楚记得别人家的婚姻、职业情况,重点是能想到“步入社会现实生活”,“抓阄中彩”,简直是拉美的“朝阳群众”。
这正是希拉尔多大夫的独特之处。
2、匿名帖
大夫也是反对派,他和理发师因为职业关系,要跟小镇几乎所有人打交道,这是他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不过他们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理发师讲10句,9句都别有用心,第一句是接话或者开启话题;大夫则9句日常闲聊,一句灵魂拷问直击心灵。
理发师广撒网,大夫“专攻”神父。
大夫这样有社会地位、有大智慧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反对派?
大概是小镇的现状实在无法直视,他在努力寻找出路。
想想过去每逢宵禁,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枪响,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橐橐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种恐怖活动的动静。很多个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
当初混乱的夜晚,小镇每家每户都跟大夫一样。这一段既有客观事实的描述,也有心理描写,读者会有身临其境的共情。
大夫是个有精神追求的人,他和妻子一起在午睡时间读狄更斯小说,他关注到报务员在用电报给意中人传诗歌和《悲惨世界》,还点评说《悲惨世界》工程量大,不如传大仲马的小说。
读世界名著对他的观察和思考应该很有帮助。
蒙特罗寡妇儿女都在国外,迫不及待要变卖丈夫的遗产跑路,但镇长和堂萨瓦斯都觊觎遗产。她装病,大夫配合:“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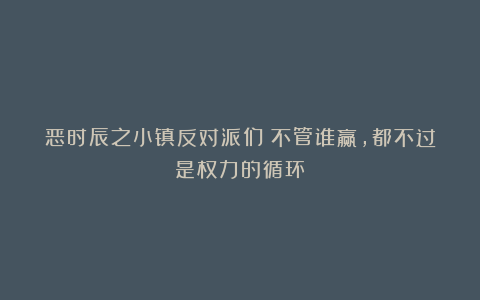
寡妇盲猜匿名帖是大夫贴的,这大概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吧。镇长和堂萨瓦斯的匿名帖肯定是大夫等反对派贴的。
小镇跟外面有联系的人,只写了镇长、神父、法官、阿希斯寡妇、大夫。
大夫收发电报是详写,收信是一笔带过。他收到的电报说“请告如何发货。”还跟报务员解释了一句:“货”是盐镪水。“街上热得像蒸笼”,大夫明知道不会下雨,还安慰报务员说会下雨。这言行妥妥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货”八成是违禁印刷品——匿名帖或者传单,或者二者都有。
堂萨瓦斯有糖尿病,大夫跟他的医患关系相当融洽。堂萨瓦斯把匿名帖当小说看,承认关于他的匿名帖的真实性,还自己爆料说他们父子糟蹋黄花闺女。
可想而知以前他还爆过多少料,也可以推测,匿名帖就是大夫写的,以后还会出现新的关于堂萨瓦斯的匿名帖。
大夫走家串户到处听到人们谈论匿名帖:
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人们发牢骚,一概不置可否。其实,他一直在开动脑筋,探求结论。
他向神父寻求答案。
3、“策反”神父
大夫还有一个特点:口才特别好。
他跟镇长、神父这种“高手”辩论从无败绩——镇长是个能言善辩的政客,神父的本职工作是替别人“洗脑”、让别人信教,大夫的功力可见一斑。
他的口才大概得益于他的观察、思考和阅读。
大夫和神父有3次深度交流、1次并肩作战的经历,在镇长的助攻下,最终“策反”神父。
第一次深度交流,大夫带神父去看一个病得快死的孩子,说“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
神父大受震撼,心境大变——怎么变?
第二次,神父偶遇大夫,问他“您的病人怎么样?”他回答以后反问一句“您的病人呢?”神父问他为什么要这么问,他说“听说您的病人当中正流行着一种很厉害的时疫”。
把神父比喻成医生,已经非常恰当,再把匿名帖比作“时疫”,更妙了。
神父一直回避问题,大夫坚持问。神父回答得很敷衍: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大夫委婉指责神父不负责任:“我们当医生的,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诊断。”
第三次,神父偶遇大夫,大夫说看神父的肝不太好,主动要求给他做检查、量血压。神父打量四周,说大夫的诊所“缺一张圣像”,大夫说“镇上也缺圣像”——神父真的太像机器人了。
神父说“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大夫问:
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神父根本不是对手,愤而离开。
大夫再出场,是佩佩被杀,镇长捂盖子,他和神父去找镇长。他们俩一起面对镇长的枪,表现各有千秋。
神父嘴比大夫笨,很少说话。
大夫客客气气地掀盖子:
我白等了,整整一下午我一直等着您叫我来验尸。
在咱们镇上没有不透风的事。从下午四点钟起,大家都知道你们把那个小伙子干掉了,和堂萨瓦斯害死卖出去的驴用的办法一样(说这句话的表情是“笑吟吟的”)。打开窗子说亮话,这个尸非验不可。监狱的犯人都爱得晕厥病,这个秘密现在也该揭开了(大夫说这句话再合适不过)!我喜欢这样,现在我们算是知道谁是谁了。
镇长也不是对手,只能亮枪。
大夫见好就收,拉住神父下楼梯。
走到警察局拐弯的地方,两个人分手,神父眼睛里已经有泪水。大夫安慰他说“不要大惊小怪,生活就是这样”。
之前神父和大夫不欢而散,再出场俩人又并肩作战,马尔克斯没有写他们是怎么达成共识的。
但神父的变化在这里揭晓了答案,他变得更有“人”性、更勇敢了,这当然离不开大夫的作用。从结果来看,大夫去找镇长的目的好像就是让神父“受教育”。
按照“职责分工,”神父才是那个给大家精神指引和抚慰大家精神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跟镇长交涉的人。
大夫干了神父的活,还干得很漂亮,神父的“倒戈”合情合理。
这次的对峙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大夫这是“自曝”。
某一次宵禁,“诊所的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咔咔声,”镇长给大夫背书:“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
对峙当晚就是大搜捕,大夫这次肯定不能幸免了。
三、理发师
小说最后一页说从理发馆搜出了武器,证实了他“反对派”的身份。在此之前,他只是表现得很可疑。
他经常快速接住顾客的话,把话题引向时政或者对“当局”的不满。
卡米查埃尔觉得坐在那里无聊,问有没有报纸,他说“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法官说周一人镇上人少,“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理发师说“你们巴不得这样”。
他在店里贴了一张“莫谈国事”的纸条,但他跟每一位来理发的顾客谈论时事,趁机说一些别有用心的话引导顾客生出反感情绪。
小说着重写了他跟卡米查埃尔、摩西、镇长、法官和值夜伙伴的交谈,职业和性格各不相同,理发师采取不同的策略,跟卡米查埃尔和法官这种身兼要职的人,他还不着声色地套话。
镇长刚实行宵禁时,理发师被抓了壮丁去巡夜。
后半夜他和小伙伴跑去屋檐下躲雨,俩人总共说了六七句话,他也能煽动情绪。说我们在这站岗,“雨底下挨浇”,镇长警察都在办公室里潇洒。
他太擅长“见人说人话”,刚给卡米查埃尔好一顿捧,卡米查埃尔走了,摩西进店,他马上跟摩西吐槽卡米查埃尔。
前面的吹捧和后面的吐槽用词都非常夸张,形成鲜明对比。既表现了理发师的性格,也交代了卡米查埃尔在小镇居民中的形象,还刻画了卡米查埃尔背后的蒙铁尔的形象。
理发师跟每一位顾客谈论时政,但从没谈过匿名帖。他有没有参与?如果有,他不谈或许是怕暴露?毕竟他话还挺多的。如果他没参与,他知不知情?
牙医让人钦佩,他怼镇长看着很痛快。大夫很和善,他“点化”神父,干得很漂亮。可是理发师让人心生警惕。卡米查埃尔嫌理发师聒噪,说宁愿让老婆理发,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
在小镇那样的环境下,理发师的反抗很勇敢,但为什么我会反感他这种“拉人”方式?因为他不真诚。
如果我是这位理发师的顾客,大概率是会当没听见,不接话,以后再也不会去这家店。勇敢一些的人肯定会跟他辩论。
2024年读这本书,理发师给我的启示是,要警惕网络中那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不要被理发师这样的人煽动情绪。
四、反对派的结局
有一个问题很致命:反对派没有足够的动力和明确的目标。
结局大家上山打游击的原因是大搜捕,这是紧急情况。一旦危机解除,比如镇长采取怀柔政策,那些跟着打游击的人信心还能不能坚定?有多少人会选择回到小镇?
这大概也是游击队里有堂萨瓦斯这种叛徒的原因之一。
《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上校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军队虽然连连告捷,但后来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
这么来看,反对派赢面不大,小镇还会处于这位镇长的独裁统治之中。那么会出现新的反对派,双方继续开展斗争。《恶时辰》的故事再来一遍。
假设反对派侥幸赢了,小镇会有新的镇长。新镇长到来,小镇又要重演之前的惨剧,《恶时辰》的故事还是要再来一遍。
不论反对派输还是赢,小镇永远都处在这样无止境的“恶时辰”之中。
作者:转蓬飘飘(斡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