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收藏后再去!敦煌石窟里的十个重要历史事件(上)
敦煌莫高窟,这座矗立于戈壁的千年艺术宝库,不仅是一处佛教圣地,更是一部刻在崖壁上的“立体史书”。
它的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串联起从十六国到元代的文明密码。
本文解码敦煌石窟中记录的十个重要历史事件。
01
佛教东传:汉武帝拜金人(第323窟)
莫高窟第323窟《汉武帝拜金人》讲述了佛教东传入中原的故事。
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征匈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将其供奉于甘泉宫,视为“天神”。后世佛教学者将“金人”附会为佛像,借此构建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记忆。
画面中,汉武帝率群臣面向两尊金人躬身礼拜,金人立于高台,衣饰华贵,形似佛像,身后侍从持幡随行,远处城池巍然,祥云缭绕。壁画虽非严格史实,却折射出佛教东传与中国文化交融的深层逻辑。
汉武帝的“礼拜”姿态,既暗合帝王对异域神祇的包容,亦暗示佛教初入中原时依附本土信仰的生存策略。
画中金人造型兼具健陀罗风格与汉地审美,面容圆润、衣纹流畅,与同期中原造像的朴拙形成对比,彰显丝路艺术的影响。
此外,壁画以“城阙”象征长安、“山川”代指西域,通过空间叙事将佛教传播路径视觉化,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珍贵缩影。
02
六朝古都:康僧会建业传法图(第323窟)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同时也是十朝都会。2500年的建城史,450年的建都史,漫长而沧桑的历史,为南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魅力。
南京的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壁画里呢呢?这背后其实就是佛教东传的南北朝分裂的写照。
莫高窟第323窟有一幅康僧会建业传法图,描绘的就是东吴时期,西域康居国高僧康僧会来到建康(南京)传播佛教的故事。
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域康居国高僧康僧会来建康宣传佛教,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看他们穿戴很奇怪,怀疑有诈。孙权得到禀报,召见了康僧会。
康僧会从南方一路北上,对南朝风俗已经比较熟悉,他知道南朝对“神通”的需要,所以虽然佛教不提倡神通,但为了弘法康僧会选择了妥协。
在见证了康僧会感应舍利的神奇方术之后,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初寺,这是南京乃至江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同时,孙权还兴建阿育王塔,以迎接供奉佛骨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原因,江东吴地佛法大兴。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以南京为首都,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阶段,隆盛整个江南。也就成就了杜牧诗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幅壁画可以分为4个画面:康僧会泛舟来到建业;康僧会向孙权敬献舍利;孙权在建业修造建初寺;孙皓郊迎康僧会。
这4个画面自由穿插,没有顺序,整个故事都安排在山川纵横的自然景色中,说明佛教除了陆路传播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传播之路。
03
凿通西域:汉武帝的丝路雄心(第323窟)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讲述了张骞凿通西域的故事。
绘制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初唐时期,正是道居佛先、佛道之争不息的时代。佛教信众借张骞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两百多年,以此与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抗衡。
佛教信众们借着张骞的名人效应,给张骞凿空的壮举来了一次历史错位,赋予了引入佛教的新含义。这幅赫赫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其实就是早期的连环画。
这幅图是莫高窟第323窟的八幅佛教史迹画之一,其他七幅也多有史实可考。当时的敦煌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绘出一部佛教史绘本,用图像记录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公元前二世纪,大汉的北方边境长期笼罩在匈奴侵扰的阴霾之下。某天汉武帝忽然得到个重要情报,匈奴人把月氏人撵得一路向西,砍死了月氏王不说还把他的头拿来做了个酒杯。汉武帝觉得摆平匈奴的机会来了,立刻出了个方案,派人去联络月氏一起合伙暴扁匈奴!
建元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27岁的郎官张骞接过汉武帝赐予的旌节,百人使团驼铃叮当向西而行。他们背负着帝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却不知前方是长达十三年的炼狱征程。
刚出陇西,匈奴骑兵如黑云压境。单于将汉使旌节掷于沙尘:”月氏在我北,汉使安得越?”幽囚岁月里,张骞的旌节成了暗夜火炬。他在毡帐迎娶匈奴女子,却将汉节深藏衣襟;他学会骑射牧羊,却将西域地图刻在羊皮。当随从们陆续消逝在风沙中,唯有甘父仍守护着那截褪色的旌节。
元光六年冬,趁匈奴内乱,张骞携妻带仆策马狂奔。穿越白龙堆雅丹时,他们舔饮马血维持生命;翻越帕米尔雪山时,冰棱割裂的脚掌在石径留下血痕。当大宛国王见到这个衣衫褴褛却高举旌节的汉使时,惊叹:”此真天神使者!”
然而历史的玩笑如此残酷。当张骞终于站在妫水河畔,昔日的复仇者已化作粟特平原的富庶之民。大月氏女王轻抚镶嵌宝石的酒盏:”汉使请看,这里可有头颅酒杯?”张骞仰天大笑,笑声中既有悲怆更含顿悟——战争阴云外,他窥见了更辽阔的世界。
归途再陷匈奴牢笼,妻子冒死传递消息助其脱困。元朔三年深秋,长安城门开启时,49岁的张骞须发皆白,怀中旌节仅剩秃杆。但随他东归的,除了胡妻与甘父,更有葡萄种子、龟兹乐谱与三十六国舆图。
未完成的军事盟约,意外熔铸成贯通东西的文明金桥。当他的马蹄印渐渐化作商队车辙,一条横贯欧亚的史诗之路正在觉醒——这不是败将的归途,而是征服者王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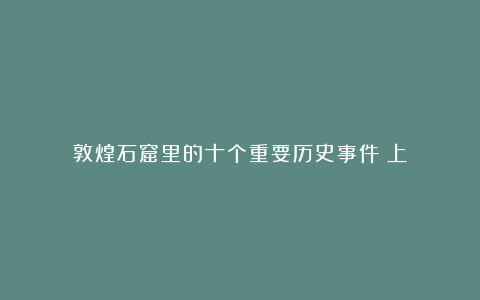
敦煌研究院
04
五胡乱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阵痛(第85窟)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至439年,匈奴、羯、鲜卑、羌、氐五大胡族相继在中原掀起腥风血雨。
西晋因八王之乱耗尽国力,内迁胡族趁机起兵:匈奴刘渊首建汉赵政权,羯人石勒屠戮洛阳引发“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建立东晋。
北方陷入混战,前后出现十六个割据政权,慕容鲜卑建前燕,氐族苻坚一统北方又败于淝水之战,拓跋鲜卑最终建立北魏终结乱局。
这场持续百余年的动荡彻底重构中国版图:汉族士族“衣冠南渡”,推动江南开发;胡汉文化剧烈碰撞,佛教传播加速,游牧铁骑与农耕文明在血火中孕育出新的制度。
五胡旋起旋灭的霸权更迭,最终为隋唐多民族帝国的诞生埋下伏笔,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而深刻的民族融合熔炉。
十六国中后期,敦煌属于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北凉,因为地处偏远,所以远比中原地区要更为稳定。这时候,一个名叫乐僔的僧人,来到了敦煌,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
由于战乱的影响,北凉的经济发展落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需要精神支柱,而统治者们也需要思想工具,佛教的传播在这段时期得到统治者们的支持,以佛教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大量涌现。
当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随着佛教一起传入的还有西域的绘画风格与造型特点,敦煌由于拥有特殊地理位置,相较于其他中原地区,更容易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北凉时期敦煌石窟,与其他位于中国内陆地区的同时期石窟壁画相比,多了一份西域的特色。
敦煌莫高窟中有三个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分别是第275窟、第268窟、第272窟,时间大致是在421—439年间。
这三个窟中的壁画内容显而易见受到了西域佛教壁画内容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北凉敦煌壁画中大量的飞天,在这个时期的洞窟里,飞天还是西域的形象。
北凉石窟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壁画的构图,在人物布局上,取法于西域菱形格因缘佛传画:主要人物一般比配角画得大一些,他们一般都以坐姿出现,这样的构图在其他时期中并不常见,但在新疆的石窟里就比比皆是。
05
佛道之争:神界融合中的文明嬗变(第249窟)
莫高窟第249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其壁画内容以独特的佛道杂糅特征,展现了佛教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博弈与交融。这一时期的敦煌虽名义上归属西魏,实则处于北魏晚期至西魏交替的特殊阶段。
东阳王元荣在此担任瓜州刺史期间(约525年至西魏初年),大力推动佛教艺术发展,却未割裂与中原传统文化的联系。
敦煌作为丝路枢纽,佛教与本土道教、神话在此碰撞,最终在249窟的天顶壁画中凝结为“天界与人间”的叙事空间,成为佛道思想融合的视觉见证。
敦煌研究院
窟顶壁画以覆斗形结构划分为四大区域,形成“天界—人间”的垂直空间:
窟顶西披绘佛教中的阿修罗,其形象立于深海,头顶须弥山及忉利天宫,象征佛教宇宙观的至高权威。阿修罗身后雷公、电母等自然神环绕,细节契合《维摩诘经》中“妙喜国”场景,暗含佛教对宇宙秩序的诠释。
与之对应,南披绘西王母乘凤辇、北披绘东王公御龙车,构成道教神话中的巡天行列。两位主神虽被部分学者解读为帝释天与梵天,但其形象与汉代墓室壁画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如出一辙,暗示道教升仙思想对佛教空间的渗透。
窟顶四披绘道教“三皇”(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四象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羽人”飞仙,其造型源自汉晋墓室升天图,与佛教的阿修罗、摩尼宝珠共处同一穹顶。值得注意的是,道教方位神与佛教须弥山体系的并存,打破了宗教符号的单一性,形成“天界秩序”的复合表达。
249窟的多元神祇体系,映射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适应性变革。佛教初传时被比附为黄老之术,两晋南北朝时期更与玄学交融。窟内道教元素的大量出现,实为佛教借助本土符号降低传播阻力的策略。
东阳王元荣作为北魏宗室,需平衡中原汉文化、鲜卑传统与佛教信仰。壁画中佛道共存的格局,既是对多元族群的包容,亦是对政权合法性的视觉强化。
249窟的壁画语言,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叙事,成为丝路文明交融的缩影。佛道之争在此并非对立,而是通过神界的符号重构,完成了外来信仰与本土传统的共生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