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新书《图解传统服饰搭配》已上线,请多支持
有关端午的起源故事里,有三个历史人物。屈原自不必说,几乎“垄断”了如今有关端午节俗的相关“解释权”,另一位是伍子胥,我们在2017年的《也许我更想纪念那个为报血仇而掀起春秋霸业战火的伍子胥》里聊过他,老读者应该都看到了,新读者可以点链接回顾一下。剩下的一位,也是唯一的女性,便是曹娥。
(曹娥像,网络图片)
水马由来为屈原,越中移吊小娥魂。
江头多少游人看,若个人家孝子孙。
——曹江竞渡
“曹娥”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并不算特别陌生,因为在绍兴境内上就有一条曹娥江,还有以曹娥为名的乡镇,也留有曹娥庙。
(曹娥江流域,上游段又称剡溪)
(绍兴市上虞区曹娥江风景,图/人民日报)
(南宋绍兴府图中的曹娥江于曹娥庙)
但曹娥的故事则比较单薄,浓缩成两个字就是——孝女。
故事说曹娥的父亲曹盱是一个巫祝,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的这个端午节驾船去祭祀伍子胥,结果不幸溺亡,也不见尸骸。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沿江哭寻了十七天后投江殉父。五日后,曹娥抱着曹盱双尸相负出水。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后汉书·列女传》
(曹娥庙山门及墓坊,图/wiki)
(曹娥庙正殿内景,暖阁内奉曹娥像,图/wiki)
因为曹娥是东汉时期的人物,相比后来的孝女故事发生的时间比较早,所以还有一个“中华孝女第一人”的头衔。曹盱迎涛神的江段也由“舜江”更名为“曹娥江”。曹娥殉父的八年后至元嘉元年(151年),县长度尚为她立纪念之,这表示书法史上非常有名的“曹娥碑”,王羲之等人都曾摹写过碑文。
(北宋元祐八年(1093)由蔡卞摹旧时碑文重书之曹娥碑,图/wiki)
(祕閣帖(一) 冊 晉王羲之書孝女曹娥碑,图/台故)
在古代,这种自残尽孝、自戕尽孝的行为是很有市场的,也颇受推崇,相关的事迹在流传过程中也会被反复诉说,使其成为教化民众的“范本”。通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对于现代人来说,一个比一个炸裂,而“曹娥投江”在许多版本的“二十四孝”中都可以看到,并且是女性孝悌故事中的比较典型的一个。
(元人画四孝图,台故)
(北宋曹娥投江砖,北京故宫博物院)
(金代雕砖,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学者们分析认为,女性孝悌故事常常伴有非常极端的烈举,如曹娥投江殉父时年仅十四岁,这在如今也就是初二初三的年纪。这样的烈举却不怎么见于男性的孝悌故事,因为在古代语境下,这个年龄的男性还有延续香火、承担徭役等“义务”,这种以身祭孝的行为也就更适用于规劝女性。
(曹娥抱尸,网络图片)
劳悦强在讨论唐代以前孝女罕见的现象时认为,这种“现象似乎是由于政府、社会以至文人史家普遍地未能够公开承认妇女的孝友行为所致”。
易素梅认为宋代开始对“孝女”的关注而是“移女孝作男忠”,不仅可以用来劝女子守节,还可以用来砥砺男子尽忠,“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要因素是政治,而不是对女性的道德规范”。
(宋女孝经图)
但曹娥的故事真的就这么简单吗?祭祀曹娥又仅仅只是为了封建语境下的孝吗?
《后汉书·列女传》中另有一位孝女“叔先雄”,故事与曹娥极为相似,父亲也是落水而亡,作为女儿的叔先雄也是自沉求父,同样也被立碑纪念,还多了“图象其形”,但叔先雄却没有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当地留下的“孝女渡”与“孝女岩”,图/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李小红的文章认为,曹娥的身份应该是一位巫女,而为她立碑的度尚则是“因势利导,将中原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
首先,曹娥出身巫祝家庭,这点是明确见于记载的,她的父亲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并且死于祭祀涛神伍子胥的活动。而在曹盱死后、曹娥投江之前的时间里,她曾有“投瓜于江”(一说“投衣于江”)以寻找父亲尸体的行为,并伴有言语“父在此,瓜当沈”。这种发出“祝”语以“瓜”(或“衣”)的沉浮为标记物看来判断曹盱尸骸位置的行为,李小红认为这“其实是在行巫作法,只不过她这场巫术活动以失败告终,最后葬身江水而亡”。
(曹娥庙壁画)
此外,当时曹娥生活的会稽地区,社会环境也明显有别于后来推崇的孝悌文化,民间信鬼崇巫的风气十分兴盛。曹家父女的行为都与当地端午祭祀相关,又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巫祝家族,度尚“敏锐地发现了巫女曹娥行迹中可资利用的文化元素”,“通过为曹娥树立孝女之美名、改葬树碑的政举,将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中,成功地将一个巫女塑造成为一个孝女,巧妙地实现了移风易俗的目的”。
尽管孝女曹娥的故事传播开去也流传下来,但在一些原始信仰浸润时间较长的地区,依然对曹娥保有“孝女”标签以外的认知,是她也成为了端午祭祀的对象,而且是非常罕见的端午女神。《云梦县志》中记载“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及瘟司、水神像。”此时的曹娥神位可与屈原、瘟司、水神并立,若仅仅是因为“孝女”恐怕不够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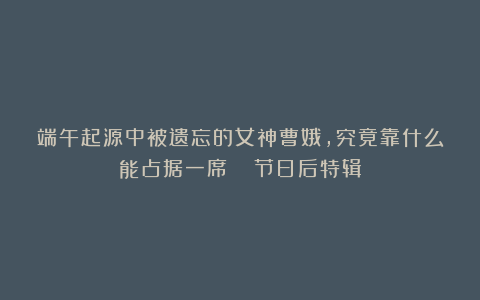
(船头有旗写“收瘟神舡”,图/《龙舟图像志》)
(凤艇上有旗写“姊妹神船”“游江五娘”,图/《龙舟图像志》)
陈志勤将曹娥的形象分成了“礼”“俗”两种:一种是官方层面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孝行教化,用以规范德行”的孝女曹娥,一种是民间层面的“作为水神(江神、潮神)信仰的功能凸显,用以祈福免灾”的水神曹娥。两种各有侧重,但又彼此复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曹娥的影响历。比如,曹娥如果仅是地域性的水神,而没有官方孝女的包装推动,其实也难以从会稽流传到云梦地区的。
作为神灵的曹娥自然需要由许多神迹来作为佐证。其中有两条是关于高丽的,《曹江孝女庙志》载:“宋徽宗大观间,高丽入贡祈潮而应,始封灵孝妇人”;“政和间,高丽贡女过庙进谒,祷娥增貌,宿于庙明日果改佳容,入朝见幸再封昭顺夫人”。
(曹娥神迹“祈潮感应”“高丽谒庙”“祈潮再应”“神风拒贼”图像,图/《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内涵置换的逻辑》)
这两条都很有意思,一条是明确了曹娥作为水神“祈潮而应”的能力,另一条则是关于容貌的祝祷,这本来无关“孝女”也无关“水神”,却是肯定了曹娥作为神灵的基本能力和灵验程度。
曹娥作为水神,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加持,也有别于普通水神。
浙江境内有古运河,如今称“浙东运河”,开凿时间始于春秋,是沟通“京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我们知道水是往低处流的,而跨越多条自然河流的运河就需要解决水面落差的问题,浙东运河最有特色的就是大量的碶闸堰坝设施。尤其浙东运河跨越了钱塘江、曹娥江等重要的潮汐河流,人们就利用潮汐河流的涨落过堰行船。
说潮汐河可能感到陌生,但说钱江潮大家就知道了,钱江潮就是潮汐河流遭遇喇叭形河口形成的。曹娥江也有潮,大约在南朝宋至南宋间修建有梁湖埭,曹娥江潮变得汹涌,潮水一路可至剡县,同样的,乘潮而行也便成为诗人笔下的快事。后梁湖埭改建为梁湖堰,曹娥江潮便平静许多,宋诗《过曹娥江》便道“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2011年曹娥江大闸建成后就彻底拦住了咸潮,如今应该是看不到曹娥江潮了。
(钱塘江与曹娥江的入海口,图/百度地图)
(曹娥江潮,网络图片)
(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网络图片)
但潮汐河的涨落并不完全等同于潮汐时刻,而是会受到河流与海洋的多重影响,非常容易就受困于堰坝前,所以高丽人以及其他有关曹娥水神的祈祷中才多为“祈潮”。
曹娥江运口有曹娥堰,在许多历史名人的故事中悄悄留下印记。如《穿越1488年:我们路过了大明朝的江南风烟》里提到过的崔溥,过上虞县时就提到“舍舟过坝,步至曹娥江,乱流而渡”,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走的水路,来回都经过了曹娥堰并留有诗句。
(明清浙东运河上虞段,图/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因为天然河道与运河之间要过船舶,一般需要卸货下客,用人力拖拽或牛拉绞盘等方式把船运过堰坝,或者为了提高效率,不拖船而直接换船。
拖船过坝遇到水流条件不佳时,如水位太低、受潮汐影响改变水流方向等,人货物都需要等待,堰坝边就十分拥堵。宋诗《曹娥堰打船》就有“浦浅舟难人,月斜潮始生。牛随堰索转,犬吠燎盆明”,说的就是大家等到大晚上曹娥江才涨潮,等待的船只们忙忙碌碌地过曹娥堰进运河。
(牛力拉船过堰坝的景象)
(人力拉船过堰坝的景象)
(浙东运河上的曹娥堰,图/CCTV)
所以,水神曹娥所掌管的不仅仅是水而已,还有交通与经济。
当地有“曹娥人,三过年”的说法,其中一个就是曹娥赛会,据说从五月初五的端午节遗址办到曹娥投江的五月廿二,历时十七天。清诗《曹江五月看龙舟》中写道:“瓣香积火同燔犊,社鼓轰雷走巨鳌。簇起一天花世界,娥心恐未解乌号”,《点石斋画报》有《虔祀曹娥》也记录了当时的盛况,主要参与者还有周边杭州、宁波等地的民众。
(虔祀曹娥)
萧山湘湖、新塘等地还保留有为纪念曹娥的龙舟竞渡活动,称“孝女龙船”。根据民国《萧山县志稿》中所记,当地还曾建有“孝女殿”,“祀曹娥”,并于曹娥投江之日举行孝女庙会。孝女龙船上“搭彩棚配锣鼓”,所以又叫“敲棚龙船”,是专门为了龙舟会建造,平日搁置在宗祠或庙宇中,不做他用。
(萧山湘湖孝女龙船的相关祭祀活动,图/《湘湖风俗》)
(萧山新塘孝女龙船)
按照《湘湖风俗》中所写,孝女龙舟会与附近的西湖龙舟、毗邻的绍兴龙舟都大有不同,龙船有特定的装扮,“旧时还有女童打扮成孝女娘娘”,对象也特定为曹娥,时间不在端午节而是围绕曹娥投江日期开站。以竞渡表演为主,分四色龙舟,船上的人也穿对应颜色的服装,并有一套独特的表演程式。
(不同色彩的孝女龙船)
相比之下,绍兴上虞这些年搞的曹娥祭祀典礼形式就过于歌舞晚会化了,缺乏与传统的衔接点而显得十分悬浮和现代。
(2018年孝女曹娥祭祀大典)
(2019年孝女曹娥祭祀大典)
(2021年孝女曹娥祭祀大典)
(2024年孝女曹娥祭祀典礼)
并且,虽然孝女是曹娥最大的叙事标签,但将曹娥文化等同于孝文化却有一种明显“打薄”处理的感觉。中国古代的孝悌故事与人物遍布各地,曹娥的故事在其中不是最特别的,并且曹娥投江的动机在古代就已经有人疑惑,摆到今天就更加难以说服普通人。
(2019年孝女曹娥祭祀大典)
若说迎合现在所推崇的价值观之一,可能答案就是曹娥庙正殿上。不是正殿里面的“人伦之光”,也不是后面的“孝感动天”,也不是左右的“江以孝永”和“先后同揆”,而是正殿前梁上相传为济公和尚所题的“真是女子”。
(曹娥庙“真是女子”匾)
(1936年曹娥庙正殿“真是女子”匾)
是否真的是济公手书已经不可考了,但这样的匾额倒是见所未见,“真是女子”,也“真是好”!
感谢阅读,喜欢请记得分享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