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宗白华《中国美术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首诗如果前面全部以实景铺垫,最后必当以情作结,“以虚为实”,使景的铺垫有所指向。因为“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同前)同样的一个景,影映出的诗境可以完全不同,如没有明确的指向,读者便不知所云。
下面略举几例,引以为证。
先来看杜子美的“两个黄鹂鸣翠栁,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用了工整的两联,形成了文字上的对称美。且平仄相谐,读来音韵和畅,语感优美。全诗色彩、声音明丽,动静交织。透过窗和门,看见的是“千秋雪”“万里船”,小中见大、见远,时空跨越,展开无限想象。近景远景相衬,欲即欲离,点染间有虚有实,是一幅极美的没骨山水画。表面上都是写景,然而前面的景都是为最后一句的“东吴万里船”铺垫,形成时空对比,表达作者的思乡之情,也暗含诗人对国家命运的牵挂。明代都穆在《南濠诗话》中强调“作诗必情与景会”,认为“以情结景”,需景为情服务,避免情景割裂。
如果杜子美的这个绝句不能作为“以情结景”的明例的话,那我们来看看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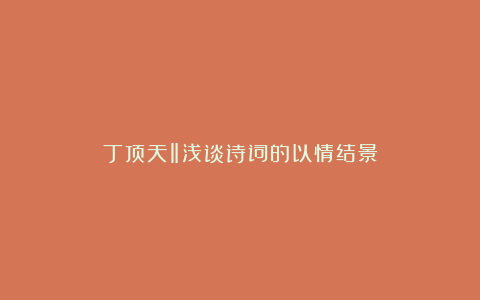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西太一宫乃道教庙宇,故址在今河南开封西南八角镇。而诗人故乡在今江西临川。这里前三句写景,展现艳丽阳春。但末了一句“白头想见江南。”由眼前美景联想起江南故乡的风光,抒发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从起承的景句,到“三十六陂春水”,转得实在太妙。眼前流淌着的渺渺春水,带着诗人展开思绪,想及故乡,将“实”自然过渡到结句“白头想见江南”的“虚”,由“景”自然至“情”,写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正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刘勰《文心雕龙》)白头游子,所见所闻,容易触发叶落归根之情思。如果四句完全写眼前之景,以实写实,这眼前之景就没有了特别的意义,就无法让人由此到彼拓开而转化为诗境了。诗人这样用从眼前实景,到“想见”中的江南,由实入虚,虚实相生,意境一下就展开了。荆公这样处理,避免了直叙“思乡”,从而显得含蓄蕴藉,诗意绵绵。
谈到诗词中的以情结景,大家熟悉的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前三句鼎足对及“夕阳西下”全部写可见可感之实景,末了“断肠人在天涯”,这人在景中,情在景中。断肠人、天涯,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情思不断。这“情”,正是“枯藤”“老树”“昏鸦”“西风”“瘦马”“夕阳”等等萧瑟苍凉之景的心灵映射。
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以情结景”的手法,举不胜举,其终了,和“以景结情”一样,都是为了达到诗的含蓄美。个人觉得,以情结景,这“情”不能完全脱离前面的景而直白表达,应将“情”化景(姑且称为虚景),与前面的实景相称,妙在虚实之间。试看“门泊东吴万里船”肯定是景亦是情,而“白头想见江南”“断肠人在天涯”,“白头”“断肠人”亦是一个“有我”之景,正契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语)和王国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