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石涛 《山水册页》局部
他的终身热爱是写字。
他的生老病死,人生多数时间,都是与字度过。
世人皆知,爱一事易,守之难矣。多少人屡屡更换追求,不如意的,未达成的,就这样丢弃。偏偏邓石如,走向了物质的反面。
他本是拿蜡烛寻路的人,只得点微光自学,好难得在旷野疾步,篆隶有名,却不借势攀附,只在乎哪天得空写字,世上有几人如他痴。耳餐之徒谗谤他,他便离钟鼎远去,做了一世布衣。
他绽放过,留下的并非空寂,只要清风明月在,就有人记得他。
人生何以疏处走马,生命何以长青,六阶课堂上,林曦老师已带大家体会过隶书《崔子玉座右铭》,小世界也曾多次分享邓石如的书论。这一次,只想带着几次扪心自问,你我一同回到,那场不老的江湖梦。
隶书《崔子与座右铭》清 邓石如
上一场同样执拗的雨,下在东汉的长诗里。孔雀东南飞,刘兰芝举身赴清池,韧如蒲苇丝。故事缘起缘灭,皖南民居的马头墙,依旧在淡烟急雨中立着,青石巷内,十来岁的石如,戴瓦楞帽,着蓬草鞋,开始又一天卖饼饵的生活。
轻纱覆城,闲庭深院似近似远可摸,在跑马廊道触雨丝,是念家塾的同龄人解闷所乐,于石如,只生羡慕。九岁那年,命运给了他空档,走漏些幸运,让他尝到了书本味,好景不长,不久后他又回到了,那生他养他的,破落大屋里。
乾隆年间的儒林,也有许多的迷惘的底层读书人,被随意栽植在凋敝的角落,未能考取功名的,为了糊口,只能做点小买卖。
不同于吴敬梓笔下的无路可走,蝇营狗苟,邓家祖辈精于书画,深藏若虚,是甘心以布衣身终老的。石如身上流着一样的血液,自然未敢怠慢。
明 戴进《风雨归舟图》局部
那日正是霞光酡红,粉墙照影,茅草粗泥夯筑的邓家大屋内,如梦如醉。血柏造的古床,已漆色昏沉,是传了几辈的旧物了,到了他这辈,只在少时爱了石刻须臾,却从未下功夫,难道此生,只看着眼前三分地。
恍惚从心底缓缓升起一丝曙光,他决心抓住刹那的动容。
只要肯学,怎会有学不会的事。
十四岁这年,石如时常闭户,翻遍秦汉前人典籍,做苦力省下的银子,尽数买了书去,以树枝为笔地为纸,他越写越快乐,仿佛找到有力的表达方式,世俗哀怨竟抛诸脑后,沉浸在此刻,好像永恒。
他初初写得不好,便寒暑不辍,日日跟着父亲苦练,约莫两三载,那篆刻已有模有样,线条浑厚,如逆水行舟着力,作一幅《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就获得众人称叹。乡间你传我,我传他,都晓得这位了,纷纷来求书。又过三四年,他在乡设馆,做童子师,渐渐不愁衣食。
明 仇英 《桃花源图卷》局部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论深情,书家们个个都不遑多让,可若没好的审美,资质好却没走对路,那与毁坏的玉璧一样可惜。
线条流走中,石如对大千世界的感受也放在里头。他留下了多个第一,篆隶书印皆超当时,也从始至终,守着内心的坚持。
他使的是题海战术。初时只效法于李阳冰,始终是一叶障目,便又追到秦篆,并以两汉众碑额的笔法为范本,取众家之所长,找到偏爱。
李斯的玉箸篆圆凝,线条健实,庄严似秦俑列队。李阳冰浸染唐代雍容,篆风来得线条遒劲。但石如仍觉少一味,便是那静中的动势。太过周正,少了神游的意趣,即是少些生命的。
山野之人石如,自他祖辈起,就与大多世俗风气不对付,在穷乡僻壤,他的思想更是不受绑束。他三十二岁前从未拜师学艺,遂从自我出发更多,执着尚力的审美,半点不由人。
清 髡残 《山水图》局部
他学古而不拘古,沿自身所想一顿挥舞。
他以长峰羊毫作书,一反前人篆法,逆锋起笔,结体大胆奔放,继而篆中有隶,参隶书体势,添加提按的笔画,方圆笔并施,赋予线条灵动。“计白当黑”的金科玉律,更是前人从未想的,旧瓶装新酒,他装得有古气,有新意。
篆书《白氏草堂记》局部 清 邓石如
一回生,二回熟,他又取秦汉碑刻和篆书笔意,化于隶书,长出来新血肉。字形化圆为方,招招精准, 式式熟稔,纵势的比划拖长,重心再往上,似石佛垂脚,跏趺而坐,神态宁静。
明清以来的文人篆刻,多恪守“印中求印”的方法,连丁敬这样的浙派老人,都墨守印内陈规,石如却顽石般,将目光转向印外,学浙派又跳出藩篱,将切刀变为冲刀,融合篆书与刀法,逐渐练得“书由印入,印由书出”。
隶书《张子东铭》 清 邓石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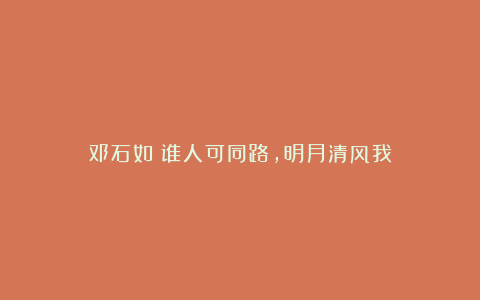
三十二岁后,他与姚鼐、袁枚这样的名流结识,又成为江宁梅镠家座上客,八年内他临遍梅家所藏金石拓片,前五年钻研篆书,后三年钻研隶书,他本是块朴木,幸而和这些人相遇,一步步地,好似河底卵石来渡他成器。
飘进书台的荣辱是非,似字虚处的白,看似无,却影响现实,可使书家审美堕入庸常。可世界不论怎样变,他还是他,若分不清飞鸟各投林,还是直面风雨,能力再大,也是无力。
万物在虚空中流转,沸腾的世界蒸着贪欲,回到大龙山茅屋下,石如晃荡的步伐有了踏实。
乾隆六十年,五十有二的石如,离开了任职的湖广总督毕沅府上,马车绝尘远去,毕沅赠他铁砚,他便拿“铁砚”作山房名,仿佛是下定了决心,余生仅想写字谋活,永不回头。
清 樊圻 《山水册》局部
时间倒回,在江宁梅家的八年,他是极为满足的,巨量的古人碑刻,助他集大成于一家。可时移世易,离开梅家后,他经梅谬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那段北上的日子,真是一场大梦。
偌大的京城,他显得极为渺小,以往的得志傲气,都被踩在了脚下。
恪守古法的正统书坛,限制着书家的视野,作篆者千人一面,一片讨好,奉四大家中的翁方纲书法为圭臬,当时坊间又传言,翁方纲不认可石如书,这话自有几分真,但大抵少不了,那些耳餐之徒颠唇簸舌。
石如被看作是异类,说明白点,不过是几杯羹,难以众人尝。
他带着壮志而来,却是落寞离开,曹文埴一心提携他,又介绍去到毕沅那做幕僚,但人至府中,毕沅幕下的名流如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也是不可一世的,走哪处,石如都能听到他“无书卷气”的闲言。
清 佚名 《邓石如像》
这些人是仰头看人的,因为布衣是他的必需品,而名流贵胄,衣服都是绞金丝,由多个顶级绣娘完工。他大可经曹文埴之手,轻松得个官职,但人在高处会不知不觉忘本。他自小尝民间疾苦,听朱门故事,也无李白的大志,不至于没得选,要趟这浑水。
连弘历八十寿辰,他都适应不了阵仗,骑毛驴独行。
世人皆寻黄金乡,他何必同往?
后来,一个是落魄布衣访友,一个是失势宰相被贬,石如和刘墉倾盖如故,相遇扬州市井,做回了真名士。他们卖字赈灾,又与八怪来往,大家促膝把酒,倾宵未够。石如兼收并蓄,在篆刻创作中,更是吸纳了罗聘的画梅理论,刚健婀娜。
明 陈洪绶《山水人物花卉图册》局部
再次听闻他下山,是他晚年游历,寻找古人碑碣时。西湖啊西湖,许多人被勾留,找到精神归宿。弘一法师在此处出家,林逋一生不沾仕途,隐居孤山,数十年不到朝市,种梅养鹤。
正是疏影横斜时,石如心神摇荡,《完白山人篆刻偶存》里写着,“直疑天上神仙侣,自续西湖处士诗”。他同林逋有很多话想说,他们甚至养鹤的心情也一样。
他又回到山上,像侠客拿着稀世名剑,在印刻中留下“本来面目”四字,暮色暗暗四合,他看到了自我的归来。
可戏中是红梅映雪,戏外却是彩云易散。
他和沈氏本来隔着门第,和二十岁年龄差,这些枷锁都没斩断情缘,直到沈氏夤夜逃走,才成全这段佳话。以为能相伴灌花酿酒,直至耄耋之年,可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五十九岁时,雌鹤西去不久,沈氏也跟着去了。
隶书《梦幻泡影》 清 邓石如
家养那双鹤,平日伴他写字,轻唤几下,就会清灵地叫上几声,可雌鹤在林泉饮水时,遭人拧断脖颈。晚年只余雄鹤作伴,为求心安,他寄鹤养在寺院,卖字的钱尽数修了鹤亭,怎料安庆知府路过,将鹤私自囚禁。
石如害怕继续失去,遂写百封信恳求,最后言辞难掩悲愤,直言还他家鹤,哪怕草民与官斗,搭上性命。他这般情真哀恸,知府樊晋脸红无理,亦怕名声有损,这才放手。
他是至情至性之人,这样的认真,也让他对自身要求甚高,对热爱的事业,愿意花时间,千百次折返。李渔写《闲情偶寄》时,石如还没出生,“不辱不殆,至乐在其中矣”,倒是像极他的知行。知足时不会觉得己不如人,知道有休息时,就不会感到疲惫。
京城书坛讲笔笔有来源,帖学馆阁当道能如何,镜中花影,于镜何碍,他继续他的创新。
明 文徵明 《琴鹤图》局部
在毕沅府做幕僚时,毕沅整日忙于公务,他碰一鼻子灰,手书付梓的心愿落空,也无人说知冷热的话,在外他是冷板凳一坐三年,其实他一天也未清闲,每日天色微明,便研墨满盏,书台上宣纸写到堆成小山,写到墨水干涸,他才舍得歇息。
半年内,他竟将《说文字原》手写了二十遍。他没有倒在一时的标签上,他也没想到,不合六书的结果,是他会自成“邓派”,独立于任何一派。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推崇他,吴熙载承继他,吴昌硕基于他,又将行草书的趣味引进篆体。
书法这张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前人造就越大,后来者不开拓得更辽远,只能算是守成之人。仅以当下眼光评价创作者,是有失偏颇的,古板的总看似正确,而有生命力的,才会跳出时代。
明 文徵明 《浒溪草堂图》局部
年至六十二,石如作《白氏草堂记》,功力更是炉火纯青,他在《赠见源禅友世虑全消》写到,“世虑全消,见几点落花,听数声啼鸟”。他已缓缓老矣,什么世面都见过,却仍是仙风道骨,想去的地方还是要去,以字会友,结识包世臣,授以书论。而后,他的门生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去。
他从山里来,最终沉眠于山风里,他走的时候,答应乡人的碑还没刻完,但会有人替他述说未完的故事。风不住,他的生命亘古长青。
你我来时皆两手空空,才可能无尽拥有,有风波迭起,也会有波光涟漪。
仍然不乏迷恋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