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建馆小记
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筹建於2006年,原址东莞常平镇紫荆花园,本馆集收藏、展示、研究、出版为一体。二十年来历经坎坷,幸而得力於当代诗学会群英们鼎力支撑,更有珠海北师大华文所和澳门大学有关院系一路扶持,始得坚持至今。现包括“路羽书房”“惠兰书苑”二个有生部分,共藏有各类稿存、信札、手迹、签名书、书画、墨宝近二万件。
为更接地气,今年3月初,应好友建议,傅天虹在360个人图书馆官网上,注册了“傅天虹的汉诗馆”,试发几篇后很满意,故决定从2025年4月1日起正式启动,将陆续整理上传傅天虹六十多年来珍藏的史料和墨迹,将各种史实公诸于众,方便大家随时上网查阅所需,以利汉语新诗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请给予关注、推荐。另外,傅天虹藏品也可酌情转让给海内外有迫切需求的机构或个人,作馆藏或研究之用,合作也行,有意者可加傅天虹微信联系。 2025.4.1
当代诗学论坛於2007年3月,创立于北师大珠海分校,至2019年已走过整整十二个年头。先后在珠海、北京、台北、澳门、香港等地成功召开十届。现选辑一百位学者的一百篇论文,以表纪念。
2007年3月,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首届当代诗学论坛)在傅天虹任教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成功举办,此为大会会场
会上,傅天虹倡议并参与发起二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12位发起人聚会留影:左起,朱寿桐、张明远、吴思敬(召集人)、简政珍、吕进、张诗剑、傅天虹(秘书长)、犁青、高戈、、黄德伟、谢冕(召集人)、屠岸(召集人)、盼耕。
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发起人聚会时签名留念:屠岸(召集人)、谢冕(召集人)、傅天虹(秘书长)、高戈、张明远、黄德伟、犁青、张诗剑、吕进、简政珍、吴思敬(召集人)、盼耕、朱寿桐签名志庆。
现实的隐喻与生命的哲思
——简政珍《当闹钟与梦约会》管窥
熊国华 | 文
熊国华,男,1955年4月出生,湖北武汉人。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副主任,兼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侧重于唐代文学和魏晋小说,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现代诗学的研究。被学界认为是20世纪对《世说新语》的文学、美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知名诗评家、诗人。
简政珍是台湾中生代诗人的一座重镇。他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季节过后》、《纸上风云》、《爆竹翻脸》、《历史的骚味》、《浮生纪事》、《意象风景》、《失乐园》等7部诗集,以及《放逐诗学》、《空隙中的读者》(英文)、《语言与文学空间》、《诗的瞬间狂喜》、《诗心与诗学》《台湾现代诗美学》等诗学专著,在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上都有杰出的表现,被誉为台湾诗坛“承先启后”的诗人,也是台湾中生代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大陆读者对简政珍也不陌生,199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曾出版了他的《诗国光影》(诗作诗论精选),受到好评。2008年10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他的诗选集《当闹钟与梦约会》,收诗147首,分为6辑:出入人生、现实的身影、意象的姿容、有情众生、所谓情诗、长诗的行脚,囊括了简氏诗作的大部分精华。本文以有限的篇幅,仅对这本诗集作一个管中窥豹式的探讨,以期为台湾中生代诗学研究提供一份个案分析。
简政珍似乎与台湾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现代派诗歌走着一条不同道路。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逼视生命的存在,在诗作中贯注着深厚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他写身体佝偻的《跌爬的人》,写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的《雏妓》,写落魄醉酒的《老兵》,描绘出弱势群体的众生相。甚至关在笼子中待杀的《公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也进入诗人同情的视野。如果说简政珍早期的诗作还比较写实的话,那末他近年来的诗作更多地由具象进入抽象,采用隐喻的手法来处理现实题材和社会问题。如他的《灾后》写台湾20世纪末的大地震,“东西还在寻找定位/马路饥饿地张开大口/一部挂在斜坡上的轿车没有人认养”,即是对震后余生和残破景象的隐喻,给人更多想象的空间。再请看《世纪末》中的诗句:
世纪末破碎的臭氧层中
能否在沙上找到足迹
为消失的海鸟招魂
讯号翻过层层的海域
追踪一只身上布满伤痕的鲸鱼
这里“破碎的臭氧层”、“消失的海鸟”和“身上布满伤痕的鲸鱼”,都是由具象进入抽象的双重隐喻,惊心地展现了世纪末地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动物种类减少甚至灭绝,人类面临一系列生存困境的图景。诚如简政珍所说:“没有现实就没有诗人,但写诗又要从现实中跳脱,诗因此是现实和超现实间的辩证。”1而隐喻,可以说是架设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桥梁。
《当闹钟与梦约会》是简政珍颇受争议的一首诗。有人说是写爱情的,有人说是写理想的,有人说是写现实的,有人说是超现实的,不一而足。“闹钟”这个意象具有计时、定时、守时、叫醒等多重功闹钟和梦约会,本身就是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辩证。诗中的“你”,可以理解为意中的“女性”,也可以理解为所追寻的“理想”。诗的第一节,大约表现一种失恋的情绪或理想的破灭,“闹钟的呼唤已瘖哑”。第二节写驾车旅行,可以理解为对“女性”或“理想”的继续追寻,读者可从“这时你听到/梦中闹钟的呼唤吗”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第三节开头:“当我在梦中将心情留给童年/河川倒溯至高山的雪原”,诗人梦回童年正如河流倒溯至高山雪原的起源一样,是为了追寻生命的原点,探寻生存的本真。诗中接着出现了5个意象叠加:
一只飞鹰在天边寻找归宿
一头牦牛在湖边孤零自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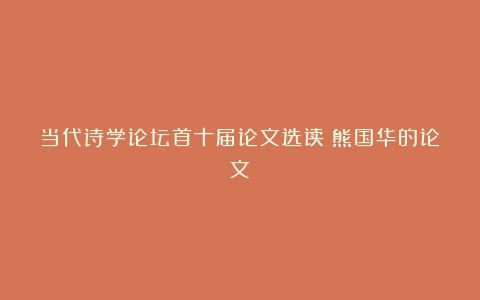
一列火车开进朦胧的战火
一张虎皮进占一个华丽的客厅
一个老钟在沾染血迹的五斗柜上
滴答
这种类似后现代拼贴手法构成的排比诗句,可以理解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丧失、内心世界的孤独和战争的威胁,华丽客厅中的虎皮意味着对动物的杀戮和掠夺,用来储存财物的五斗柜却沾染了血迹,滴答的老钟是这种灾难的见证(同时又与诗的开头相呼应)。这一系列叠加的意象,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实际上可视为物质文明表面繁华所掩盖的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层隐喻。这首诗不是结构的,而是解构的;不是逻辑的,而是反逻辑的;既是写爱情的,也是写理想的;既是现实的,也是超现实的。诗人打破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梦幻、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界限,进入一种自由自在“心无滞碍”的写作状态,充分发挥了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为读者提供了多种想象和思考的向度。“人说,歧义是一种美德/我躲在歧义里/制造歧义”(《语言》)。简政珍把《当闹钟与梦约会》当作一部诗集的书名,可见他对这首诗的重视程度,或许是他在这首诗里实现了他“制造歧义(多义)”和隐喻的美学理想吧。
简政珍是比较典型的学者型诗人,而且具有极强的现代感和生命感。他的诗中大量出现现代生活的名词、意象和场景,诸如电线、轮胎、荧光幕、雅虎、网络、SARS、飞机、报纸、电视、广告、高楼、国际电话、股市、超市、政客、选举,以及台风、地震、洪水、酸雨等台湾常见的自然意象,广泛地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他尤其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命运,甚至推及动物和植物的命运。简政珍认为:“生命是一项命定的旅程,只有先觉悟到这种命运,人才能展现及逼视存有。” 2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在于他对生命有超乎常人的感悟,以及对生存环境的焦虑和恐惧。在《生日》中,我们随着切蛋糕的“刀起刀落”,似乎感受到人生的历程:“这一块赤脚的日子给你/那一块羞涩的时光给他/这一块不知酸甜苦辣的/留给母亲/那一块,爆竹碎裂后的积累/留给妻子/剩下这一块残缺的我/给自己”。生命的残缺,在于人生的各种不美满和骨肉之间的生离死别。在《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现代“游子吟”的动人情景:“针在纤维的缝隙里游走/我在跳动的烛光中/探寻母亲的心事”,经过母子分离前最难熬的不眠之夜后,“我们一齐等待/台风过后的晨光/父亲在墙上的遗照/还未收回笑容”。读到这里,只要尚有一点人性的心灵,又怎能不被感动!
对生命最深刻的感受,恐怕莫过于面对和逼视死亡,只有感受到死,才能更好地感受到生。生死是一个轮回,人类就在这个轮回中不断进化和繁衍。简政珍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透过现象对生命的本质作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并对生存的荒谬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请看他的《市场》:
凡能走动的
都在刀口的寒光下
看到灵魂的远景
凡和躯体有关的
都能引起唇舌的论争
只有未能羽化登仙的羽毛
是唯一
不必细究的归宿
凡能走动的
都把分尸后的残骸
带回去做一道
在浪漫烛光下
使灵魂提升的
菜
诗中第一个“凡能走动的”,可以理解为市场被宰杀的鸡鸭猪狗等动物,渴望死后灵魂升天。第二个“凡能走动的”可以理解为宰杀者或者购物者,把动物“分尸后的残骸”带回家做菜,在得到物质享受的同时,还心安理得的得到“灵魂提升”的精神享受。诗人充分利用了诗歌语言的歧义和隐喻。不仅如此,两个“凡能走动的”似乎又具有一种互文关系,即第一个“凡能走动的”也可以指人,第二个“凡能走动的”也可以指动物。“市场”可以是宰杀动物的交易场所,也可以理解成人类相互残杀的场所。被宰杀者自以为脱离了苦海,灵魂升天;宰杀者总能找到任意宰杀的理由,自以为是在替天行道、伸张正义,两者都以谎言自欺自慰,丧失了生命的本真和智慧。诗人以此揭示出生存的荒谬与残酷,直指人性的底蕴。
基于对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深刻体验,诗人发出了“我们有如烛火/在痛中饮尽一生”(《我们有如烛火》)的呼喊,暗示人们:人生是痛苦的,如同蜡烛不断燃烧成泪,人的一生是饮泪的一生。而最后“当日历在火中燃烧/年复一年/我们只是一支已无形体的/烛心”,一切归于空无,归于虚幻。诗人不仅深刻揭示了生命的悲剧性存在,也使我们想起佛教的“苦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和印象中,简政珍是把西方存在主义与东方佛教思想融会贯通得最好的诗人之一。他比台湾早期超现实的现代派诗歌更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问题,诗歌在他手里是一种“现实的隐喻”;他又比台湾七十年代兴起的明朗写实的乡土诗,多了几分思想深度和开阔的视野,诗歌在他手里是一种“生命的哲思”。这两者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技巧,或许是简政珍以及台湾中生代诗人的一种美学追求吧。
2007年2月28日于广州
馆主简介
傅天虹,1947年生于南京。现任北师大珠海校区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顾问,历任北师大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文学院教授。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委副主任、澳门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捐赠人等。
傅天虹襁褓中父母去了台湾,70年代中期后才和台湾家人联系上,其时作品频频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雨花》,以及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等报刊,1981年1月美国《世界日报》副刊曾以显著篇幅发表他组诗《南京杂咏》。他蝉联二届雨花文学奖、获台湾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等,当时北亰《嘹望》《人物》等杂志,台北《文讯》等杂志,曾以专文或专辑推介过他。 怀着强烈的沟通意识,在大陆业已成名的傅天虹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乡叔何家骅(时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先生协助下,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促成台湾老诗人组团北京的破冰之旅。傅天虹1984年创办金陵书社(诗学会前身),1985年协助蓝海文创办《世界中国诗刊》,1987年在挚友路羽、洛夫、犁青、黄德伟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0年正式注册当代诗学会。1991年他客居澳门,潜心编著《大中华新诗辞典》(全套15册),《世界华文诗库》(多册),在工商阴影下为诗坛抢救了一大批原始资料和原生态的诗集。1999年在任仲夷、梁披云、贺敬之等老前辈扶持下,他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建香港、澳门两总部;设立“龙文化金奖”,至今已颁发3届;主编《国际炎黄文化名人大辞典》《国际炎黄文化名人作品经典》,以及《千禧献辞》手迹版等。新世纪在挚友屠岸、张默、犁青支持下,他以诗存史,正本清源,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诗丛系列,历时25年,至今推出50套共1068部诗集。2007年,他任教珠海北师大,提出以人为本的“汉语新诗”概念,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同时,在挚友屠岸、谢冕、吴思敬、朱寿桐等和院长张明远支持下,倡议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论坛在谢冕、吴思敬主持下,至今已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等多地举办了十二届。
傅天虹自幼酷爱写诗,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40余部,发表论文多篇,编著达数千万字。生平入编《中国大百料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等权威文本,诗作入编最新商务印书馆版《大学语文》等教材。半个多世纪来他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出版家、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校时主讲“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课程,主持“汉语新诗教授工作坊”等实践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