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建馆小记
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筹建於2006年,原址东莞常平镇紫荆花园,本馆集收藏、展示、研究、出版为一体。二十年来历经坎坷,幸而得力於当代诗学会群英们鼎力支撑,更有珠海北师大华文所和澳门大学有关院系一路扶持,始得坚持至今。现包括“路羽书房”“惠兰书苑”二个有生部分,共藏有各类稿存、信札、手迹、签名书、书画、墨宝近二万件。
为更接地气,今年3月初,应好友建议,傅天虹在360个人图书馆官网上,注册了“傅天虹的汉诗馆”,试发几篇后很满意,故决定从2025年4月1日起正式启动,将陆续整理上传傅天虹六十多年来珍藏的史料和墨迹,将各种史实公诸于众,方便大家随时上网查阅所需,以利汉语新诗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请给予关注、推荐。另外,傅天虹藏品也可酌情转让给海内外有迫切需求的机构或个人,作馆藏或研究之用,合作也行,有意者可加傅天虹微信联系。 2025.4.1
当代诗学论坛於2007年3月,创立于北师大珠海分校,至2019年已走过整整十二个年头。先后在珠海、北京、台北、澳门、香港等地成功召开十届。现选辑一百位学者的一百篇论文,以表纪念。
2007年3月,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首届当代诗学论坛)在傅天虹任教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成功举办,此为大会会场
会上,傅天虹倡议并参与发起二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12位发起人聚会留影:左起,朱寿桐、张明远、吴思敬(召集人)、简政珍、吕进、张诗剑、傅天虹(秘书长)、犁青、高戈、、黄德伟、谢冕(召集人)、屠岸(召集人)、盼耕。
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发起人聚会时签名留念:屠岸(召集人)、谢冕(召集人)、傅天虹(秘书长)、高戈、张明远、黄德伟、犁青、张诗剑、吕进、简政珍、吴思敬(召集人)、盼耕、朱寿桐签名志庆。
“追求感觉的智慧”
——简论简政珍的诗论和诗作
古远清 | 文
古远清(1941年8月- ),男,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市文联第六、七、八届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博导评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庭外’审判’余秋雨》《几度飘零》等。
通常讲的评论家有三种层次:一是紧紧依附创作,追踪作家的前进步伐,缺乏自主意识,更不用说超前性;二是善于从作品中看到底层的意蕴,从中发挥自己独到的见解;三是独立于任何作品之外,从众多的作品中思考文学的本质及有关文学的美学问题。这种思维横跨时空的评论家,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家。《诗的瞬间狂喜》,便是简政珍迈向思辨型学者所走出的第一步。
《诗的瞬间狂喜》标志着简政珍的爆发期的来临。先前的拘谨与青涩逐渐逝去,代之而来的是严密的思索和有着延伸意义的超越性。这种带有海阔天空的超越,使他不再去重复先人讲过多次的“诗是一种最精炼的语言艺术”、“诗变形地反映生活”这类话,而改换不同视角,在不同场合提出“诗是一场纸上风云”、“诗是最危险的持有物”、“诗是诗人和语言的对话”、“诗是感觉的智慧”、“诗是诗人意识对客体世界的投射”以及“写诗是一种独白中吐露时代的声音”……这些思考,均带有简政珍的艺术个性。以“纸上风云”这个比喻来说,诗人不能躲进象牙之塔,必须面对现实却无能为力去改变现实。诗虽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把“纸上风云”当作现实的风暴就过分夸大了诗的功能。这并不意味着简政珍完全否认诗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用。所谓“诗是最危险的持有物”,讲的是诗重整现实,尤其是想担负摧毁现实既有世界的功能时,必然会受到思想僵化保守的政治家的干预。这种干预“不是把诗人视为社会’进化’的祭品,就是刻意淡化诗的影响力。”1为了不当“祭品”,诗人应讲究斗争策略,在干预生活时要写得委婉曲折,而不宜大声疾呼。由于是带着枷锁跳舞,说起话来未免欲言又止,因而使人感到似懂非懂。尤其是那些拒绝迎合现实的趣味和大众的口味、思辨性非常强的诗,更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诗集必然卖不出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简政珍认为:“在这个时代当一个严肃的诗人面临自己诗集畅销时,都应该认真考虑到自杀。在这个时代,诗集畅销是严肃诗人最感到羞愧的事。”2简政珍还把诗集的畅销看作是奇耻大辱,这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应注意的是,作者这段话是指当时特定时空的特有现象,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众多畅销书差不多都是迎合小市民的庸俗产物。至于在法国,艰深的Dessida的解构理论一度还成为畅销书,不免对法国人肃然起敬。再看台湾当代诗坛,诗集难得畅销,但少数畅销的诗集,几乎都是“情绪散文”之作。好的诗不一定要艰涩,但面对麦当劳的庸俗时代和选秀的劣质社会,诗集一旦畅销,严肃的诗人的确应反过来考虑自己的诗集是否有媚俗的倾向。
如果说,对意象的着重与经营是简政珍诗法的核心,那么,追求“感觉的智慧”,则是简政珍诗论的特色。他的多处论述受到海德格尔及胡塞尔的影响,讲求论诗和写诗一样,要意味隽永,能给读者精致的品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论“也是声音后的沉默,因为它是一种独白”。
对诗人来说,诗集的问世等于缔造了一个艺术世界;对评论家来说,评论集的出版应该意味着另一个更完整、更富于思想性的艺术世界的诞生。人们高兴地看到,在这个政客说谎、话语贬值的世纪末,简政珍先是拥有了“放逐诗学”这么一个独立完整的评论天地,以后以“濒死的心情”制作了一个“语言与文学空间”,还陪同读者进入缪思所管辖的神秘住所,邂逅瞬间的狂喜。他始终反对文学是一种游戏的观点,严肃地对待创作和评论,“希望自己对文学的思考是透过语言对人生真诚的感受,而且不是为了演练一套游戏法则或理论”3。这点应充分肯定。以《放逐诗学》为例,“放逐”是指作者由于种种原因离乡背井出走,转化为对乌托邦的寻求,而这种放逐心境伴随着文化身份的确立以及浪迹天涯所带来的孤独感,便成了创作的重要题材。作者认为,书写故土再现家园,使放逐处境变成一刹那的跳脱,虽然放逐文学无法解决放逐者的漂泊处境,但是成功地书写放逐就是一个反放逐者。在此书中,作者通过风格多变的余光中、及善于让诗的意符浮动的叶维廉等五位作家,针对他们的放逐意识进行条分缕析的诠释,试图为台湾的当代文学建构出具有美学意义的放逐诗学。
简政珍认为:“诗是诗人与现实的辩证,是现实与人生’哲学化’的结果。”这里讲的哲学,不是人生的意象化,而是经由形象思维后的提升。基于这种观点,作者的《放逐诗学》不是将“语言事件演化为现实事件”,以诗例印证时代的步伐,把诗学研究弄成历史学、社会学的翻版,而是让美学与历史对话,以“物象的观照”以及“现实的观照”去书写1950至1970年代的台湾诗史,在关注后现代风景及长诗创作时,不以预设的立场为诗人定位,不以标签作为现代诗的图腾,而注重那些“天然去雕饰”的作品,这便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既展现出“史”的磅礴,又游刃有余地保持着研究与批评的态势。
在新世纪的台湾新诗研究历程中,简政珍的力作显出了一种先导性,其后来出版的《台湾现代诗美学》,超越了自己,也超越别人,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学院派诗人的简政珍,不仅在现代诗的理论研讨上做出成绩,而且通过浓缩的意象、偏向知性的语意结构和淡中见奇的诗,说明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亚于抽象思维。
长期在书斋里讨生活的简政珍,勇于面对现实,对荒谬的社会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和愤慨。这改变了过去学院作家创作视野受局限的状况,并将自己与中产阶级的“自足感”和“妥协感”划清了界限。如有“新史诗”之称的《历史的骚味》,以中国近代史情结和当代政治社会现状作背景,借刘邦的豪爽笑声、尿床的皇帝乃至对炖烂狗肉止咳嗽的老朽的国大代表的嘲讽,对现实中存在的诸如农药残毒、生态环境污染、股市长红、行贿选举、万年法统等丑恶现象一一 作了讽刺和批判。
长诗《历史的骚味》固然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本质的深层思考,简政珍的短诗同样表现了作者对当前现实的反思和不留情面的批评。写得过于直露的《选举》,作者对行贿现象的深恶痛绝之情仍表现得充分和动人。《大学校长》同样写得尖锐、泼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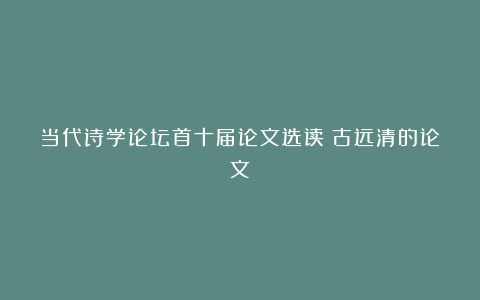
据说,他是太阳旗下
残余的星子
只在上级来访时发亮
每天在行政大楼的顶端
研究如何以农药培养人事
以南京大屠杀的魄力
去除人文、艺术等杂草
在“你农我农”的世界里
看不见农民缩水的身影
只看到
官员胸前的红花
至于诗
他说:当然没有用
因为不能创造
欧罗巴
这里写的大学校长,只会对上级负责,而对下级尤其是广大教师的科研成果,不但谈不上尊重,反而只会粗暴地扼杀。“以农药培养人事”,这种做法离奇,但奇而不怪。校长拿着上级指示,见不合口味者便打击之、消灭之,这种做法与用“农药”杀人无任何不同。本来,简政珍的诗历来以意象经营取胜,但这首诗主要以警句吸引读者。其中写的“红花”可以使人联想到是由无数优秀人才的血液所染红。我们从“红花”中闻到的不是香味,而是从历史垃圾中发出的历史骚味、腥味。在我们看来,简政珍所写的这类讽刺诗,当然不会“没有用”。它虽然不能创造著名的养猪饲料“欧罗巴”,但能打扫政治垃圾,能将学阀式的学校行政长官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简政珍的诗与流行的政治诗的不同,在于反映现实却不过于贴近现实,沉思现实时不把功利放在首位。在他的诗行中,有着比功利更深层的哲学意识。简政珍的作品与干着喉咙叫喊的抗议诗或控诉诗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他的诗没有单一的主题和明朗的题旨。其作品意象不算复杂,但里面有多层的意蕴。歧义迭出的《市场》,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强调诗的多义性的简政珍,没有把晦涩当作追求的最高目标,也不为迎合大众故意写些大白话。他喜欢在平淡中见深致,在平易中见含蕴,使自己的诗作和散文明显地划清了界限。在诗的语调上,他不喜欢“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语速,而偏爱“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节奏。他坚信“诗的本质是沉默的,而不是人刻意制造的声音”。既客观冷静又包含了是非感,这正是他的诗作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
馆主简介
傅天虹,1947年生于南京。现任北师大珠海校区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顾问,历任北师大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文学院教授。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委副主任、澳门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捐赠人等。
傅天虹襁褓中父母去了台湾,70年代中期后才和台湾家人联系上,其时作品频频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雨花》,以及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等报刊,1981年1月美国《世界日报》副刊曾以显著篇幅发表他组诗《南京杂咏》。他蝉联二届雨花文学奖、获台湾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等,当时北亰《嘹望》《人物》等杂志,台北《文讯》等杂志,曾以专文或专辑推介过他。 怀着强烈的沟通意识,在大陆业已成名的傅天虹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乡叔何家骅(时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先生协助下,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促成台湾老诗人组团北京的破冰之旅。傅天虹1984年创办金陵书社(诗学会前身),1985年协助蓝海文创办《世界中国诗刊》,1987年在挚友路羽、洛夫、犁青、黄德伟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0年正式注册当代诗学会。1991年他客居澳门,潜心编著《大中华新诗辞典》(全套15册),《世界华文诗库》(多册),在工商阴影下为诗坛抢救了一大批原始资料和原生态的诗集。1999年在任仲夷、梁披云、贺敬之等老前辈扶持下,他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建香港、澳门两总部;设立“龙文化金奖”,至今已颁发3届;主编《国际炎黄文化名人大辞典》《国际炎黄文化名人作品经典》,以及《千禧献辞》手迹版等。新世纪在挚友屠岸、张默、犁青支持下,他以诗存史,正本清源,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诗丛系列,历时25年,至今推出50套共1068部诗集。2007年,他任教珠海北师大,提出以人为本的“汉语新诗”概念,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同时,在挚友屠岸、谢冕、吴思敬、朱寿桐等和院长张明远支持下,倡议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论坛在谢冕、吴思敬主持下,至今已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等多地举办了十二届。
傅天虹自幼酷爱写诗,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40余部,发表论文多篇,编著达数千万字。生平入编《中国大百料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等权威文本,诗作入编最新商务印书馆版《大学语文》等教材。半个多世纪来他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出版家、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校时主讲“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课程,主持“汉语新诗教授工作坊”等实践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