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是书院制和私塾制,还不存在班级规模大小的问题。班级规模大小问题是随着现代学制的实施而发生的。1902年“壬寅学制”是现代学制的预演,《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高等学堂章程》均规定学生数“每班至多不得过四十人”。其后可能发现新式学堂之初,大学生源极为难得,不嫌其多,只嫌其不足,所以到正式发布“癸卯学制”时,便没有了这方面的限定。事实上最初大学的班级规模都是很小的,譬如1917年《北京大学日刊》公布学生统计数,文科预科为三年级10人,二年级16人,一年级122人,总计148人。又如1925年,钱基博去清华大学任教大学部甲戊两组国文课,每星期8小时,每组学生只有16人。但后来大学渐渐上了规模,学生多起来,相较于其他科目,国文课教学特别费时费力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所以到了30年代的金陵大学,就规定大一国文课每班的人数不得超过30人。到了40年代,燕京大学更规定大一国文课每班的学生不能多于20人。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云南大学文学院的姜亮夫院长就说:“国文教师,终日忙着改文,这一期才完,下一期又到,结果是工作过重,只有从速度方面设法,于是圈过点过,便算完事,教者是虚应故事,学者是毫无进益,等于白靡国币,是种极可怕的现象”。黎锦熙也说:“记得二十七年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曾经颇紧张地做过一番工作,集合全校并师院各系国文教员每周开一次谈话会议定一年级统一的教材,议定指导写作办法三种(作法统整有效办法,作文批改符号及指导办法,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写作办法),认真实施,一学期后,渐难支持,其原因就在教员的负担太重,比较担任二年级以上的分系功课要多费数倍的时间”。
所以当年一些认真的学校,都非常重视班级规模问题。1938年秋,西南联大招的新生特别多,有640人,都要开“大一国文”课,于是中文系紧急成立了21个教学组,其中读本7组,由罗庸、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王力、余冠英、陈梦家分别任教,作文14组,任课的教师有浦江清、朱自清、许维遹、李嘉言、吴晓铃、余冠英、陶光等,堪称一时之盛。
这在今天恐怕令人难以置信,600多名学生,今天有的学校大学语文教师可能一两人就全包了。所以钱学森问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吧?
当年即使个别不太重视大一国文课的学校,班级人数也都不是很大。1939年叶圣陶去武汉大学任教,中文系主任故意刁难他,让他教3个班的大一国文课,这让叶圣陶非常气愤——3个班的学生是多少呢?是88名。
抗战胜利后,高等教育逐渐恢复,1946年度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数增至185校,学生总数129,336人;1947年专科以上学校增至207校,学生数增至155,036人。于是1948年南京教育部修订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提出“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应竭力设法开设大教室(文理法三学院最好每系有一适用之大教室),尽量容纳应修学生合班讲授,不得以院系为单位,分别设班,以求全院全校互相沟通,但语文科目之每班人数,不得超过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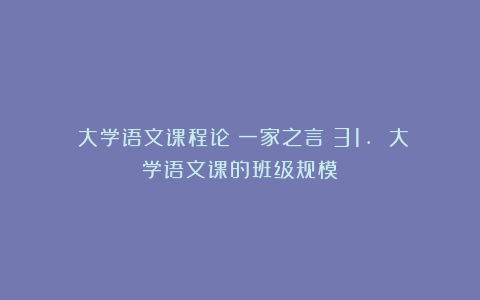
尽管如此,语文界同人仍然觉得这个数字过高,所以到了1948年,徐中玉为大一国文教师打抱不平说:“国文课又确实辛苦,因为有许多文卷,许多学校又不肯为文卷之多就减少教授授课的钟点。……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应该而且也可以改善。国文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三班九小时七十五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勉强还可以来得及。每班人数如果超出三十人,便当减少授课时数为两班六小时,……各大学哪里没有多少冗员?少用几个职员,就可以多聘几位教授了,在国文功课上来省钱,不但太笨,简直是罪恶。”
再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后的情况,当时百废待兴,大学教师队伍也尚未完全恢复,所以这门课一开始就是大班上课。最早恢复大学语文课的南京大学,据侯镜昶说:“在刚开设此课的第一学期,由于教研室师资尚未调齐,我们采用大班形式上课。当时文科各系学生二百五十人合为一班,理科学生(包括专科班)二千人,分为两班在大礼堂上课”。
这本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后来却被延续下来,虽然不再有千人的大班,但上百人的课堂却是司空见惯,几百人的课堂也并非偶见,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教育报》报道:
当学生身处巨大的阶梯教室,老师连后排学生的脸都看不清时,语文还怎么传情达意?当一学期的大学语文课匆匆而过,老师用跟中学类似的方式一张考卷定分数,语文又怎样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训练学生思维?与之相对的是大学里的英文教育,课时远远多于大学语文,而且大多是小班教学,学生的学习热情就大得多。
于是早在60年前就曾呼吁大学国文课必须小班化的徐中玉先生也再次发出呼声:“’大学语文’宜于小班教学,否则教师很难于做到关心每一个同学,也不利于学生进行讨论。较小班级的教学效果,会比百人以上的大班灌输好得多。”
目前世界高校普遍废除了上大课的方式而趋向专而小,分小班上课。哈佛大学规定一个课堂学生不得超过14人,普林斯顿大学规定一个课堂学生数不得超过12人,伯克利分校规定一个课堂也不得超过14人,明尼苏达大学母语教育课程的课堂平均学生数为22人。还有的学校甚至把这作为招生宣传的亮点,如斯坦福大学在广告中就特别说明,它70%左右的本科班级都在20个学生之下,这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师,教学质量更能得到保证。
而中国高校大学语文课的大班化现象无疑是与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的,究其原因,还是与这门课的定位不清有关,偶闻有学校领导说,大学语文要向“百家讲坛”学习——“百家讲坛”是什么性质呢?按易中天的说法,就是一锅老少咸宜的“萝卜汤”,15岁至60岁人群皆可听,然而也就是听听而已,节目组领导曾提议增加与听众互动环节,被易中天一口回绝,说“那还不乱套呀”。所以大学语文不是综艺类节目,只要教室够大,音响够好,讲得够好,多少学生都不怕,甚至越多才越有人气,这样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把大学语文当成了讲座课,当成了综艺节目,而放弃了本该有的母语高等教育定位。
由于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就发生两个结果,一是这门课没有实效,最终被取消;二是一些学校另起炉灶,譬如开设“沟通与写作”之类的课程,明确规定班级规模不超过15人——大学语文未能实现的小班化,换个名字做到了。
清华沟通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