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 关于“读”的调养
如何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养过来?温儒敏开的方子是读书,读书,大量地读书。这个方子在中小学恐怕不灵,只要还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可能大量地读书,只有进了大学,这才真正成为可能。第一,大学已经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又有很多可供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第二,大学图书馆有大量的藏书,有良好的读书环境。目前大学的这一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譬如入学头两周不上课,搞军训。笔者认为军训不应该影响读书,应该从入学第一天就开始读书,让学生知道大学是读书的地方,可以兼有别项活动,但是不能没有读书,读书改变气质,这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我们在学校教室里,常常可以在墙上发现这样一幅意味隽永的名言:“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读书变化气质。”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读书》中的一段名言,这段话与素质教育思想非常接近。人的学习是多层次的,大致说来,第一层是知识,它需要记忆和积累,主要就是读书;第二层是能力,它在对知识反复运用中形成;第三层才是素质,它是知识和能力长期实践、积累之后造就的一种人生态度。素质教育便是注重第三层又不偏废前两层的一种完整的教育思想。
譬如读史。记住了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和年号,这是知识;会用这些知识分析历史,这是能力;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不为一时一事的现象所迷惑,始终对人生抱有乐观信心,这才是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所以说“史鉴使人明智”。
譬如读诗。会读会背几首诗,这是知识;学会做诗,便是能力;学做诗先学做人,使诗如其人,使人生如诗,机智灵敏,潇洒脱俗,这就是素质。所以说“诗歌使人巧慧”。
譬如学习数学。记住一些公式,这是知识;会用这些公式具体运算,便是能力;于运算中养成精细的思维方式(数理逻辑思维),使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于各门功课学习,乃至贯穿整个人生,这才是学习数学的最大益处。
譬如学习博物。博物泛指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是培根时代人们热衷的科目。认识一些物种,懂得它们的分类,这是知识;能够利用、保护这些物类,这是能力;观世界之博大,察万物之精彩,乃悟人类之地位与责任,如此焉得不深沉?
譬如学习伦理。伦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高尚品德,所以这是一门直接作用于人的素质的学问。学了一些伦理知识而不贯彻于行动,是最轻薄而不庄重的。西方人说中国有伦理学而无哲学,排除自大的偏见,其实倒是赞扬我国先贤们对自己的理论都能身体力行,他们都是一些庄重的人。
培根所举各门学问,唯最后“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一句,只着眼于能力,值得进一步讨论。其实逻辑与修辞同样改变人的素质:逻辑要人做得对,修辞要人做得好,假如你能让自己的人生既合乎逻辑,又注意修饰,必能培养一种良好的气质。所以此句若改为“逻辑使人认真,修辞使人精采”似更为妥贴。
最后稍嫌不足的是这段话漏掉了“语文”,今试补上:语文教人语言文字听说读写,为史鉴、诗歌、数学、博物、伦理、逻辑和修辞等学科提供学习工具。语文学习也有知识、能力、素养三个层次:认识几千个字,读了几百篇文,这是知识;能用这些知识做工具,学好史鉴等各门功课,这是能力;在各门功课的学习中,形成一种语文素养,透出一种读书人的气质,这才是读书的最高目的。
那么什么是读书人的气质呢?首先当然是爱读书,嗜书如命,语言文字成了他的一种生活状态,形成一种书卷气,或者叫做诗意的生存。曹文轩曾讨论过这种读书人的气质,他说:
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这从气质上便可看出。读书人的气质是读书人的气质,这气质是由连绵不断的阅读潜移默化养就的。有些人,就造物主创造了他们这些毛坯而言,是毫无魅力的,甚至是丑的。然而,读书生涯居然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依然还是从前的身材与面孔,却有了一种比身材、面孔贵重得多的叫“气质”的东西。我认识的一些先生,当他们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叙事或论理,当他们站在讲台上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地讲述他们的发现,当他们在餐桌上很随意地诙谐了一下,你就会觉得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使你对你眼前的形象过目不忘,永耸心中。有时我会恶想:如果这些先生不是读书人又将如何?我且不说他们的内心因精神缺失会陷平庸与俗气,就说其表,大概也是很难让人恭维的。此时,我就会惊叹读书的后天大力,它居然能将一个外表平平甚至偏下的人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使你觉得他们的奕奕风范,好不让人仰慕。此时,你就会真正领略“书卷气”的迷人之处。
一学期或一年的大学语文课当然达不到这样的目标,但是我们要把这样的目标告诉学生,让他们在大学四年里,乃至今后的一生中都追求这样的人生境界。这一单元的课文,就可以选择《世说新语》、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谈美》,以及《西方名著入门》中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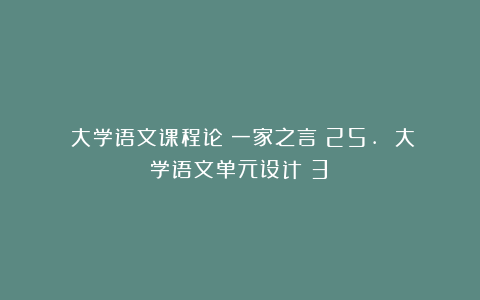
再说导读方面,第一应该是开书目。大学虽然有读书的时间,图书馆也有大量的藏书,但对于刚从应试教育走出来的学生来说,未免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眼下和长期的书目。大学生据说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必读书目100种,中文专业也有类似推荐书目,但是大学语文还缺少这样的书目,原因恐怕还是和语文特殊的学科性质有关。其他专业都有自己的内容,所以比较好开书目,大学语文比较特殊,它以其他学科的内容为内容,但那只是凭借,不能随便开一堆其他学科的书目凑数,必须要有符合语文自己目的的书目。譬如高教司推荐中文专业书目的前面几种是语言学方面的,有赵元任的《语言问题》、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等,大学语文应该相对减轻专业难度,选一些更适合进行阅读训练的书,如尘元(陈原)的《在语词的密林里》和《重返语词的密林》这样的书。其他专业的书也是如此,要选择一些语言文字通俗优美的科普读物。大学语文要研究一下,搞一份书单,首先推荐10种共同书目,争取在大学一年级时阅读;然后再结合各专业学习需要推荐100种书目,以供各专业学生大学四年继续学习语文乃至终身阅读所用。
第二是调品味。开书目主要告诉学生应该读哪些书,调品味则要告诉学生不应该读哪些书。如今读书环境杂乱,好书坏书混杂,温儒敏说连北大中文系学生都不读书,或者只读些《鬼吹灯》《盗墓笔记》,以及“40岁以前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这样的书。这种情况可能有普遍性,有人统计中美大学生阅读书目的差异,中美著名大学排名靠前的阅读书目如下:
中国5种:《平凡的世界》《三体》《盗墓笔记》《天龙八部》《明朝那些事儿》。
美国10种:《理想国》《利维坦》《君主论》《文明的冲突》《风格的要素》《伦理学》《科学革命的结构》《论美国的民主》《共产党宣言》《政治学》。
阅读品味和难度高下立判,必须引起重视。上世纪40年代朱光潜写过一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讲了10种低俗趣味的现象,可以列为本单元课文,或者今天已有更新的此类文章,可以再找一找。
第三是教给读书的方法。应试教育搞坏了学生的胃口,包括读书的胃口。读书本来是很开胃的事情,但是被应试教育搞坏了,那么今天大学生应该如何读书?目前大学语文教学中流行的那种解剖刀式过度阐释的方法,同样会搞坏学生胃口,所以笔者设想回归阅读的初衷,只设置三项最低目标:第一,读一本书之前,先看一下内容提要,把握主要意思。这和应试教育的背标准答案,把它作为终结性目标不一样,这是要作为阅读的起点,带着主旨思想去读,不要把书读偏了。譬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经典名著之一,俄国文学名著。女主人公安娜是个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贵族妇女,她不满封建婚姻,憎恨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丈夫卡列宁,不顾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攻击,自由大胆地爱上了青年军官弗龙斯基,后来终被遗弃,她悲痛欲绝,卧轨自杀。
知道这个就够了,不要求学生自己去概括,搞什么“研究性学习”——书还没读几本,研究什么?有人说“独立思考的前提是你读过上百本经典”,笔者很赞成这个说法。所以关于“内容提要”,重要的不是要你概括,而是要看一看(很多学生是不看的),作为读书纲要,不要把《安娜·卡列尼娜》读成婚外恋什么的艳情小说。
第二,读完后要能说出书中的一些细节(不是全部),譬如纳博科夫为学生出的《包法利夫人》考试题就有:爱玛读过什么书?最少举出四部作品及其作者;爱玛喜欢她所处的山间湖泊是有一条孤零零的轻舟,还是没有轻舟?描述爱玛的眼睛,双手,阳伞,发型,衣着以及鞋等等。目的在于提示学生,不要光看故事情节,也要注意作品细节,尤其是语言文字方面的细节。
读一本书,假如既能知道基本主旨,又能说出若干细节,有这两项差不多也就够了,假如还有余力,那么第三,还可以挑选一些段落熟读或背诵,譬如我们都知道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这一段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好的书里总能找到这样一些精彩的段落,大学生正是人生的黄金阶段,精力旺盛,应该多背诵一些东西,你不让他们背诵,他们自己也会找东西背诵,譬如早些年大学里曾流行的《大话西游》,下面一段话当时的大学生几乎都会背诵:“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所以不让学生背诵一些更加正能量的东西,实在是浪费了他们的脑力和精力。
最后再捎带说一下朗读,朗读是一种介于“读”与“说”之间的训练。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诵读、朗读是“读”的重要方式。今天假如我们只是为了获取信息,那么一般的阅读(用眼看)也就可以了,但是假如是语言学习,而语言本是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那么朗读、诵读就仍是重要方式。当年辅仁大学陈垣校长重视国文教育,要求学生熟读背诵,说:“令学生读之烂熟,涵泳玩索(每一二句),习惯自然,则出口成章,可免翻译之苦。……学本国文贵能使言文一致,今以《论语》《孟子》为言文一致之标准,选出数十章,熟读如流,不啻若自其口出,则出笔自易。”
朗读还是一种更为高级的阅读与交流。有一年国际上召开海明威小说研讨会,受到邀请的与会专家不是要准备一篇论文,而是要交一篇你能够朗读的海明威小说的篇名,到时候,大会就安排你上台朗读。几天会议下来,没有人是在做学术报告的,大家都是轮流去朗读自己准备的海明威小说,因为每个专家对海明威的理解存有差异,再加上海明威的小说素以冰山理论而著称,潜台词要比直接形之于文字的丰富得多,所以,听每一位专家的朗读,其对声音、节奏、感情的独特处理,确实要比听一篇单纯的学术报告生动得多、丰富得多。
这一单元的课文选篇,还可考虑梁文道的《我读》,这是一本比较大众的讲读书的书,还有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系列节目相配合。还可选[美]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以及《西方名著入门》的导言“如何阅读及为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