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知道“远征军”这个词汇,是在1978年春天,那年我还不满18岁。当年的莫高窟很古怪,说是文物研究所,但却有很多庄稼地,还有一个农场,里面羊圈、猪圈、牛棚、粮草库等农业生产设施一应俱全,跟我插队时的生产队不相上下。务农的人都是本所的职工,那时每人每年都必须轮流干一个月农活,而且每个周末还要干一天农活。我刚到莫高窟的第二天就乱窜到这个场院,我看到一位戴眼镜的长者提着猪食桶卖力地喂猪,我跟他打招呼,他只是和善地点了一下头便继续他的劳作。事后我向一位前辈打问那人是什么人?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他是个右派,还是远征军“。我问远征军是啥?他说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右派、国民党、反动军队这些词汇我耳熟能详,那都是阶级敌人,从小就知道了,但”远征军“对我来说却非常陌生,因为我们的课本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从那以后”远征军“便成了我的一个疑问,直到84年的一天,我竟然意外地从另一位在莫高窟打临工的垫圈老农身上得到了答案,而且就在这一天,我似乎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 本文自2004年在网易论坛、新浪博客等网站多次发表;于2013年在《当代敦煌》发表;于2016年在《大匠之道》一书发表。
雕塑/文:杜永卫
张有宁老人雕像(铸铜)
偶然看到一组照片 — 《最后的远征军老兵》,几位年迈沧桑的面孔,像粗粝的树皮让我震撼!我想起很早以前,曾经创作过一位和他们一样的老人。由于年长日久,这件头像放在了哪里,我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在助手的配合下,我在仓库里翻腾了一上午,终于找出了这件尘封多年的作品。清理掉上面厚厚的尘土,重新做上颜色,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依然如新,而那一年的那一天,也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那一天,我知道了很多我那个年龄段的人不知道的事情;那一天,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道理……
杜永卫雕塑工作室库房
那一天在1984年,两个同事的孩子打算报考雕塑专业,请我教他们学做头像。当时我也不过刚从美院回到莫高窟,也正是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
学做头像,最好的方法就是写生,初学写生通常是选一个老人做模特,因为老人骨骼突显,容易把握和认识造型。当时,在单位找一个闲着的老人还真不太容易,正当我发愁之际,一眼瞥见垫圈的张老汉,垫圈,如今的年轻人知道者不多,我稍微解释一下:过去,厕所叫茅圈,为了厕所卫生和清理粪便时不污染环境,必需每天运来土在粪便上垫一两次,粪便蓄满了,再用铁锨起出来,故名垫圈。垫圈也是一项农活,种地需要肥料就必须到处掏粪积肥。当时莫高窟有六七处厕所,每天都能看到张老汉往来其间劳作的身影。
《莫高窟速写》杜永卫写于八十年代初
我招手让他过来,说明了情况,老汉倒也不笨,一说就明白模特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按当时美院雇模特的工资标准,一课时三毛,全天两块四支给他报酬。张老汉起先不要,他说哪有坐着还挣钱的道理,但在我的说服下他答应挣这钱。因为我知道,做模特不是件好差事,一动不能动,一天下来,就是壮汉也吃不消,何况眼前这老汉,看上去已经六十开外,不仅背驼而且还瘸着一条腿。
《莫高窟南区》杜永卫写于八十年代初
做雕塑时用的模特,必须站在或坐在一个能转动的台子上,台子一米见方,40厘米高,可随时调整模特的角度。张老汉腿瘸,不能像正常人一步登上去,必须先爬上去,然后才能坐在凳子上。他一不小心就滑转半圈,那样子非常滑稽,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不过他挺大方,丝毫不介意,也没有首次“登台”时的晕台情况。我心想:他或许是到处掏厕所,习惯了人们的嘲笑,便学油了。
《莫高窟80年代办公区》杜永卫写于80年代初
这次雕塑是示范性的,边塑边讲。我按照张老汉给我的第一印象讲道:从打大形开始就必须同时考虑到传神,眼前是位驼背的老农,卑微、憨态且土气,一开始就必须牢牢抓住这种第一感觉。我一边雕塑一边捕捉这些我认为的他身上最鲜明的特征。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眼前这个老汉,与我平时上茅厕不经意瞥见的那个,猫腰低头、反手抄把铁锹、一瘸一拐的寒酸老农判若两人。只见他,在模特台上,两手扶膝,腰板直挺,双目有神,那最具特征的驼背也似乎找不到了。我当时认为,他那是因为过于紧张而改变了他的“原生态”,便要求他自然,放松,但他却说,平时就习惯这么坐凳子。
《莫高窟中寺》杜永卫写于八十年代初
一上午快过去了,我始终把握不准他的感觉,打出的大形怎么看也与我最初印象的“卑微、憨态且土气”不着边际,尤其他那昂扬的头颅和他那用自己的手梳理过的与老农不相符的发型,让我竟不知如何塑造。对于自己的雕塑,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形似而神不似,纵使我做得很逼真很形象,但塑造出来的人,若不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农,那一定是失败之作。临中午下班的时候,他竟不时摸出点东西放在嘴里嚼动,严重影响了我雕塑。本来我就因为把握不准造型而心中不快,看到他吃东西不免恼火。我很不礼貌地告诉他,工作时严禁吃东西。老汉脸红了,剩下的时间一动不动。
《莫高窟黑佛殿》杜永卫写于八十年代初
敦煌的3月依然寒冷,可张老汉的脸上却不断地冒汗,但我还是认为,他那是过于紧张所致。
下午课上,他仍然脸上挂着汗珠一动不动。课间一休息他就急忙嚼东西,我说才吃过午饭就这么饿?他说对不起,当兵的时候落下了胃病,不嚼点东西坐不端正。我问他当什么兵?他迟疑了一会说,都当过。这话把我逗乐了,我说什么叫都当过呀,莫非你海陆空都当过?还是国军共军都当过?他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爬上台子,依然保持着他那个与老农不相符的姿势,一动不动……
《莫高窟南区》八十年代初
不觉得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他在我的雕塑架上东瞅瞅西看看,到书架前还翻看我的书籍。我发现他识字,便问他是否念过书,他说上过高中和中专,还曾在南京军政大学进修过两年,这下我开始好奇了,心想,这垫圈老汉不一般啊,没吹牛说大话吧?我倒了杯开水递过去,半信半疑地问他:那你咋就从军大高才生混成垫圈老汉了?老汉见我没有恶意,平时他也能看到我整天在洞窟里画画临摹,在石窟外到处写生,是一个比较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可能因此对我怀有好感和信任,也可能是因为那几年的政治环境开始宽松,因言获罪的时代开始慢慢转变,于是他才敢反问我说“你知道远征军么?”什么,远征军?远征军这个名词我在几年前听过一次,那不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吗,它曾是我们单位一个老学者当年的一项“罪名”,这个名词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但为了不干扰他讲下去,也为了解除我多年的一个疑惑,我说不知道,听都没听过,但我很想知道。在我诚恳的目光期待下,他终于对我们讲起了,他亲身经历过的那一段,在当时已被中国人集体失忆了几十年的抗日战争中的故事。我也干脆洗干净了手上的泥巴给老汉搬过去了我的靠背椅,索性听他讲讲对我们这辈人来说,那个十分陌生的——中国远征军。他这一开讲不要紧,随着他传奇故事的展开,眼前的老汉,不!老人的形象在我的眼睛里,已不再是最初的那种“卑微、憨态且土气”的感觉。他很有口才,他的故事让我们听得入迷,听得激动,听得唏嘘不止、热血沸腾!
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资料图)
老人名叫张有宁,敦煌人,大约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抗战年代,他正于国民政府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酒泉中学前身)读书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政府因英国政府请求,准备组织一支远征缅甸的抗日部队。当时抗日宣传遍及全国,很多学生投笔从戎。17岁的张有宁正是在这一时期的1942年,不顾家人阻拦,毅然应征入伍参加国军,随即被编入远征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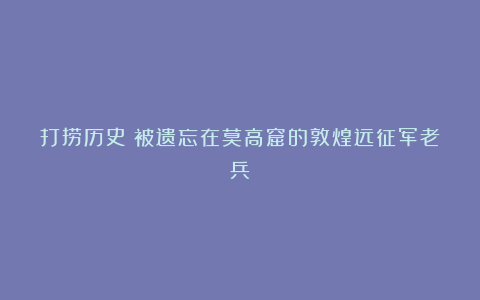
中国民众欢送远征军赴缅作战(资料图)
据他说,中国青年远征军是国民政府组建的一支文化程度高、武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部队。队伍里绝大部分都是知识青年。当时甘肃是抗战大后方,参军出去的学生兵不少,仅敦煌就有五六个学子赴缅参战。进入缅甸的十万青年,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队伍。他所在的部队叫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是当时中国最强的机械化部队。老人不无骄傲地说,他们的部队进入缅甸后,所向披靡,打得日军闻风丧胆,歼敌无数。此外他们还解救出了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的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他们战功赫赫、威名远播,使新一军成为了当时驰名东西方的“王牌军”。
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资料图)
1945年日本投降后,按照盟国商定的结果,中美英准备分别派兵进驻日本。当时他所在的新一军,很多人被作为进驻日本的中国军人挑选出来进行培训。据他讲,准备进驻日本的中国军人还要求相貌、身高以及文化程度: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而他因为条件符合且作战勇敢,又是政治学校出来的高才生,刚刚十九岁就当了少尉排长,于是被确定为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第一批人选。
1945 年圣诞之夜新一军军官与盟军联欢(资料图)
1946年初的一天,他们被集合登上了轮船,准备前往日本。在海上颠簸了几天以后,他们终于登陆了,当看到岸上阔气的洋楼洋房鳞次栉比,他们都非常兴奋地以为到了日本,然而,他们却被长官欺骗了,登陆的地方不叫日本而叫秦皇岛。当时国共已经准备开战,原本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驻扎日本,但最后因内战使中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化为泡影,成为国人至今耿耿于怀的遗憾之事。
1945年进入沈阳的新1军新38师,全美械装备(资料图)
沈阳街头欢迎从缅甸回来的国军进驻的标语(资料图)
他还讲到,在东北期间,他们的部队被称作“铁军”,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把短枪,全服美式装备。平时行军多乘卡车和吉普,还和苏军干过仗,他说子老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但后来不到两年却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我问他,你们那么厉害,怎么就打不过共军呢?他已潮湿的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喉头动了一下,却没有作声。
1944年6月16日,缅北中国远征军攻占加迈远征军向日军猛烈开火(资料图)
中国远征军,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二十万热血青年组成的虎贲铁军,一支本该作为战胜国驻扎在日本的军队,被投入到内战后,烟消云散。他们当中大部分后来成为解放军的成员,他们因掌握先进武器装备技术,成了解放军中作战素质最好的战士:他们教会了土八路使用大炮、坦克、迫击炮……壮大了解放军的力量,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张有宁老人就这其中的一员。
远征军坦克兵(资料图)
远征军在安装武器(资料图)
1941年1月,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加入《租借法案》中国抗日军队接收了35辆美制M4谢尔曼系列坦克。中国远征军驾驶这批坦克深入缅甸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取得了众多战役的胜利。(资料图)
新中国成立后,老人被选拔到南京军政大学深造,原本会成为军中重要人才而前途无量,但后来因一次“口误”而因言获罪,从此开始他人生的厄运。这个所谓的“口误”是怎么来的呢?他说,一次部队组织看电影《南征北战》,该片描述的四平战役,讲述的是1946年-1948年国共双方先后调动了大量兵力,在四平展开四次大战役的事情。当看到国军缴械投降的场景时,他情绪激动,他说了一句:这不真实,国军不是因为打不过才缴枪的。结果,他被告发了,接着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直到1960年因粮食短缺,被遣返原籍敦煌务农。十八年前为保家卫国走出敦煌,走上抗日战场的热血男儿,十八年后又灰溜溜地被国家当作犯人发配到了家乡。
北大荒劳动场景(资料图)
回到家乡,并不意味着他厄运的结束,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他必然首当其冲。长期被批斗和繁重的劳动改造,没有击垮他的精神却击垮了他原本强壮的身体。战争中就搞坏的胃,在那个时期被切除掉了四分之三,因此他必须一天到晚不停地嚼点东西才能撑下来。一个地主成分又曾是“蒋匪军”加“反革命分子”多重身份的“阶级敌人”,在那个年代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是上苍的恩赐。他说敦煌的亲戚多比较纯朴,明里暗里帮助他,才使他度过了那屈辱、悲惨的岁月。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张有宁老人不再背负那些沉重而屈辱的“帽子”去熬度人生,能够安心从事晚年的一份垫圈工作,他说他知足了。
一位老师的文革速写
听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我问他你那条腿是战争中负伤的么?他说不是的,他一直很幸运,可能是因为敦煌大佛一直保佑着他,虽然战斗中经常挂彩,但都没有危及生命,而这条瘸腿,是后来被批斗时打残的。至于那驼背,他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但我断定那不是病理上的脊柱变形,不然他不会在模特台上坐得那么端正,或许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因长期的磨难、屈辱、隐忍、被低头认罪,抑或是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养成的已经不能自我纠正的习惯动作吧!
今天街头的远征军历史图片宣传
听完了张有宁老人讲的故事,我为自己的肤浅感到羞愧,也为自己先前对老人不恭感到深深的自责。我非常投入地以最快速度完成了这件头像作品,我不忍心让老人在那模特台上坐得很久,也不忍心看他瘸着腿爬上爬下的样子,我手上的雕塑已经不是最初设想的那样,我不再凭借自己浅薄的主观意识去把我所要雕塑的人事先设定成某种类型,也不想刻意地把他塑造成什么英雄好汉。我只想认真地,发自内心地,努力把我眼前的老人,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把他在垫圈劳作中已经看不到的,他原本的睿智、深邃、刚强的内在气质定格下来。我做得很像,但别人看过后都说,虽然很像但气质不像,你没有把他做成垫圈老汉。我说:不,我做的是军人!
2004年于敦煌初稿,2013年整理修改
张有宁先生永垂不朽!
后 记
2013年我将此文收载于我们主编的《当代敦煌》一书之后,有一天一位70来岁的老人带领他40多岁的儿子来到我的工作室,他说他是张有宁的大儿子张孝孔,他说他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很是感动,于是特意带着他的长子前来感谢我。他说我文中记述的很多关于他父亲的事连他都不知道,他说他在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们母子去缅甸作战,父亲回到敦煌的时候,已是18年以后,他自己都已经20岁结婚成家了。他还说父亲活着的时候,很少给他们谈起他在外面经历的那些事情,他只是从他母亲那里得知他的父亲是为保家卫国奔赴抗日前线去了,回来以后怎么成了那样,他一概不知原因。他曾经很想知道,但父亲从来不提起,他也不知到为什么。我在想,他的父亲不愿在孩子面前提起往事,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很伤心,不愿揭开那屈辱的疮疤;另一个原因是他不能说,即便是他和他那些战友的抗日事迹他也不能说,因为在那个年代,讲出来就会大祸临头,都会给家族和后人带来无穷的麻烦,他只能把一切都埋葬在肚子里。张孝孔老人两眼湿润地说,他一直对父亲的认识很模糊,直到他读到我这篇文章,才看清楚了自己的父亲!
中国远征军是1942-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出征滇缅印、抗击日本的英雄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征战取得彻底胜利的丰碑。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对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立下赫赫战功。本贴作者按中提到的那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所谓右派,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也是敦煌研究事业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和本文主人公张有宁先生,都曾是中国远征军的铁血战士,真正热爱祖国的热血男儿!我们《当代敦煌》已计划在“打捞历史”栏目,对这位已故的,历经磨难而又谱写下壮美人生的老前辈,进行挖掘研究并深入报导!
2017年10月31与敦煌修改整理
作者在创作《王子牧羊油画》
杜永卫 曾用名:杜一田。非遗敦煌彩塑技艺传承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高级环艺设计师,教授。历任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副所长、敦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东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东京艺大客座研究员;中央美院雕塑系传统课兼职导师;兰州交大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师大敦煌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客座教授;酒泉职业学院特聘教授;江南石窟艺术指导专家。敦煌中国画研究院学术院长,《当代敦煌》总编辑。
作品曾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并赴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展出。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国驻澳大使馆、埃及开罗市政府等机构收藏陈列。敦煌菩萨银币设计获美国世界硬币大奖赛最佳奖;龙门石窟卢舍那银币浮雕获新加坡国际钱币博览会金奖。其他美术作品屡获国际、国家和省级各种奖项。雕塑作品《水月观音》获云冈国际佛教艺术大展最高学术成就奖。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