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伦敦城北部的巴比肯,是建于二战后的住宅综合体。曾被票选为“伦敦最丑建筑群”的它,如今却成了伦敦最特别、最有个性的区域,也是建筑与文艺爱好者的天堂。
二战后的“城中之城”
如果你在词典中搜索“Barbican”,出现的解释是“瓮城”,一种紧邻主城门外,半圆形或方形的防御与屯兵小城,如中国长城的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位于巴比肯庄园南面的伦敦墙街和城墙遗址,便是英国版瓮城。
19世纪,这里是工厂、仓库、市场和商店的聚集地。二战期间,包含巴比肯在内的伦敦城遭受德国纳粹闪电战攻击,满目疮痍。正所谓全面的毁坏带来重置的机会,战后为了快速复兴城市,英国住房部长邓肯·桑迪斯提出建造一个战后模范社区。建筑团队张伯伦、鲍威尔与本恩承接了这个任务,有别于传统居住楼盘,他们提出了“城中之城”的概念,欲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乌托邦。
这个城中之城整体布局参考了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和《光辉城市》理论,三座平面布局成三角形,高43~44层的塔楼,是光辉城市的“点式高层建筑”,悬挑阳台端部优雅地卷曲着,像船身一般。它们也有实际用途,特殊的形状减少了风荷载,并减轻了结构框架的应力,阳台出挑距离很大,为下层创造了深深的檐口,这些檐口既提供了来自构件的保护,又为居民带来一种安全感。U型、口型、Z型、条型的公寓,搭配顶层半圆空间,则是马赛公寓“版式多层建筑”的变体。架高的平面层、水平窗带与过道、屋顶花园、洋房等设计,也都满足了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五原则”。塔楼和裙楼的围合,呈现出一种介于古典欧洲住宅广场和现代住宅开发之间的折衷感。此建筑群被取名为“巴比肯”。
造镇、造小区,在如今看似稀松平常,可在二战刚结束的欧洲,算是巨型开发项目。巴比肯光住房形式就有顶层公寓、塔楼式公寓、裙楼式公寓、联排别墅等,近2000余套。除此之外,还包含商店、学校、教堂、美术馆、图书馆、温室花园、中央人造湖、电影院、酒吧、餐厅、咖啡厅等配套设施,就连英国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也规划于此。伦敦地铁甚至为它重新设立了巴比肯及沼泽门地铁站。集万千生活所需于一身的巴比肯,确实称得上是一座小型城市。
迎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混凝土的灰色调、战后的住房短缺问题,以及勒·柯布西耶的设计理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住房或经济适用房。然而这仅仅只是建筑形式上的“混居”,打从一开始,巴比肯的建设就是以出租给相对富裕的人群为目标,而不是真正的阶级混合。
建筑师对客群的定位有这么一句描述:“年轻的专业人士,可能喜欢地中海假期的风格、法国美食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住宅内部的设计也暗示着这点,庄园中不是工作室、小型公寓,就是别墅。带有景观阳台的客厅、极具现代感的室内装潢等等,都是在迎合中产阶级对生活的向往。
这些细节的出发点,是以设计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同时,鼓励中产阶层的人们回归,从而振兴城市与经济。因此,最初的建筑计划,是以白色大理石和抛光混凝土作为主立面材质,搭配缤纷的马赛克装饰。但巴比肯区从自给自足的垂直花园城市,到学校、酒店和公共空间的引入,再到为中产阶层以上客群而打造的艺术中心,不断修改的规划与设计,也使工期和预算不断超出,最终统一改以价格低、工时快及难度低,且时下正流行的粗野主义风格。不过,如今还是能在顶层公寓的半圆屋顶、图书馆与艺廊的方盒空间等地方看到纯白的粉刷。此外,地面的黄色指引线、蓝色金属扶手板、红色消防设备、绿色的柱头、木质的门窗等缤纷的配色细节,也点缀了刚毅的建筑群。
纵使毁誉参半,巴比肯住宅区的发展可说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桃花扇》的反面——先看他楼塌了,再看他出计划,最后看他起高楼!从断垣残壁发展成一个完整且扎实的城中之城,从社会层面来看,2000多套住房确实缓解了战后居住短缺的问题,也改变了邻近金融区以商业为导向的单一土地规划模式;从生活层面来看,巴比肯的设计、宣传与营销,改变了因工业革命导致居住郊区化的模式,民众逐渐回归城市;而大胆地将文化与艺术置入庄园,也准确地预测了伦敦未来的生活体验与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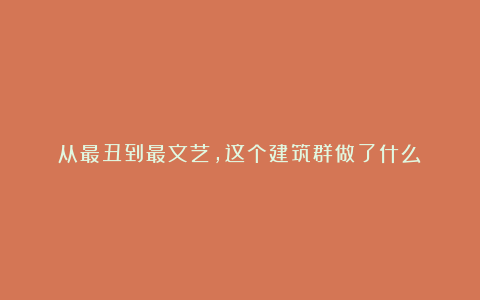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相较于整个巴比肯住房的开发,艺术中心直到1982年才完成,它包含伦敦最大的公共图书馆、艺廊、如阶梯金字塔般的剧场、应用剧场屋顶空间的植物园、女子学校、音乐学校,以及重建的圣吉尔斯教堂,穿插散落在人造湖周围。
由于巴比肯的开发时间过长,在艺术中心建成的80年代,粗野主义风格已经过时,时下流行的是由玻璃和钢铁为主的“高技派风格”,巨大的体量与“性冷淡”配色,也使巴比肯在2003年“灰伦敦民意调查”中被评为“伦敦最丑陋建筑”。朴质、坚实,已经是对它比较好的评价。
但正所谓“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审美是主观且随时代改变的,走过风霜的巴比肯靠着内在气质力挽狂澜,成为伦敦最重要的文艺胜地。这里不仅是全欧洲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也是伦敦交响乐团和BBC交响乐团的驻团场地。随着时代演变,多元音乐也逐渐涌入,如非洲的现代舞、印度的民族乐器等,当然,英国古乐学会乐团演绎的巴洛克和古典音乐也是常客。1988年推出的巴比肯国际戏剧节“BITE”,使戏剧、舞蹈、音乐的结合不再局限于物理建筑,成为满足文艺爱好者们的视听盛宴。
巴比肯美术馆不定期推出大大小小的展览,例如知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的设计展、英国当代视觉艺术大奖“透纳奖”获奖作品、伊姆斯夫妇的家具展等等,都曾在此展出。可容纳1949个坐席的巴比肯剧院,则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经典剧目的场所。不喜欢古典的朋友,可以到毕特剧院体验实验剧场,观看互动式木偶戏,当然也能到电影院欣赏各式电影,刺激的好莱坞大片或小众的独立电影会在三座电影院中轮番播映。
顶楼植物园坐落在剧院上方,屋棚由钢和玻璃构成,开放于1984年,是伦敦第二大的室内植物园,拥有大约1500种植物和树木。或许温室的出现,一方面源于曾经大英帝国的民族习惯,他们喜欢收藏、展示外来的生物;另一方面,温室也保护了这些在原生地已经稀有甚至濒危的植物。除了文艺活动,植物园也出租作为婚礼、庆典、私人派对等活动的背景板,以及地方学校户外教学的热门基地。走进温室,湿润的空气和茂盛的植物林,加上水泥建筑的衬托,一种有别于赛博朋克的超现实混搭感瞬间席卷而来。
除了封闭式的植物园,中央人工湖也为许多野生生物提供了自然栖息地,鹦鹉、绿头鸭、苍鹭等滨水生物都是这里的常客。员工们殷勤的修缮与保护,加上动植物的自然定居,让巴比肯内部形成了微气候,据说这里比伦敦的平均气温温暖了3℃。
乌托邦社区的实现
在顶层筒形公寓中醒来,穿越带有黄色指引的红褐色铺砖过道,喷泉如舞动的音符呼应着不远处的音乐厅,静谧的湖面与摇曳的植被交相呼应,在郁郁葱葱的植物园中享用司康与伯爵红茶……看似梦境的惬意生活,都能在巴比肯实现。
巴比肯建成至今,从“未来生活的示范社区”,到“现代世界的奇迹”“伦敦最丑建筑”,再到“欧洲音乐与文艺重地”,已然过了40个年头。正如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所言:“建筑至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建造者设想的生命,一个是他日后度过的生命,两者从不相同。”有趣的是,巴比肯独特的粗糙肌理,都是在现场浇注的混凝土基础上,以“纯人工”锤击的方式一点一点凿出来的。刻意将车行和人行道分开的设计,加上建筑楼、空桥与平台的相互交错,不仅隔绝了外界嘈杂的喧嚣,也自然分割了公共与私密空间,变化的平台更是增加了视觉与步行的趣味性。
架高的平台不仅丰富了居住生活,更保护了古罗马时期的伦敦城墙。不过在寸土寸金的伦敦,不像大部分古迹保护的手法,这里的城墙被低调地安置在巴比肯博物馆地库中,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彩蛋。从停车开始就能看展,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展陈。
另一个彩蛋,是位于红砖平台上,一棵造型如王座般的树。它以19世纪作曲家费利克斯·孟德尔颂命名。传言孟德尔颂曾在这棵树生长的地方——英格兰东部的白金汉郡伯纳姆山毛榉林中获得灵感,谱出了经典的《仲夏夜之梦》。这块林地在1880年被伦敦城政府买下,而这棵树也在1990年被吹倒,树桩最终被卖到了巴比肯艺术中心。所以究竟这棵树和巴比肯有什么关系?孟德尔颂不是英国而是德国人,树和巴比肯也没直接关联,也许,将种种看似没有关联的事物串在一起,并一本正经地展示出来,就是他人难以理解的英伦浪漫。
巴比肯在2001年被英国遗产保护组织列为“二级文物”,它从规划之初至今,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预想——“自给自足的乌托邦”。日趋繁茂的植被覆盖着粗糙的混凝土表皮,诉说着不曾被遗忘的垂直花园城市理念。现在的它,代表着自由、奔放、率性、多元,同时又象征着严谨、端庄、高尚、典雅,宛如遗世孤立的桃花源。
·END·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