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文|胡叁叔
编辑|胡叁叔
前言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非洲狮的祖先可追溯到十二万年以前,两万年以前,它们就从非洲向亚洲印度迁徙,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渐缩小,目前已绝迹的巴巴里和北非地区的伊朗狮,都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狮子造型艺术由西向东的传播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远古时代,人们常以动物王国的规则来比喻,设想人间的规则,便以处于生物王国最上层的野性动物,来代表其政治和神灵的权力,并以语言、服饰和仪式为载体。
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区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野兽也不尽一致,其中,在近东,印度,中亚,甚至在中古时期,甚至在欧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无处不在的对比视角和材料里,动物和信仰的联系十分紧密,在古近东,希腊和罗马,波斯,以及南亚的印度和中亚的大草地上,都有大量的“动物”的史实。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特别是,在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狮子更是不同信仰和不同的生物,在中古代历史中,它也是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生物。
在地中海各国的狮群起源地,从埃及到两河流域,再到希腊,各种狮群的形态都有,经过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而演化出基督教与伊朗的狮群。
印度的信仰中也有许多关于狮的图像。地中海、南亚地区的“狮群”向欧亚地区迁移,形成了“大平原”式的“狮群”;而到了中国,又被“华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狮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全世界的宗教和文化中,狮子形象的交互与演化,不仅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狮子形象,也折射出了人性美学在各种信仰和文化交互中的独特规则。
狮身人面像源于埃及和西亚,最开始的时候,埃及就已经有了狮身人面的作品,而在18世纪(大约在公元1567-1320),更是从大名鼎鼎的图坦卡门陵墓里挖出来的一张金色的椅子,就是中国的和尚们用来当金狮的床榻。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椅子的靠背上,雕刻着两个金色的狮头,代表着法老王的权势,椅子的四条腿,则是模仿了狮的前肢和后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发掘出来的亚洲最早的石头狮子,还有随后在绘画、青铜器等上描绘的狮子的卧、走、跪、蹲等姿势。
它们的前肢伸展整个身体卧下,前肢直立,后肢蜷卧,奔跑伸长、人狮搏斗等,这些都说明,他们已经对狮子的形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创造,一直到公元5世纪,狮子的形态才趋于完善。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从武惠妃石椁拂菻画到敦煌画稿
根据《后汉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记录,《狮子王》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汉章帝章和二年八十八岁的时候,月氏派使者来献狮子,而月氏在汉和帝永元二年的时候,又派使者来进献过狮子,以及永元十三年的时候,安息王满屈来过狮子。所谓的“狮子”,其实就是伊朗人的“狮子”。
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长安城中有“慈恩寺,四壁为尹琳所绘,正西方为狮,东方为大象。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曾有一篇关于长安道政坊宝影庙的文章,“韩干曾在庙中绘制过一幅穿着紫色僧袍的弥勒佛画像,画像中的佛像和两只雄狮栩栩如生。”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文殊”和“普贤”就是骑着“狮”和“象”的佛像,在洛阳,成都和五台山,也有类似的佛像。袁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纪》中提到,五台山佛陀庙中,“坐着一尊雄狮,满五殿,雄狮神态威严,步履轻盈,呼吸均匀,看得时间越长,越觉得是在活动。”
早在唐代,开元以后,就出现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佛教作品,西安碑林中也发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佛教壁画,比如唐开元九年(721年)兴福寺一座残存的石碑旁的狮人,其实就是一个人端端正正地端坐在狮头之上,并且在狮头之下还垫了一块圆形的地毯。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开元24年(736),大智和尚的石板上,雕刻了一尊披着绸缎的仙人,坐在一头雄狮之上,周围环绕着一圈葡萄架和百合。石台孝经碑下的奔狮,不但头顶有一对长鹿,而且周身也有一道豹纹环。
应当说,狮子是佛陀高贵、威严、勇气、力量的来源,这跟它借助百兽之王的形象来突出自己的身份有很大关系,不过,不管是骑狮人,还是坐狮人,他们的面孔和衣着都属于武者的,而不是菩萨的神像。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尤其是在碑林藏盛唐地宫的石门上,有一幅壁画,壁画上有一个胡人,戴着冠冕,身穿一身唐装,手里提着一根长长的锁链,一只手提着一条用来训练狮子的锁骨,跑了出来,颇有几分“华化”后的骑狮者的风范。
在同一时期,韦泂墓、李宪墓和薛儆墓的石棺上,都有一些精细而复杂的纹路,以及一些走兽的纹路。在山西薛儆开元九年(721年)的墓石椁线上,雕刻着各种奔驰的狮子、大象和神兽,而在棺材的柱子上,则雕刻着一位骑着狮子的胡人。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唐玄宗在开元后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其中等级最高,也是最精致的一件作品,就是贞顺太后(武惠妃)于开元25年(737)的石椁上线雕刻。
而牵狮的形象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战士,头顶高高鼓起,脖子上套着一个项链,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腰间系着一个袋子,身上裹着一条绸缎,一只手握一根绳子,另一只手则将一头雄狮绑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是一种希腊和拜占庭时代神话中的经典形象。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类似的形制可在敦煌所绘的《文殊菩萨坐狮子》中找到。
这位骑士,是一位长发披肩,双目炯炯有神,手中握着一根手杖的武士,他坐在一只张开血盆大口奔跑的雄狮之上,双脚紧紧地踩在雄狮的肚子上。
这位骑士大概就是希腊罗马传说中的“雅努斯”,他手中握着一根手杖和一把关键的钥匙,守护着房屋、街道和城市的安全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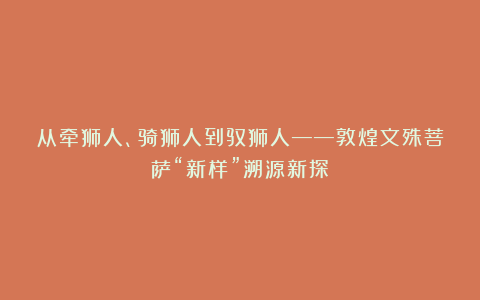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中晚唐以后文殊菩萨“新样”的图本改造
长安皇室的画家和匠人们,根据外国粉本制作了牵狮人、骑狮人和训狮人,并以此作为模板,用于京城的寺庙和其他地方的岩画,敦煌17号窟内的藏经洞中所出土的画作,说明了他们在制作过程中做了充足的工作。
不仅需要手工绘制,而且需要参考粉本绘制,“粉本”是6-10世纪画作的总称,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明确指出,无论是纸张上的画作,还是绢画上的画作,都必须以粉本为基础。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粉本的基本结构可以长时间保持不变,但其内容可以随着技艺进行临时性的制作,进而产生丰富的新风格。
文殊菩萨坐狮子的丝质画像,毫无疑问是一幅以粉末为基础的、按顺序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敦煌220窟的通道北面,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发现一尊文殊像,这尊雕像是五代唐朝庄宗所画,名为《大圣人文殊师利佛体及随从》。
有专家推测,这幅文殊像是在五台山绘制的,上面有一幅匾额,上面写着:“文殊像,骑着一只绿毛雄狮,右边是一名络腮胡子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马鞭,看他的样子,应该就是“于阗王”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因为归义军节度使氏与于阗皇族有长期的婚姻联系,因此,敦煌石窟中有许多关于于阗瑞象、护法神的图案。
五台山是唐代皇室寺庙,画的时候,用的是长安的白描,与吴慧妃棺材上的白描很相似,但那个时候,工匠们或许认为这是古代的驭狮人,所以无法分辨出牵狮人、骑狮人和驭狮人的区别。
到了后期,更多的人被误认为是南海昆仑人,所以,在“新样”的传播中,于阗王和昆仑人都被称为白描。“新样”可以简单地被解读为一种新的风格,但是,对一种“样式”而言,它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对形象的新的认识和观察方法。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于阗王”代替以往的“昆仑奴”成为驱使狮子的人物,说明敦煌文化中添加了一些异域因素,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风格。
我们发现,不但敦煌有于阗王与昆仑奴隶的“牵手”图案,而且在瓜州的东千佛洞和吐鲁番的巴兹克里克岩洞中也有,在内蒙古的黑水城中发现了内蒙古的“黑水”遗址中发现的“西夏丝绸”图案,在日本京都的“清净”寺庙中发现了“观音坐狮”图案,在佛殿中发现了“慈悲”图案。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消息之所以会流传开来,就是因为长安的缘故。还有杭州飞来峰青林洞的卢舍那佛抱着狮子的雕像,以及南朝的北山镇的雕像。
这些都表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每一个时期的艺术家都能独立创作出来的,尤其是那些艺术家,他们不会抛弃现有的图案,另辟蹊径,这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延续。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长安大批匠人迁移到河西一带,敦煌便成了长安画家和绘画作品最主要的聚集地。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当时的社会各界都在祈祷着和平,供奉着功德之主,迫切需要画家们用新绘画作品来填补心灵上的空虚,于是文殊佛像和佛像也随之繁荣起来。
九世纪以来,莫高窟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长安皇室和寺庙里的绘画作品,也被敦煌画家们复制并复制,甚至达到了几十幅之多。
从敦煌壁画“韦摩”的发展与演化可以看出,最初盛行于敦煌壁画上的中原帝王使臣、外邦蕃王使者问疾的画面,在中唐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画面形式与美学形式。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维摩不二图》中,有一幅描绘了“比丘里”的维摩,正与文殊菩萨辩论,四周有菩萨、门徒、天女和天王诸神,为一幅有名的作品。
尤其是那名长着络腮胡子的外来人,更是猜测他就是于阗王,他一直以为络腮胡子,戴着鸭舌帽,眼睛深邃,鼻子高挺,就是天王,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中唐之前,那些高鼻子,眼窝很深的外来人,在画面上并不常见。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从长安至敦煌这一时期美术形象风格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牵狮子的人,从满面络腮胡子的老者,变成了昆仑的奴隶,或者是于阗的国王,在迎接佛祖的时候,牵狮子的姿势也变成了站在原地的姿势。
其次,是骑狮者,从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者,变成了一个文殊佛陀,他的两条大腿耷拉着,而不是一个骑着一头雄狮的老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第三,驱狮者:从西域的蛮人驱使雄狮的速度变成了昆仑人驱使雄狮的速度,于阗王的样子也从昆仑人的样子变成了温顺的样子。
在盛唐向中唐转变过程中,“核心”在哪里?在“变异”的文化和美术的交流中,华化和佛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如同一种拂尘
结语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狮”是一种“异域文明的典范”,“狮”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信仰”,原本对“狮”的描述更多地体现在佛教对其奉纳上,而非对其雄壮的追求,这只是一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根据“拂菻画”中的素描,对原有的“狮”进行了重新设计和表达。
从形态变化上来说,狮群从凶悍凶残变成了强大而平静,从人类与狮群的融合变成了温和而谦卑,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在节日宴会上的狮群中,“华化”的标准人物也渐渐变成了和平的象征。
而在明朝和清朝,狮群则安静地蹲在门前,就好像一只被阉了的哈巴狗,再也没有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也没有了往日的雄伟。这头雄狮已成了一头普通的雄狮,它已没有了咆哮的雄狮。石狮与西域的异国画风是彻底不同的,学界同行可以感受到,我就不多说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从盛唐时期的牵狮人、骑狮人、驭狮人,到中唐时期文殊佛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绘画粉末,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也没有因千里之外的距离而丧失联系。
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华化”的过程中,继续焕发着勃勃生机,这既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的魔力,也是敦煌文化“世界性”的共享和共通的界面。
参考文献
1.《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张惠明.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敦煌研究,2000(4):1-9.
3.[林伟正.五台山文殊骑狮像的宗教图像历史与视觉文化分析(上、下).艺术学研究,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