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医踪:消失的子山氏
陈子煜
前言:在奶奶给我留下的那一箱古籍医书里面,有几本手抄本字迹最为工整,落款为子山氏张春启。问过很多老人及本地的文化学者皆不知张春启为何人,史料理毫无记述。那册《脉决》抄本边页挤满蝇头小楷,某处批注:“壬寅春,治周家媳妇癥瘕,用抵当汤加麝香三分,经行如墨三日而愈。“这让我想起张大夫沟的传说,那位总在深夜提着桐油马灯出诊的郎中。村中老人摩挲着抄本惊叹:“这手悬针垂露的功夫,没有三十年临池写不出来。“常言道见字识人,写出如此字迹的人定然也医术不凡。遥想佛坪境内与此相关的大概唯有张大夫沟这个地名了,不由的大胆将此二者联合起来,作此闲文。
——陈子煜
祖母去世后,我常在老宅阁楼翻检旧物。某日拂去桐木箱上的蛛网,一摞泛黄的古医书在晨光中浮现。这些祖母留下的医典大多虫蛀严重,唯三本手抄本保存完好,素绢封面上“子山氏张春启“六个行楷清隽如竹,墨色历经百年仍泛着幽蓝光泽。这样的字迹,让我想起熟的那位太白山下的老中医,他案头永远摆着《灵飞经》和《黄庭经》,说习字如习医,都讲究气脉通贯。指尖抚过“子山氏张春启“的落款,墨痕里仿佛还游动着百年前的呼吸——字是极工整的馆阁体,横折处却藏着柳骨颜筋,像极了老药铺抽屉柜上的隶书铭牌。
在县档案馆的铜锁木柜前,管理员老周抖开登记簿:“光绪二十年到民国十年的县志都在这里。“泛黄纸页沙沙翻动,墨字里跳出同治三年的虎患、宣统元年的蝗灾,却始终不见“张春启“三字。县志编修王老摘下老花镜沉吟:“子山氏倒像是别号,秦岭七十二峪,古时隐士多爱以山为号。“戴着铜框眼镜的管理员老周啜着搪瓷缸里的浓茶:“咱们这深山里,多少赤脚郎中活人无数,县志上连个药渣子都留不下。“沉默半晌,他又推了推鼻梁上的铜镜框对我说:“或许你可以去张大夫沟问问,都是张大夫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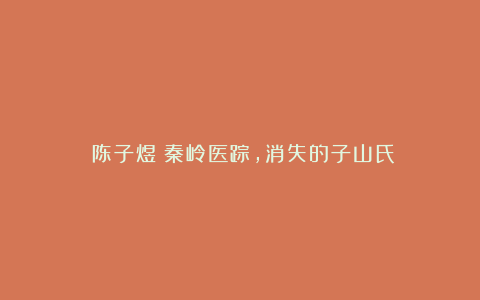
张大夫沟的晨雾总比别处散得迟些。露水打湿的羊肠小径上,九十岁的周阿婆正在晾晒柴胡。“张家药铺啊,原先就在那麻柳大仙的庙后头。“她颤巍巍指向半坡几块青石地基,“说是光绪年间发山洪,连人带屋冲得影儿都没了。“老人浑浊的瞳孔里泛起星点光亮:“我奶奶见过张大夫,总挎着个藤药箱,穿一身青布褂子,头上缠着一头黑包帕。“
在村东头残存的半截土墙下,我遇见了据说是张氏后人。满脸沟壑的老汉蹲在门槛上卷烟:“听太爷爷念叨过,祖上是有个会扎针的,后来遭了祸事。“烟丝明灭间,他忽然压低嗓音:“说是三个娃娃生下来脸跟染坊布似的,接生婆吓得摔了铜盆……”话尾被山风卷走,散入坡地上的野薄荷丛里。
后来一位名老中医翻着我手机里的照片沉吟:“红面可能是新生儿红斑,花脸或是胎记,这在现代医学都能解释。“她忽然指着书页间的批语:“看这句‘小儿惊风,当察目睛青脉‘,百年前就懂得观察眼底变化,这位大夫不简单。“窗外的广玉兰落下一片白瓣,轻轻覆住“慎用斑蝥“的朱批。
黄昏时分的张大夫沟浸在黛色里,放牛人赶着牲口趟过溪水。那些工整的墨字突然在眼前活过来——青衣大夫踩着露水出诊,药箱里艾绒压着《临证指南》;深夜归来时,桐油灯照见木盆里三具小小的紫绀躯体;砚台里新磨的墨,从此混进了妻子无声的泪。
山月爬上老药柜时,我终于一个手抄残卷上寻到蛛丝马迹:“张春启,同治八年自城固迁入,精医术,善疡科,无嗣。“墨迹在光绪十七年处洇开团云雾,像极了那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追问。玻璃柜中的医书依然散着淡淡药香,某个夹页里露出半片风干的佩兰,不知是百年前的哪位病人夹进去的谢礼。
陈子煜,医生。
陕西佛坪人,现居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