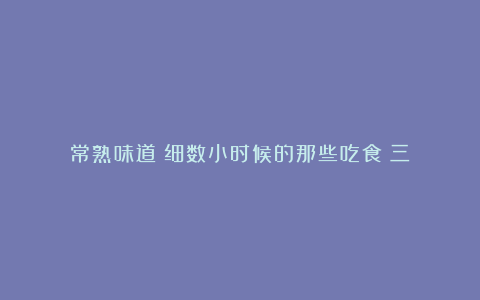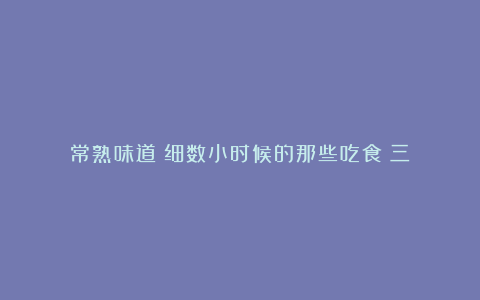|
春天来临,大地复苏,青团子、酒酿饼就上市了,许多茶食店、点心店一盘盘油光锃亮的青团子就整齐地排列好了,同时,在店门口摆出平底锅,一炉接着一炉地熯酒酿饼,有猪油豆沙与玫瑰猪油两种。
常熟的酒酿饼与苏州的形态略有不同,比如苏州采芝斋的,个头像鲜肉月饼那样,小而厚;而常熟的,较大而薄,但其味道差不多。正反两面色泽焦黄,硬壳酥脆,周围饼皮松软弹牙,酒香浓郁。吃刚出炉的,香甜滿口,一边烫嘴咧牙,一边却狼吞虎咽,真叫一个“煞念”(这是一句常熟话,意“舒服极了!”)。
这时候,春笋也大量上市,有浙江的大档笋、本地虞山的黄笋、燕笋,我只知道黄笋比大档笋小,色黄,但比燕笋大。燕笋像一支支箭竹一样较细瘦,色较淡,带点青绿,肉质细嫩清香,毎天早上山民拿到早市场一小捆一小捆的扎好卖。
笋的吃法很多,我家一般有笋烧肉、笋烧鱼、笋丝炒肉丝、笋丝摊蛋、油焖笋、笋炒莴苣、笋烧豆腐、虾米笋丝紫菜汤等等,当然,最常见的是腌笃鲜。加了笋之后的菜肴特别鲜美,往往是笋先吃光。
家里也常熬笋油,夏天加点虾子酱油冷拌面是绝美佳品。也有不少人家论担买春笋,因为大量上市时十分便宜,买后去壳切条焯熟,放黄豆加酱油、糖一起烧,然后放在匾子上晒,晒干后即为笋豆,易于储存,既可当粥菜,又是可口的零食。
春暖花开时节,街头巷尾到处能见到叫卖刀鱼的挑担人,他们大都来自长江边的浒浦,那里盛产长江刀鱼,刚捕获的刀鱼,鱼鳞银光闪闪,鱼鳃鲜红,鱼眼明亮,十分新鲜,价格很便宜,是百姓的寻常时令菜。
一般用来清蒸或草头垫底红烧,鱼肉白嫰细腻,鲜美异常,但我本怕腥不喜食鱼,又嫌刀鱼细刺很多,所以不太喜欢吃,偶尔夹一筷中段尝尝,真是个“阿缺西”!
如今刀鱼已成奢侈食品,动辄上千、几千元一斤,令人咋舌,真难以想象!
同时,油菜花盛开前后,正是甲鱼最肥壮的时候,所以也叫菜花甲鱼。
有一次,父亲约几个朋友在家聚餐,有一个朋友就在老同兴门口的那个熟食摊上买了一只菜花甲鱼来,夹了一块甲鱼肝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甲鱼的味道,真是鲜!从此也知道了甲鱼最好吃的部位是裙边。
那里三日两天有新鲜的甲鱼卖,那时的甲鱼都是野生的。
农历三月初三是常熟的拜香日,长长的拜香队伍从城隍庙出发经西门、山前街,登虞山到祖师山藏海寺。
这天热闹非凡,拜香队、看热闹的游人、小贩齐涌到西门,平时冷清的山前街一下子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流如潮,似今日之赶庙会。
山前街上的山前豆腐干生意大好,该豆腐干也是常熟一种特产,历史悠久,由山前一农家祖传工艺精心制作,细软鲜美、其味独特,比现在的开洋豆腐干要好吃多少倍。有一块块的,也有小方块的用稻草绳扎串起来一串串卖,既可当零食,又可点饥当主食。
到五月份,本地蚕豆上市,我母亲最喜欢吃,家里总是天天几斤几斤的买,最朴实原始的烧法就是烧葱油蚕豆,除当小菜外,我们放学回来每人盛一小碗空口吃。
开始上市的蚕豆极嫰,还带点涩,清香甘甜,慢慢开始変老,需吐皮。蚕豆季节较短,所以家里常抓紧时机放开肚子吃。到后来蚕豆荚出现皱纹变色,就剥豆板,葱烧豆板酥、炒豆板、虾米豆板汤,又是另一种风味,同样鲜美。
储存的硬蚕豆到夏天用水浸泡剥壳加咸菜,烧咸菜豆板汤,淋上麻油,鲜中带点酸,是夏天清爽开胃的一道家常汤菜,几乎天天吃不厌。
端午节前,家家户户就忙着包粽子了,母亲、家佣及几个亲友一起围着边聊边包,有肉粽、赤豆粽、枣子粽、白米粽,全用糯米。
肉粽是隔天先用酱油拌透淘净的米,同时五花肉在酱油里浸透,买了新鲜的粽箬,先将一部分米放入,再放两块肉塞紧,然后再洒上米包上,用稻草绳扎好,我们则在旁边观看。
然后分批上灶头大鑊内用柴火烧煮,随着蒸气越来越多地冒出,香味也迷漫整个灶间,我们守着灶头等待着出锅,出锅后迫不及待地要紧先尝鲜,那个鲜劲真是无法形容,如今的什么蛋黄火腿粽、鲜肉豆板粽、菌菇咸肉粽、瑶柱火腿粽等花里花哨的各种粽子,都无法与那时自己包的纯粹的肉粽比。
仔细想想也是,那时用的是农家黑毛猪,纯黄豆传统工艺酿造的酱油,地产的糯米,新鲜的粽箬,这些精品汇合一起,怎能不让人断魂?
那刚出锅的新鲜滾烫的肉粽,一只实在不过瘾,但大人只允许每人吃一只!分送一些邻居和亲友后,剩下的放起来慢慢当早餐、点心吃。不少学生就带粽子到学校作中饭。
端午节那天,除了吃粽子外,一家还团聚一起弄些菜喝点酒,记得一次吃清蒸鲥鱼,鱼肚子内塞了火腿片,我第一次知道了鲥鱼是不刮鳞的,因为鳞片很肥,是精华。别人大快朵颐、吃得津津有味,惟有我怕腥只吃鱼肚中的火腿。那时吃鲥鱼也算不上什么奢侈,然而现在竟然成了稀罕珍品!
端午节后,许多家庭也开始着手做酱了,先蒸酱黄糕,切成小块,我们往往蒸好后也吃上几块,又甜又松软。
然后让它发霉,再放入酱缸内晒(晒前加什么料不知道了),只记得逐渐变稠,每天用木勺搅动,晚上用盖盖上,最要当心的是一阵雷雨过来,需急忙盖起来防雨淋,待太阳出来再开盖晒,日久月晒就成浓浓的甜酱了,中间还可放入生瓜、生姜等,就成了酱瓜、酱生姜。
自制的酱及酱瓜似乎比店里买的要好吃,我们放学回来常用手指捞一点偷吃。
这个时候还有一种鱼,叫塘里鱼。个头短小,头大且扁,嘴巴肥大,鱼身黑色细圆鳞片,像黑鱼那样,两鼓鳃突出,这是肉头最好的两块面颊。
家里常加咸菜红烧或炖蛋,后来母亲从上海学得将鱼尾弯过来塞进鱼嘴成一团,放油中炸,再放入熬过的酱油糖葱姜料中浸泡,就成了葱煎塘里鱼,外酥里嫩,葱香鲜甜,是很好的喝酒佐菜。
有一个问题至今还未弄清,小时候也常听大人说土婆鱼炖蛋、红烧土婆鱼等,不知土婆鱼是否就是塘里鱼?还有银鱼炒蛋,另有说“烩搜炒蛋”,不知是不是一回事?(常熟土话对外地人真会感到莫名其妙!)
此时,黄鱼也大量上市,街头巷尾到处可听到挑担卖黄鱼的叫卖声。黄鱼十分新鲜,鱼身发黄发亮,鱼鳃鲜红,肉有弹性。
好像是二毛钱一斤,如果成担买还要便宜。许多家庭都成担成担地买,除马上吃的外,大部分去除鱼鳃和内脏,洗净,用盐腌,数天后,两条两条地将尾巴扎牢,倒挂在竹竿上晾晒(那时各家基本上都有晒场),晒干后收起来可一直吃到来年春天。特别在大热天,拿几条出来蒸蒸,既清爽又咸鲜,非常下饭。
在鱼中,我只喜欢吃的是黄鱼和带鱼,因为这些鱼,刺少且粗,肉头硬(黄鱼是蒜瓣肉),再加上在上海外婆家经常吃糖醋黄鱼及糖醋带鱼,他们烧得非常好吃。
进入六月份梅雨季节,河虾也多起来了,且是籽虾,价钱很便宜,我们也常买来吃,祖母及母亲将籽虾中的虾籽洗下来加酱油蒸,就成了新鲜虾籽酱油,拌面、蒸水豆腐、炖蛋都是很好的佐料。
吃过几次酒炝虾,那是必须要用十分新鲜的活虾,端上桌,虾还活蹦乱跳,通体透明,虾肉Q弹,带有甜味,酒香浓郁。
有的人家买了很多虾,焯虾干,以后拿出来配菜或当小孩零食。
那时还有一种叫糠虾,像虾皮那么大小的小虾,非常便宜,买回来后洗净与鸡蛋调和一起炖,非常鲜美。
这时宝岩的杨梅也成熟了,常熟人成群结队去看杨梅,游宝岩寺,顺便带些回来。
宝岩杨梅一般偏红,果实较小,但汁水不少,甜酸中带点鲜,也是常熟一大土特产。
七月份开始放暑假,七八月份也是最热的天,清早我们常跟着母亲去菜市场买小菜(母亲是教师,所以也有寒暑假)。
离家最近的是在家斜对面一个空场内的小集市(后来这片空场成了县政府第二招待所,简称“二招“),较大一点的在西门大街书院弄口往东的一段,最大最热闹的是老县场菜场,大致是县西街、县东街、县南街、現京门电影院四叉路口周围。
那时的所谓菜市场,实际就是像北方集镇上的集市那样,各个个体摊贩排列在马路两侧,有的搭一小摊位,有的是地摊,也有的挎了篮、拎了农副产品流动兜售。他们大部分是周边的农民及渔民,挑着自己种植的蔬菜,自己捕捞的鱼腥虾蟹,拎着自己放养的鸡鸭鹅,自家鸡鸭孵化的蛋,上城出售。
这些农副产品新鲜、原生、无公害。蔬菜都是水淋淋的,十分有精神;鱼虾活蹦乱跳;鸡冠鲜红、鸡毛光润、眼睛明亮。也有不少卖松树蕈的,都是虞山山民自己挖的,也很便宜,母亲买回后加菜油熬蕈油,以后吃面、烧豆腐等等,口味都是绝佳,松树蕈吃口有点带脆,奇鲜无比,是常熟虞山名特产,母亲毎次去上海都要前一两天去市场买新鲜的松树蕈带去。
这些集市只做一个早市,落市前贱卖收摊,九、十点钟结束,所以早上是小菜场、茶馆、点心店的天下。
那时没有什么城管,自然形成集市,快落市时,负责扫马路的清洁工就抡着江北扫帚打扫垃圾,装车拉走,一切恢复街道原样。
这个季节卖田鸡及小蟹的特别多,田鸡就是青蛙,他们将几只青蛙的后腿用铅丝穿在一起,这些青蛙都是活蹦乱跳的,买时不称斤两,就按这一串一串买,价格依青蛙大小不等而不同,都是老百姓寻常价,买好帮你剪头剥皮。我们一般是加点毛豆子红烧或者烧汤,肉质细嫰,其味鲜美。烧汤的话,肉白鲜香、汤汁清澈,夏天吃很清爽。
有一段时期,大概禁捕青蛙,市面上无田鸡可买,代之于卖癞蛤蟆,开始大家不敢买,因为那一身癞皮实在恐怖,再加听说身上有毒,后有买过的人说,不碍事,剥了皮与田鸡一样吃,我们也买点尝试,的确味道也还可以,就是肉头粗一点、肉色有点青紫,比田鸡少鲜点,宜加辣椒红烧。
小蟹,农民则是将蟹一只只用稻草绳系成一串,毎串五六只、七八只不等,大小均匀搭配,他们一串串放在地上卖。流动的则臂挽竹篮,篮中放一批,双手拎了好几串在人群中穿卖,价钱按大小、数量不同而不同,但非常便宜,一两角左右一串。
母亲告诉我们要挑乌锈的,即肚脐腿脚有黑锈斑的,蟹黄及肉较结实。买回后对半剖开,蟹黄还比较饱满,一般烧油酱蟹或面拖蟹,加点毛豆子颜色更好看,味道更鲜美。这种蟹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六月黄”。
祖母在世时,由于常吃素,所以她常做“炖豆腐”,做法非常简单,在豆腐中放入盐,少许味之素,搅碎拌和,浇上菜籽油,洒上葱花,大饭鑊上蒸即可,端出时热气腾腾,白色的豆腐周边一圈金黄色的菜油,上面绿色的点点葱花,又好看、油又香,吃口肥嫰。
以致于离家多年在西安工作的大哥回来,说最想吃的是炖豆腐。炖豆腐的灵魂,一是细嫩的豆腐、二是清香的菜油、三是大锅的鑊气,但如今已较难全面达到这样的标准了。
暑期中,家门口的会元坊,不时听到卖吃食的叫卖声,早上有糕团、大饼油条粢饭糕。
十点左右叫卖:“鸡笃面筋、肠脏肚子肉!”是连汤带菜的,白汤鲜美浓郁,家里夏天怕烧,往往买一些再加点水和辅料,就可作中餐的汤菜。
下午有卖糖粥、汆臭豆腐干的,还有,时不时的卖西瓜、卖棒冰、卖“唤”的等等,大大方便了居民。
那时家家户户都在灶头上用稻柴火、大饭鑊烧饭,吃起来更香,且每锅饭底下都会留下一大张锅巴(常熟人叫“饭滞”),这是大家都嫌弃的东西,因为较硬且粘牙,有时最后一个人盛饭,饭不够了,只好将饭滞也刮点下来用汤泡软对付着。
一般是吃过饭后,将饭滞铲下,放下一顿泡粥,这样的饭滞粥有股焦香味,夏天吃,开胃清爽,又利于消化。
有时家里有人感冒发烧或者拉肚子,沒有胃口,就特意关照,锅巴多烧焦些,变“枯滞饭”,这样泡粥后更利于消化,或者干脆给病人喝“枯滞(粥)汤”,这也是一种民间土方。
想不到如今锅巴已成受宠之食,与其它食物搭配烹煮为顾客喜欢的菜品。想想也是,如今都用电饭煲煮饭,哪还有什么又香又脆的锅巴?真是“物以稀为贵”!
夏天晚上,太阳落山后稍凉快些,情窦初开的年轻人结伴逛街,一方面出来放松放松,另一方面互相窥视异性,试探交流。
老县场县南街口是最热闹的地方,小贩也抓住商机,这时你能看到有不少树了一大捆芦粟的商贩,常熟人把芦粟叫芦穄,是类似于甘蔗的植物,但芦荠细而长,呈青蓝色,虽没有甘蔗那么甜、汁水那么多,但较清香,且因细,易于咀嚼。
价钱也很便宜,二分钱可买一长根。买后折断成数小段夹在胳肢窝里,一段段慢慢吃。次晨清早往往看到,马路上隔夜的芦穄皮丢落一地。
九月开学,不久就是中秋节了,家家都准备祭月。茶食店门口现熯现卖鲜肉月饼、肉饺(与月饼类似,但是短长条形,如今已不见),店堂内卖苏式甜月饼,广州食品店则有各色广式月饼。
城内到处都能闻到桂花香,大量的鲜果、山货也下来了,常熟街头可以看到许多挑担卖虞山毛栗子的,都是带毛刺的果实,以示新鲜。现买现用蒲鞋帮你踩开,虞山的栗子外壳白色,栗子肉,色泽金黄、桂花香浓、吃口细嫰、含水量足。
生吃熟吃均宜,生吃脆嫰甜润;熟吃甜糯桂香,山景园等大菜馆就以虞山栗子为料制作出栗子烧鸡、栗子烧肉、桂花栗子羹等菜肴甜羹。街上买的糖炒栗子大都是外地产的褐壳栗子,以天津良乡栗子为最佳。许多家庭小店则摆摊桌卖桂花糖烧芋艿。
街头巷尾还有许多背着笆斗叫卖紫熟菱的,是常熟各池塘采的菱角煮熟而成,又糯又甜,是人人喜爱的零食,记得好像八分钱一斤,我们经常买半斤放口袋内慢慢吃。
这个时候前后,玉米(常熟人叫雨麦)也收获了,常熟的玉米因吃口甜糯而有名,有白色的、黄色的、白的和紫红色夹杂在一起的,而以白色和黄色的为更好,白的一般较嫰,水份含量多,而黄色的软硬适中,既糯且有嚼劲。
常熟雨麦以北门外几个乡产的雨麦为最好,大都为金黄色的,玉米粒排列紧密整齐,粒粒油亮。烧煮后香味四溢,一口气可以连吃几蒲(常熟人把一个玉米棒叫一蒲雨麦),玉米粒啃光后还要咀嚼吸取棒渣中的甜汁,再喝煮玉米的汤才肯罢休。
由于玉米粒像粒粒珍珠,所以上海人叫珍珠米。上海二表姐最喜欢吃常熟雨麦,母亲这个季节去上海,总会托人买好北门雨麦带去。
秋天也是收获毛豆的时候,这时城里到处都见卖毛豆的农民,常熟毛豆有一种品种叫“牛踏扁”,毛豆米寬大扁平,似被牛踏过一样,色泽青綠,煮熟后鲜糯清香,为毛豆中佼佼者。
毛豆大量上市时,有的人家买一麻袋,加盐焯熟晒干,叫毛豆荚干,放起来,大人小孩当零食慢慢吃。客人来了泡一杯茶,抓一把毛豆荚干,不失为一种礼貌招待。如带小孩来,临走时捧一把装孩子口袋,以示喜欢。
还有的做熏青豆,如今在方塔前的塔弄内还有好几家店卖这一常熟特产。
农历九月九是重阳节,街上糕团摊就买五颜六色的重阳糕,每块糕上还插上一面小旗。
秋风起,蟹脚痒,十一月份是吃大闸蟹的最好季节,家家都抓紧这一时机尝鲜,大人小孩围坐在八仙桌上有说有笑,一边掰蟹脚吃,一边聊愉快事,其乐融融。
由于那时吃蟹也是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件普通事,所以,不少人家一次多买点,剔蟹黄、出蟹肉、炒蟹粉、熬蟹油,储存起来吃。饭馆面店也推出炒蟹粉、虾仁蟹粉、蟹粉豆腐、蟹粉蹄筋、蟹粉面等等时新品种。
冬天,街头就飘出烘山芋和汤山芋的香味了,烘山芋摊主都是外地人,买一只捧在手里滾烫焦香,连皮带芯吃下又暖又饱。
另外,一些本地家庭也做做小生意,用木板搭个小摊、几条长凳,卖汤山芋。一大锅用红糖烧的汤山芋,再洒点桂花,很是香甜(但常熟人有时讲话恶作剧,把大粪缸内浮在上面的粪便叫“吞汤山芋”)。
我们省中读书时,在书院弄与小山台口,就有一家。早上上学时路过,买一小碗汤山芋吃吃,只需两分钱,热吹铺烫的两大块黄红色的山芋浸在红糖色山芋汤内,既好看又好吃,一碗下去浑身暖彤彤。
冬天,小时候有时馋,不怕冷用两只冻红的小手剥生荸荠吃,又甜又脆。有的人家烧煮一下,常熟人叫“闸熟荸荠”,也很好吃,脆中带糯,街上也有得买。还有的买后风干,为风干荸荠,皮发皱,易剥,虽水份较少,但吃口更甜,是孩子喜欢吃的零食。
冬天没有紫熟菱了,但有一种叫乌菱的,又黑又硬又大,两只弯弯的菱角像非洲野牛的两只牛角,又粗又尖。这种菱根本咬不动,一般将它煮熟切开剥壳,不过菱肉极糯,它也是给灶王爷的祭品,是否象征着用牛头去祭,就不得而知了。
转眼就放寒假,这时离过年就很近了,家家户户就都忙于购置年货、烹煎烧炖。走到大街上可以看到头戴罗宋帽、身穿棉袍、脚穿蚌壳棉鞋的行人拎了大大小小的纸包,行色匆匆地赶回家。
小街巷内冒出蒸气的灶间,女人们在忙这忙那,孩童们则在空场、街边打棱角、踢键子、跳绳,摔炮等玩耍,年味浓浓,一幅丰子恺画笔下的过年景象。
我们家也像其他家庭一样,母亲汆走油肉,家佣烧柴火。这是一项需要技术又危险的工作,因为炸煮中油易爆出溅到脸上烫伤,但又要掌握火候及开闭鑊盖的时间,既不能未汆够,又不能汆焦。一方块一方块金黄色的走油肉汆好,一一放入家里老祖宗传下来的金边大盆子内。
又按传统方法做爆鱼,这边姐姐帮摊蛋饺,佣人杀鸡开肚清洗,女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则在旁边看,也因此,成家后,过年菜基本上都由我准备及操作。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牵糯米粉蒸糕,将牵好的粉拿到店里请他们代蒸。一直忙到大除夕,一家围坐在桌子上吃年夜饭,冷盆、热炒、大菜,十分丰富,最受大家欢迎最热闹的就是暖锅了。
祖母、父亲、大哥、二哥喝点黄酒,我们则咪一点老白酒(甜米酒),一家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年夜饭吃过,大家就围在一起搓元子,切糕丁,以年初一早上吃,因为年初一禁动刀、禁扫地。
年初一,小辈向长辈拜年,长辈给小辈压岁钱,吃过团圆糕后,按惯例,一家去已去世的前母(大哥、大姐、二哥的生母)家去拜年,他们住在丰乐桥缪家湾。
上午我们几个小的,先去外婆——庞家好婆处拜年,她给我们每人一份压岁钱,並在那里吃中饭。
下午去几个舅舅舅妈处,他们带我们去坛上、大田岸、小庙场玩,晚上就在舅舅们家里吃饭,开了好多桌,菜肴丰富,非常热闹。
虽然平时胃口很好,似乎永远吃不饱,但一到新年,一吃就饱,所以人们常说“年饱,年饱!”大概是因嘴巴不停地吃点心零食,再加上新年菜肴丰富、油水足的缘故。
年初二开始又亲戚间相互聚会,不停地“吃,吃,吃”“玩,玩,玩”,所以小孩是最盼望过年。
新年店舖几乎都关门停业,但街上人流不息,逛街的或探亲访友的,老县场是最热闹的地方,流动杂技团、猢狲出把戏、套泥娃、看西洋景等占据了广场的各块空地。
乡下上来的农民拎了竹篮卖自制的咸草头、黄莲头、甜脆梅、熏青豆、毛豆荚干、风干荸荠等。
咸草头非常鲜,黄莲头则开头有点发苦发酸,但嚼后慢慢觉得甘甜清爽,真是“苦尽甘来”,这两种小吃在“饱新年”中是清口解腻的最好零食。
在老县场周围还有许多临时的小吃摊,如:豆腐花、油片细粉汤、鸭血粉丝汤、汆鱿鱼、汆春饼等等,春饼实际上就是春卷,春卷皮内包了韭黄肉丝或白菜肉丝在油中汆。
但常熟的“春卷”与其他地方的不同,它的春卷皮大,包的形状也不是那种短圆柱形卷状,而是长而扁,似一条条朝板的饼状,所以叫常熟人叫“春饼”。
这样在平底油锅内接触面大且均匀,容易熟。汆好后平摊在漏槽上滤油,买几条后,每条切成几段装盆,淋上鲜酱油,喜欢吃辣的加点辣花酱,刚汆出来吃特别香脆鲜美。
以上列举的小时候的吃食只是一部分,很可能还有不少遺漏,只好请各位“老常熟”补充修正了。
尽管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大不如现在,但却能吃遍现在为珍稀高档的食物,尝到現在尝不到的真味实料,还能吃到現在根本吃不到的东西,所以怎能不让人怀念“小时候的味道”?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吴文化第一山——常熟虞山
作者介绍:黄仁彬,1940年生,1946年2月-1951年7月在常熟石梅小学读书,1957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常熟中学,1961年7月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1980年底调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先后任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1988年评为副教授,任教期间主讲了数学分析、复变函数、拓扑学等14门课程,作为主持人之一完成了数学分析课程建设,並荣获江苏省Ⅱ类优秀课程。1993年获首批全国高师院校曾宪梓基金会教学三等奖。多次参加全国性专业会议並大会发言,1993年参加一般拓扑学国际会议並在分会场上作报告,发表多篇论文。曾任苏州市数学会常务理事(高教组负责人)、苏州市教育学会中学数学分会副理事长。2001年退休。现旅居海外。
留言功能现已开通,页面底端可见“写留言”入口~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