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曾说过一句让无数美术生’破防’的话:
‘我14岁的时候,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但却花了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像小孩子一样作画。’
巴勃罗·毕加索
看到这句话,多少人心里不是滋味;这到底是天才的炫耀,还是艺术路上最深刻的顿悟?
如果毕加索活在今天,他14岁的画作早已刷爆全网,成为’神童’代名词。
那个少年笔下的《最初的圣餐》《科学与慈善》,光影精准、人物传神,笔触老练到仿佛已与画笔共舞数十年。
当时的画坛前辈们频频点头:’这孩子,前途无量!’
最初的圣餐
科学与慈善
他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名望,地位唾手可得,但毕加索偏不。
他像个任性的顽主,在艺术这个无限游戏里,主动关掉了’写实’这个最强脚本。
于是…画风突变!
1907年《亚威农少女》登场,人物棱角分明、面容扭曲,仿佛被几何图形撕裂重组。
当时观众们的表情大概和今天普通人看到抽象画一样:
‘这…也算艺术?我孩子也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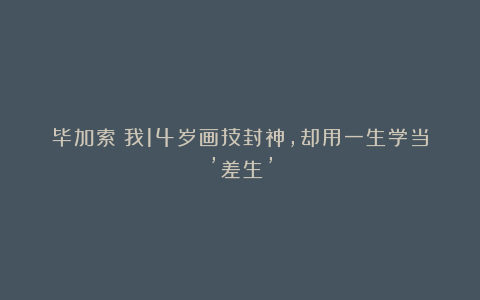
亚威农少女
毕加索为何要’自废武功’?
真相是:他并非不会写实,而是不屑复制现实。他拆碎表象,把眼睛、鼻子、身体打乱重组,像孩子般大胆拼贴。
正面脸孔上嵌着侧面眼睛,后背曲线扭转到胸前。有人戏称,他画的是’三维立体拆解说明书’。
他晚期的《公牛》系列创作过程堪称’艺术瘦身’:从一头筋肉扎实的写实公牛,一步步简化,最终仅用十一根线就勾勒出雄壮魂魄。
↓
所谓大师,不是做加法堆砌繁复,而是做减法直击灵魂。
当技巧登峰造极,真诚反而成了最难抵达的境界。
毕加索不是穿越者,却完成了艺术史上最惊人的’逆生长’。他挣脱了’画得像’的枷锁,向孩童借来勇气与好奇,在画布上重建艺术规则。
下次再看到抽象艺术,别急着说’看不懂’或’我也会’。那背后或许是艺术家如孩童般执拗的探索;笨拙的涂抹之下,藏着他们重新理解世界的灼热目光。
或许毕加索最羡慕的人,是你家隔壁那位握蜡笔的小邻居:线条歪扭却自由,颜色大胆且无畏。
真正的返璞归真,是阅尽千帆后,仍有勇气重新笨拙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