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当代敦煌”蓝字关注我们哦,更多精彩!
以前莫高窟的孩子们是如何上学的
文 / 孙儒僩
说起几十年前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子弟受教育的问题,我心里会感觉到难堪与内疚。上世纪四十年代常书鸿先生携带两个子女来到这个荒凉的莫高窟艰苦创业,女儿常沙娜初到莫高窟大概有十三、四岁,儿子常嘉陵大概只有四、五岁。身居莫高窟没有办法上学,后来女儿常沙娜就寄居在敦煌县城的一户人家里,在县城上小学。后来又到酒泉住校上初中。儿子常嘉陵太小没有办法上学。到了解放以后,莫高窟职工人数逐渐增加,有的结婚成家,有了孩子 ;有的职工从北京等地调来莫高窟,同时也把他们未成年的孩子随同一起带来。解决职工孩子上学的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十年代常书鸿和女儿、儿子在莫高窟
回忆当时的情况:史苇湘、欧阳琳是1950年在莫高窟成婚,同年结婚的还有窦占彪。1951年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干部高瑞生夫妇调来莫高窟,带来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大的只有两、三岁;1951年霍熙亮的夫人在因抗战离散多年之后来到莫高窟团聚;我和李其琼1952年在莫高窟成家;1954年李贞伯、万庚育从北京调来,他们有三个小孩,最小的一个才二、三岁。1955年前后孙纪元、冯仲年的家属也相继来了;在莫高窟成家的职工也相继有了子女,一时间莫高窟人丁兴旺。本来比较孤寂荒凉的环境,有了一群儿童,有了娃娃们哭闹和嬉笑声音,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欢乐。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孩子们逐渐成长,家长们又在上班,所里组织一些家属办起了幼儿园,一间房子几个小凳子。我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食物短缺,孩子们营养不足,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呆呆地坐在小凳子上,没有一点精神玩耍。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这些小孩大的已经有十来岁了,小的也有六、七岁了,摆在职工们面前的直接问题就是孩子们受教育的难题,孩子是家长的希望,大家虽然焦急,但是莫高窟远离城镇、交通困难、没有教师,小孩子们的受教育问题一直难于解决。
大概到了1958的时候,所里才请了段文杰的夫人龙时英老师在莫高窟办起了小学班。因为孩子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刚开始办起的是一二年级的复式班,在同一间教室里,她一会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布置作业,一会又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课。开始只有五六个孩子,以后逐渐增加到了十多个。也有了应该上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龙老师一个人再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教四个年级的课,有几个孩子就到敦煌县城去住校,读五、六年级或上中学了。在1962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所里在敦煌县城的东街上租了一个院子,有三间平房、三间厢房。孩子们住在这个院子里,到就近的学校去上学。院子里还开了个学生灶,请了位妇女给孩子们做饭,由龙老师负责照管孩子们日常生活和监督学习。后来又换了林桂心老师来管理。
敦煌文物研究所托儿所儿童节聚餐-1956年6月1日
1964年以后所里有了一部改装的轿车,在那段时期里,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所里的汽车把孩子们接回来。一回到家,家长们就忙着为孩子们做点吃的,然后洗澡、换衣服。星期日中午吃过饭,下午又送他们回到敦煌城。要是遇到所里的汽车出了故障,孩子们往往半个月都回不了家。在那时,孩子们集体住宿在两个大炕上,互相会传染上一身的虱子,特别是在冬天,毛衣和棉衣上有了这种寄生虫非常麻烦,虱子和虫卵是捉不干净的,最好的办法是用开水烫,但第二天衣服干不了,又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替换。我们只得用点666农药粉涂抹在毛衣、棉衣上,再放在室外冻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怕孩子穿了抹有农药的衣服会中毒,就用力拍打衣服后再让他们穿上,但下一个星期回来,身上依然如故地带着满身的虱子,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后来,家里孩子多的职工家属,就干脆到敦煌城租房子住下,这样既可以照顾学生的生活,也可以方便他们上学。我也曾经把我的一个女儿寄宿在霍大嫂家上学,后来上高小就住在学校里了。因为敦煌县当时人口不多,住校学生很少,我女儿就在学校老师的食堂搭伙。在学校上完课,有时要参加劳动或打扫卫生,之后再去食堂吃饭时饭菜都凉了,特别是在冬天吃有羊肉的汤菜,羊油凝固了,吃下去胃里很难受,从此就再不吃羊肉了。我的小儿子也是要住校,那时他才六岁。有一次是冬天的星期六,他没有回家,说是老师要娃娃留下有事,晚上娃娃自己一个人在宿舍生火,柴火爆出的火星飞溅到炕上的被褥上,娃娃没有发现,慢慢地被褥燃烧起来了,好在他及时拿脸盆打水把火给浇灭了,避免了一场火灾。可是被烧毁的被褥是别的同学的,只得由我们赔偿了。
敦煌文物研究所儿童“六一”演出-1959年6月1日
子女们在城里上学,每星期回来一次,一回来我们就忙着为他们洗衣、做饭,根本没有时间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在六十年代,我在管理洞窟的加固工程,我的爱人李其琼为了做纪念莫高窟建窟1600年的临摹工作从而十分繁忙,经常加班加点,真有顾此失彼之感,对子女的学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关心,虽然感到内疚,但是也无可挽回。
到文革期间我们的大女儿刚初中毕业,就要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期间,各级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二女儿小学毕业后也无法继续升入初中上学,小儿子还在上小学。因为我们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被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农村后接受劳动改造,三个子女也随我们一齐下到了农村,这是我家的情况。实际上当时研究所职工的子女,特别是四、五十年代职工的子女都没有受到较好的学校教育。我们下到农村以后,老大和老二成为了家里主要的劳动力,承担了挣工分养活一家人的任务。那时小儿子不到劳动的年龄,要小儿子继续去上学,可是他死活不去,我们夫妇反复劝说甚至打骂,他就是不去,还说:“你们上了学,又怎么样了,还不是要回到农村种地,我放牛去!”后来经过多次劝说,终于还是去了学校。但是在文革期间,当地农村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就得在家帮助大人做点家务,或是为生产队放牛、拾粪来换点工分,所以学到的知识少的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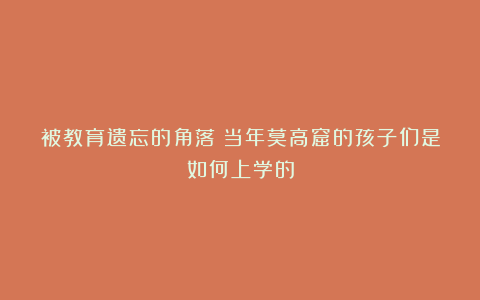
1972年落实政策,我们携带三个子女又回到莫高窟,当时所里正在招工,但招工是根据有关部门安排的,自己单位的子女也不让招。于是老大、老二又去上学,下乡前老二连初中都没有上过,为了让她有点基础,我就现炒现卖,在家里教她英语的26个字母的读和写、初中数学有理数等简单的知识。1973年出来个“白卷先生”张铁生,就打乱了全国的教育,学生成了以“学工学农”为主,而学习文化知识倒成了次要的,一个学期终了,他们的课本没摸过几次,书本都是新的。那时候,学校冬天学生取暖的煤砖是学生拓的,学校农场的房子是学生参与修建的,秋天学生们要去农村帮农民平田整地、拾棉花。儿子的班上还为电信部门挖了埋电缆的沟,学校收到的每米五毛钱的挖沟费用也不知去处。1975年,老大、老二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就高中毕业了。虽然她们已经下过近四年农村,但根据当时的政策,还是得再次下乡,否则以后就不能招工,只能又第二次下乡了。
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小学毕业班合影(后排中间为龙时英、左为李承仙)-1963年9月12日
我不是为我的子女诉苦,因为四、五十年代或是后来从别的地方调来研究所职工子女的情况大体相似。有几家职工夫妇都是本科出身,后来都是高知,可是儿子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被强令下乡插队去了,后来也没有再进学校学习的机会。与此相似的职工子女还有不少,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年代里,研究所职工的子女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本科的,少数能上中专、大专的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外地调来的职工,子女因各种原因滞留在莫高窟不能到敦煌县城上学。于是在莫高窟又由一位职工家属开办了一个小学班,没有老师就让所里的职工担任。万庚育有时调去教语文课,我也曾去给他们上过数学课。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拨了一笔基建经费,才在敦煌县城东门外要了一块地皮,连续修了两栋宿舍楼,把有子女的年轻职工迁居到县城,让他们的子女可以就近上学。职工每天有通勤车往返莫高窟上下班,改善了职工生活,解决了子女上学的难题。老职工的子女虽然在上学问题上遇到困难。后来通过自我努力,也能勉强自谋生路。
上述子女的受教育的问题,我只能简单作些回忆,这一篇短文还是我二女儿孙晓华补充整理的。最后我和孩子们深切怀念龙老师,是她的辛勤耐心的劳动,使我们的一群孩子受到初步教育,为他们后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抚今追夕,社会的发展,敦煌研究院的巨大变化,职工们生活的改善,子女受教育的困惑已结不是问题了。我为现在的职工和他们的子女感到庆幸,我也觉得欣慰。
写于2016年2月、2017年11月14日修改
孙儒僩 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间,曾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等古建筑研究基础工作。上世纪50年代,参与多次石窟考察,并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等。
本期编辑: 远近 水中天
品读之后
愿享同感
– END –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