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盛泽,总要到附近的保盛桥走一走,因为那里留驻了我太多的岁月记忆。
从我家出门向东十来米处,是保盛桥弄的南口,顺着弄堂往北走,大约五十来米,就是南北走向的保盛桥。从解放初的盛泽镇地图可以看到,从西白漾横贯镇区、向东奔来的市河水,在经过开源、永安、善家、登椿、龄家、东庙等六座桥后,从保盛桥下流入五水会聚的东白漾。因此,保盛桥上有“五聚潆洄资保障,六桥锁钥庆安澜”的桥联。
保盛桥弄(作者提供)
解放初盛泽镇局部地图
史料记载,保盛桥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87),嘉庆二十三年(1818)重建,单跨石梁,花岗石构筑,桥长27米,宽2.7米,跨度5.3米。1926年盛泽遭特大龙卷风,桥面及栏杆损坏,后修复为水泥磨石子桥面、水泥栏杆。如今,历经近百年的日晒雨淋、风吹露涤,桥面变得粗糙,露出混凝土中的石子颗粒,桥坡护墙与栏杆之间出现了裂缝,部分桥栏杆甚至露出了锈迹斑斑的钢筋,静卧在河面之上。桥下河水很浅,河道有一半种着水生美人蕉,已无法行船,也很少有行人登桥过河。
特大龙卷风毁坏保盛桥桥面
可是,在我儿时及年少时的记忆中,保盛桥没有这样苍老、荒寂,保盛桥两岸呈现的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桥畔场景,这从盛泽画家庄子明先生创作的与保盛桥有关的两幅画可以看出,其中“保盛桥景”似乎是从桥的东南方向视角画的,而“东漾划船”描绘的则是从保盛桥方向朝东望去的景色。
保盛桥景(庄子明作)
东漾划船(庄子明作)
在我的记忆中,有更多的保盛桥畔人们的日常生活画面。每天早晨,唤醒保盛桥的可能是位于桥北先蚕祠西侧新民丝织厂上早班女工的匆匆脚步,她们须得赶在凌晨4点前到达工作岗位。4点过后,当刚上完夜班(晚8点到晨4点)、家住山塘街一带的新民厂女工们拖着疲惫步伐过桥回家后,保盛桥附近进入短暂的沉静时刻。稍后,打破保盛桥附近宁静的,可能是“倒粪工”和“接粪船”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蚕祠与西侧的新民丝织厂办公大楼
那个时候,小镇居民家家户户都使用马桶,每隔一、两天,必须把马桶内的粪便倒掉并对马桶进行清洗。当然,粪便不能随意倾倒,小镇有个卫管会,它每天安排职工挨家挨户去“倒马桶”。与“倒粪工”配合的,是一早停靠在保盛桥堍的“接粪船”,这是附近农村生产队按镇卫管会安排而来“接粪”的。接粪船上一般有两个农民,船在桥堍旁停靠好后,农民挑着粪桶跟在“倒粪工”后面。倒粪工把附近居民家马桶里的粪便倒入农民挑的粪桶里。当一担粪桶满了,一个挑空桶的农民接上去跟在“倒粪工”后面,另一个农民把粪担挑到船上、倒入船舱,然后再回去跟在“倒粪工”后面,等下一个轮回,直到“倒粪工”负责范围内居民户的马桶全部倒好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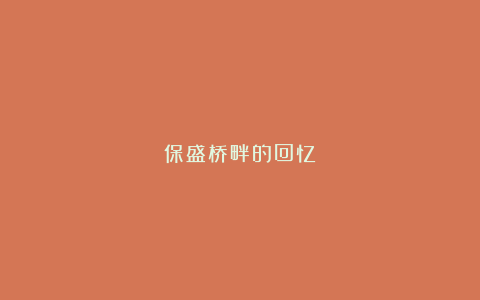
倒马桶
“倒粪”与“接粪”工作通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进行,绝大多数居民都还没有起床。有的人家隔夜把需要清倒的马桶放在门外,“倒粪工”倾倒后会用清水帮助进行粗略洗刷;有的人家(如我们家)缺少替换的马桶,隔夜就不关门,“倒粪工”会轻轻地开门入户并报一声“倒马桶”后,进入房间取走马桶(拎或端,取决于马桶是否有拎环),并不影响大家睡觉。这大概可以称为是“夜不闭户”。当人们纷纷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生活的时候,“倒粪工”已经收工,“接粪船”也已离开保盛桥。满船载回生产队的大粪经过发酵以后将是庄稼的上等有机肥料。我插队时,曾当过一回生产队“接粪船”上的挑粪人,不过那次的船不是停在保盛桥,而是停在保盛桥沿市河溯流二百来米的东庙桥边,那是古镇当时商业繁华之所,挑粪时已经能碰到早市人员,其中还有认识我的,一声“你是寅初吗?哎呀!你晒黑了!瘦了!快认不出你了!”,至今还能清楚记得。
“呜……!”一声汽笛长鸣声在东白漾上空回响,那是停泊在保盛桥畔来往于盛泽和嘉兴间的客轮准备离开码头的信号。那个时候,如果要去大一点的城市去购物、看病或游玩,盛泽人首选的地方多半是嘉兴。虽然行政关系上两地不属于同一个省,但地理关系上距离很近,仅相隔18公里。记得上中学时,每次学校组织“远足”(春游或秋游),我们都是早晨从盛泽出发,步行36里路到嘉兴,然后再凭双脚在嘉兴市里逛建国路,到火车站看火车,到南湖去参观烟雨楼。直到下午时分精疲力尽,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到达离火车站不远的轮船码头,乘轮船约两个多小时后,于傍晚时分回到保盛桥畔。从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启航,每天一班往返于嘉兴与盛泽之间的这个客轮,随着公路客运的发展,大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盛泽轮船码头(凌淦群绘)
当年驶过保盛桥或停靠在保盛桥畔的船舶,从船的造型看,有“本地船”和“绍兴船”,本地船船体相对圆浑,船头窄而翘,而“绍兴船”(不是乌篷船)船舱较长,船体显得修长,船头宽而平。从船的建造材质看,有木头做的,也有水泥做的。从船的行业归属看,有属于运输行业的,也有属于农村生产队的。运输行业的船中,船上人员大多属于同事,也有船上人员都是一个家庭的。从船的行驶动力看,多数是人力驱动——即通过摇橹、撑篙来使船前行,也有一些在船尾安装一台小型柴油机作为动力来源,俗称“挂机”,偶有船舱内安装大马力柴油机作动力的轮船(往往是船队前面的动力船),轮船一般停泊在东白漾,因为再往西行驶,便是又长又窄的市河,不适合船体较宽的轮船通行。这些船都是运送货物或材料,很少看到捕鱼的渔船,这大概是因为集体化以后渔民捕鱼后必须到指定的地方集中上交“渔获”。
在小时候看到的船中,印象很深的是稻草船。当时,附近的人家大多使用以稻草为燃料的传统大灶,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稻草供应,将面临能源困境,而稻草船则是向附近居民供应稻草的唯一渠道。所谓稻草船,是附近农民把稻草先是一捆一捆码放在船舱里,然后再一层一层得叠起来,每叠一层,稻草捆向船沿外侧伸出去一些,这样叠了很多层以后,船上的稻草堆成下面窄、上部宽的形状,且宽出船体很多,断面像倒置梯形一样,整体像小山一般,稻草船整体看上去像是在水上移动的庞然大物。这样的稻草船,船头上必须有一个人用竹篙把控船的方向,因为船尾摇橹者此时的视线完全被稻草遮挡,看不见前方。当一艘稻草船停靠在保盛桥畔,会有“柴主人”(贩售稻草的经纪人)到附近街道弄堂吆喝,听到声音且家中需要添购稻草的居民,会来到保盛桥畔,报上自家需要的稻草数量,然后船上农民把稻草一捆一捆扔到岸上,由“柴主人”作为中间人把秤、称重、计价,交款。因此,稻草船实在是保盛桥附近居民的流动能源供应站,它与两岸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后来,随着煤球炉的普及,烧稻草的大灶被逐渐淘汰,稻草船也慢慢从保盛桥畔消失。
在保盛桥畔,有来来往往、东来西去的船,也有附近孩子们夏日游泳的好去处。在桥堍西南角,当时有一处可容四、五人同时洗菜淘米或洗衣提水的河桥,河桥西边靠里是一栋大房子的临水北墙,墙基由从水底打桩并堆砌起来的大块条石构成(这栋房子现在还在,并且似乎是当年保盛桥畔留下的少数房子之一)。水中石头墙基旁边是一片浅滩,学习游泳的孩子们一开始双手扶着木板、木盆等有浮力的东西在那儿“扑通扑通”地用双腿打水并扭动身体。后来渐渐熟悉了水性,变成一只手扶浮板,另一手划水,双腿打水并扭动身体前行。最后学会了,那就彻底离手。孩子们没有教练,不讲究姿势,照葫芦画瓢,孩子们无论男女,通常在一个夏天内就能学会游泳。学会游泳的孩子们不再满足于浅水滩的扑腾,遂去横渡保盛桥两岸的市河。到年龄大些,体力、水性都增加时,孩子们常常横渡东白漾,从保盛桥桥基处出发,游到对面盛泽中学老虎灶附近的河桥,或者游到升明桥桥洞的石基边,休息一会再游回保盛桥。
水中的石头墙基(作者提供)
升明桥(作者提供)
现在回想,儿时在保盛桥畔游泳时有两种举动是非常危险的,一是在桥栏杆上跳水,二是用潜泳方式穿越船底。保盛桥桥面栏杆离桥下河水水面大约有两、三层楼高,不记得是哪个小伙伴“发明”的桥栏杆跳水,我们一众男孩经常挨个排着站到桥栏杆上往下跳。虽然站上栏杆时,我望着下面的河水有些害怕和犹豫,身后小伙伴加力一推,我便故作“勇敢”表演“高台”跳水。当时的跳水姿势是最简单的全身绷直,仍能记得当年“跳水”失重所带来的刺激感,它与后来乘飞机时飞机急速降低高度所带来的感觉相仿。现在想想,在桥栏杆处跳水是很危险的,因为保盛桥下的河水并不很深,记得跳下去入水后,双脚很快就触到河底,整个身体迅速反弹上冲,这说明入水的冲击力很大。如果双脚刚巧冲撞到河底稍稍尖锐些的石块或砖块,则可能对脚甚至腿带来严重的伤害。
桥上跳水
再讲讲小时候以潜泳的方式穿越船底的故事。保盛桥下的市河中船只来来往往,也不知道是哪个小伙伴首先“发明”的,我们会等船工摇着橹、船头刚行驶通过我们游泳区域的时候,从船一侧的水面一个“猛子”扎下水中,迅速潜到水底,身子贴着河底向河对面潜去,从行驶中船的另一侧浮出水面,以此显示自己的潜泳能力。这需要能在水底下潜泳足够长的时间,否则会被“闷”在船底。另一个危险是,尽管小朋友们穿越的都是人工摇橹船,不是带有螺旋桨的机动船,但这些船在水中划动的橹板,为了经久耐用,外侧都包了铁皮,如果划动的橹碰到了潜泳者,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事故。但可能因为“无知无畏”,我们对来自船工们的严厉警告采取忽视的处理方法,伙伴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也曾经好几次潜泳穿越船底。大约十年前,一次在带孙子学游泳时,我还曾“表演”从泳池的一端一口气潜泳到25米的另一端的泳技,这大概是在保盛桥畔玩船底穿越时练就的“功夫”。
孩子们在行驶的船旁游泳
保盛桥桥面不仅是孩子们的跳水跳台,也是附近大人孩子们的纳凉平台。傍晚时分,大概是夏日中一天里保盛桥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在太阳下山后,先用水泼在桥面上,等水干后在桥面上铺上草席。桥面上最多可铺六条席子,中间留一条窄窄的过道供来往行人通过。晚饭后大家坐在席子上,或是摇着芭蕉扇,或是享受着从河面掠过的习习凉风,边看着满天星斗,边讲着各式闲话或故事,没有蚊子的侵扰,直到夜深了凉快了才陆续散去。有时候天非常热,包括我们在内的几家孩子们会通宵睡在桥上,直到第二天天亮。在桥上睡通宵的时候,因为后半夜气温低,常常要盖上被单以防受凉。记得有一次,我们盖在身上的被单被人偷走了,直到天亮醒来才发现。因为我是最大的孩子,被单被偷的主要责任在我,为此挨批是当然的,此事也较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桥上往事,记得保盛桥南堍西侧边上一户我们称为“老王婶婶”的儿子叫金林,大我们好多岁,常给我们讲故事,做游戏。有一次桥上乘凉时他拿了一颗糖果给我们四、五个孩子出了一个题目“这颗糖放在你身上的什么地方,你的右手拿不到”?并用这颗糖果作为答案正确的奖励。大家纷纷在自己身上比划着、尝试着,说着不同的答案。经过一番思考和比试,最终是我胜出,获得了奖励的糖果,还得到了金林大哥和他父母此后对我的不断夸奖。这件事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是如此深刻,以致在日后的几十年里还曾先后把此游戏题目给儿子和孙女、孙子分别做过。
桥上纳凉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关于保盛桥的往事如同流水般不断涌出。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家里养了一头猪,母亲在保盛桥河桥边放一口水缸,请邻居们下河淘米时先在缸里淘一下,一天下来沉淀的米泔水就是喂猪的上好饲料。又如,一起在保盛桥河里游泳的七个男孩(桥北两个,桥南五个)到读中学年龄时,成立了一个篮球队,还曾一起合影。再如,1968年9月27日,也是在保盛桥畔,我带上被褥,登上前来接我的生产队水泥船,开始了五年的知青生活。
邻家男孩篮球队(作者提供)
如今,保盛桥东、西两边各几十米的地方都建了可以通小汽车的平桥,桥的北侧是商店林立、车水马龙的舜湖东路,只有桥的南侧通往山塘街的保盛桥弄没有什么变化。当我拾级而上、逐级而下走在显得冷清的保盛桥上,其主要目的已不是过河,而是对家乡故土往日岁月的一种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