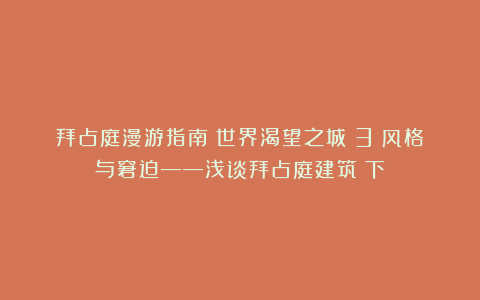本节讨论:中期帝国葬礼需求与建筑扩大-回归穹顶十字或穹顶巴西利卡平面-萎缩希腊十字平面的复兴-晚期帝国Γ型或Π型步廊-多层薄砖与多层条石镶砌-柯拉修道院的马赛克精华-奥斯曼人对拜占庭艺术的终结 子坐标集三(下): 希拉米艾哈迈德帕夏清真寺-玫 瑰 清真寺-卡兰德哈恩清真寺-帕玛卡里斯托斯修道院(从略)-柯拉修道院-费纳里伊萨清真寺
这座教堂是君士坦丁堡现存最小的拜占庭教堂,原名是穹顶前的先驱圣约翰(即施洗者圣约翰)教堂(Ἃγιος Ἰωάννης ὁ Πρόδρομος ἐν τῷ Τρούλλῳ,The Church of St. John the Forerunner by-the-Dome)。
与汽车比较,其体例极小
教堂可以追溯到12世纪,而建筑的部分证据可能可以将建造时间前推到九世纪,包括朴素未装饰的圆顶而非南瓜型穹顶或者犬牙型的檐口,以及圆形的鼓座而非多边形鼓座,前者多见于9~10世纪的行省建筑。同时建筑外立面块石与薄砖的间隔砌法,也是显著的8~10世纪的技法。建筑是最典型的中期帝国教堂结构,包括三开间前廊、9开间中厅与三个半圆室。
以上谈及的中期帝国的首都建筑在形制上大幅缩小简化,本质上是由于帝国处在黑暗时代以后的虚弱期,两线作战、国库空虚、民穷财尽 。教堂主穹顶的直径才3~4米,每个跨间的边长也只有这么点,对比圣索菲亚的正面70米的宽度,仅需要9个跨间。
即便是马其顿王朝盛期,其实也是一个地方化的区域型强国 ,与国力相对等的条件下也已经不具备建造奇观的客观能力,何况相对简朴自律的军人皇帝也无意于此。
从科穆宁王朝 开始,拜占庭建筑其实已经逐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晚期帝国建筑的部分先兆 已经出现。包括泽伊雷克清真寺的多教堂半圆室的不规则并排 ,打破常规的穹顶建设 ——中间礼拜堂呈椭圆形的主穹顶直径7~8米(约翰二世为使建筑更辉煌而要求设计的尽最大可能的巨大),远大于马其顿王朝早期的单个穹顶,且并不是中央主跨或者梅花型布局的穹顶。
相对于马其顿王朝,科穆宁王朝时期教堂的穹顶有意识扩大了
这种框架结构上略显随意的组合 反映的确实帝国重新开始追求体例更大、更有表现力的公共建筑,但是缺乏财力(或许还有技术)完成宏伟且规则的单体设计,只能分批次地改造扩建实现更大的教堂空间才能容纳的各种需求,例如葬礼教堂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核心框架结构最后的风格变化——萎缩的希腊十字平面教堂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在整个中期帝国,帝国疆域范围内从来没有停止过建造八角形教堂与小型的穹顶巴西利卡。
即Gül Mosque,这也是一座根据建筑下部凹砖技术定位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即科穆宁王朝时期)的拜占庭教堂。据推断为Christos Euergetēs修道院(与附近的一座圣狄奥多西娅修道院易混淆),但可能后来也献给圣狄奥多西娅。
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狄奥多西娅纪念日,在1453年5月28日,即奥斯曼人攻陷君堡的前一日,整座教堂装饰着玫瑰花环,君士坦丁十一世与普世牧首莅临祈祷,还有很多人彻夜祈求,但未能挽救亡国的命运。奥斯曼人入城后,圣遗物被扔掉,圣人的遗体喂了狗, 这里也被改为清真寺,奥斯曼人所见的无数玫瑰大概是其得名的缘由。
在外形上,该修道院似乎与利普斯修道院构型类似,是一个有四个角落小穹顶的五瓣梅花结构。但实际上,它的形制规模比利普斯修道院大很多。中央穹顶大约有9米直径,比马其顿王朝初期3~4米的直径放大了三倍,十字方场平面的简单筒拱或单交叉拱跨间无法支撑这样规模的穹顶。因此,在巨大的砖构平台上实际上又回归了一个高耸、有二层围廊的穹顶巴西利卡结构设计。
这是对于查士丁尼标准结构的复古。二层围廊四角的小穹顶才是中期帝国的特色。
两种五瓣梅花平面结构示意,左侧方形为交叉拱跨间,右侧长方形为筒拱跨间 中期帝国附属小教堂(chapel)安置方式:贴在主结构外部(如利普斯修道院左右半圆室两边的小教堂);组合在教堂内;安置在二层围廊(如利普斯修道院二层的四个小教堂 )
然而由于频遭兵祸、地震与火灾的摧残,建筑上部已全为重建产物,挺拔的墙体之上低矮、缺乏鼓座的奥斯曼穹顶显得极不协调,像一个没有头颈的人,情况与阿提克穆斯塔法清真寺类似。
卡兰德哈恩清真寺
Theotokos Kyriotissa教堂(Mother of God Enthroned,今卡兰德哈恩清真寺)是一座12世纪末的教堂,约在1190/1195年建成。教堂的平面发展经历了古罗马时期的浴室以及6~7世纪的两座旧教堂,在残余的地基上重建。
教堂位于瓦卢斯水渠附近,系列图显示从五世纪初到1200年的建筑与平面图变化
安苴利王朝 政治黑暗、内部倾轧,上层穷奢极侈。这一时期重建的建筑同样扩大了其中厅与穹顶面积,前者边长19米,后者直径也达到8米。因此也需要粗壮的柱墩支撑穹顶,回归了十字型穹顶教堂(cross-domed church)平面。与玫瑰清真寺类似,中厅的一个角跨间有二层的小教堂。眼前的是西北向东南的视角,当面的主穹顶鼓座有个很低矮的鼓座是角跨间的穹顶小教堂
两侧半圆室由于沿用了旧地基而呈现出明显的歪斜,其中北侧的也安置有穹顶小教堂。
教堂的前廊(包括小穹顶)、外前廊、钟楼与南北两侧的步廊已毁。
12世纪教堂复原图
对比今天俯视的教堂,除了利用7世纪旧教堂的主后殿,12世纪的构建仅剩1/3
教堂被转为清真寺后,由于kalenderi托钵僧将其作为mevlevihane(mevlevi,即whirling dervish,旋转苦行僧;hane,集会场所),因而得名卡兰德哈恩(Kalenderhane)。
考古发掘发现的6、7世纪的镶嵌画,是君堡仅存的圣像破坏运动前的马赛克 3.4 萎缩的希腊十字平面
也是在这一时期,为了扩大中厅穹顶面积而不显得笨重,外省的一种建筑处理方式【约700年在尼西亚建造的Koimesis教堂即采用这种形制】在首都重新焕发了生机,随后又持续影响了首都附近的地区。
这就是 萎缩的希腊十字平面(atrophied Greek-cross plan) 建筑方案。
此种方式将中厅的四个支撑筒拱压缩为较厚的拱券,这样四个角跨间就融合消失在柱墩里了。中厅近似于仅剩穹顶跨间,在恢复了方形的平面同时取消了十字方场平面的立柱,提高了空间的统一性 。对不大于10米直径的穹顶,高耸的帆拱-拱券结构外部砌筑为四方形,其敦实程度已足够应付侧推力,而不至于犯下圣伊琳娜教堂早期设计的错误,近20米直径的穹顶两侧仅有单薄的拱券,近乎无视物理规律。
同时没有了半封闭的角跨间(为了建二层小穹顶,二层角跨间内侧多为四瓣式设计,即四个微型半圆室包裹穹顶,下部支撑有时就需要一层有承重墙承接),中厅对周围高度渗透 ,一个拱券通往半圆室,另外的三个直接连通到前廊与侧廊,或者可以将它们建造成连续带拐弯的交叉拱廊,即步廊(ambulatory)。帝国中晚期就习惯于增建前廊与步廊扩大建筑的总面积,且大多出于葬礼目的。君士坦丁堡保存至今的萎缩希腊十字平面仅有帕玛卡里斯托斯教堂与柯拉修道院。
帕玛卡里斯托斯修道院(最初建构)
教堂立面与平面,穹顶直径约为5米
其与Koimesis教堂的前廊仅开小门与中厅连接不同,前廊与侧廊构成的Π型步廊都是列柱支撑,一层空间一览无余。中厅的萎缩十字方场起拱于一层屋顶高度,仅联通半圆室的拱券延伸为筒拱。
柯拉修道院(最初建构)
12世纪的柯拉修道院复原图,从东南部半圆室望去,下部筒型地基为六世纪遗构
柯拉基督修道院,在现代土耳其曾经是卡里耶博物馆,2020年又先于圣索菲亚重新被改回清真寺(暂停开放,据说2024年2月以后已恢复穆斯林礼拜),无疑是除了圣索菲亚之外君士坦丁堡最出名的拜占庭建筑。它拥有整个君堡最多的马赛克镶嵌画,也是公认的帕列奥列格时期拜占庭艺术的丰碑。
当然,这座教堂的历史要早很多,柯拉(Chora,χώρα)一词意即乡下、土地,修道院初建的时候还在君士坦丁城墙以外,可能是6世纪福卡斯的女婿在其倒台后所建,并退居其中。
地下的北侧通道
后由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岳母重建(1077-1081)为十字方场构型,又因地震大部损毁。约翰二世的弟弟伊萨克·科穆宁修复时定型为了萎缩的希腊十字,构型高度简单,只有前廊、中厅与三个半圆室,其中仅中厅与中央半圆室留存至今。
中期帝国各地的萎缩希腊十字平面教堂,A为柯拉修道院 四、 装饰主义对建筑的遮蔽
中期帝国政治上的奋发伴随着1204年的耗竭化为泡影,首都的建筑也遭到了连日的劫掠与破坏。尼西亚的流亡政权回到君士坦丁堡后,高度封建化,在与诸多分裂政权的狗斗和内战泥潭中迅速衰败。
东罗马帝国晚期是一个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的时期。在帝国仅存的领土君士坦丁堡与伯罗奔尼撒半岛,贵族与高级官僚将大量的金钱与精力投掷于扩大、雕琢、美化已有的教堂,沉溺在神明最后的瞩目中。在这一时期,规制小巧的教堂基本上成为了陈列描绘耶稣与圣母生平事迹画像的背景板,密集的圣像画装饰形成了信息过载,而使人忽略教堂建筑自身高耸的美感以及象征意义。
事实上,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刚建成的时候,教堂内除了穹顶上的耶稣像与半圆室的圣母玛利亚,圣像画是很稀少的。早期的教堂主要使用名贵多彩的大理石、黄金,以及玳瑁、贝母等装饰,珠光宝气,在光影错落间美轮美奂。
镂空大理石柱头
一直到圣像破坏运动结束后,东正教社会出现了对于禁绝圣像崇拜的强烈反动 ,使徒时期、教父时期乃至圣像破坏运动时期殉难成圣的圣徒都受到了虔诚的崇拜——东罗马人将圣徒视为有罪之身接触上帝的无罪媒介,认为圣遗体、圣遗物乃至圣像都存在超自然的力量 。原本作为象征的圣徒被广泛神格化了,成为了小教堂供奉的对象。基于部分“神迹”的出现,一直到后来信奉正教的俄罗斯人还认为亲吻描摹圣徒的画像能够治病。从中期帝国开始,主要的几位被尊崇的圣人的画像已经有了鲜明的符号学 特征,便于信众辨认。
仔细想想,东罗马人这种做法也有将一神教重新复归罗马多神教的倾向。其中是非曲直,难以论说。
4.1 帝国晚期的营建
1261年,利用守备空虚的机会一举夺城,踌躇满志的“蜘蛛”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荣归他忠诚的君士坦丁堡。
然而,帝国早已不再拥有完整的中央集权治理能力,外交手腕下形成的脆弱平衡随时会被强力打破。不幸的是,奥斯曼人已经在恰纳卡莱琢磨怎么渡过海峡了。13世纪晚期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相对和平与强盛的时期,是奥斯曼风暴来临前最后的安宁,首都的部分教堂也得到了拓建。
费纳里伊萨清真寺现存南北教堂
利普斯修道院北教堂13世纪末的重建使其恢复了五穹顶十字方场结构 ,圣餐准备室与圣器室外附属的小教堂消失了。但在1940年敦巴顿橡树岭考察的时候,朝西的两个小穹顶已经坍塌,至今依然空置。
北教堂原构复原图
南教堂的建设时间稍晚于北教堂的修复,供奉施洗者圣约翰,使用的则是时兴的萎缩希腊十字平面。
从半圆室看,左为南教堂,南北两教堂仅一层连通,南教堂的支撑拱券很窄清晰可见 连续交叉拱构成了完整的步廊,北侧与北教堂连通,南侧则在末端半圆室修建了附属小教堂,与帕玛卡里斯托斯修道院的设计高度一致,不过西侧与北教堂的前廊平行增加了一个带穹顶外前廊,穹顶位置偏离了教堂轴线。稍晚还在整个南北教堂的西侧至南侧修建了一条Γ型步廊,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安葬需求,整个教堂共安置了29座陵墓以及四座骨库(Ossuaries)。
帕玛卡里斯托斯修道院
收复君堡以后,帕玛卡里斯托斯修道院在当时的首席御马侍从手中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增加了一个外前廊,又在外前廊以外再增建了一条Π型步廊(北侧尽头为单间穹顶小教堂),使教堂前部出现一个低矮的回廊群组,既提供坟墓龛室,又能在中庭举行仪式时遮掩前廊人员的视线。教堂的三个半圆室也被拆除,中间的半圆室扩大为菱形并安放了一个稍稍偏离中轴的直径6米的穹顶,比中央主穹顶还大。
在其死后(1305年),其人的遗孀玛莎在最南侧的步廊扩建出了一个经典的十字方场平面的附属小教堂(parekklesion),以安葬其夫,这与其他此前出现的单开间小教堂都不相同。修道院精美的马赛克均在这座小教堂中。
小教堂半圆室
修道院与小教堂立面均使用四五层薄砖与三四层条石交替的砌法 ,这是晚期帝国重新出现的特点。
4.2 死如秋叶之静美
从14世纪开始,奥斯曼人接连夺取了布尔萨、尼西亚与尼科米底亚等东罗马人在小亚细亚的重镇,并派出雇佣军在巴尔干局势中添上一把火。1354年,受邀登陆加里波利参与帝国内战的奥斯曼军队就地修筑堡垒,开始蚕食巴尔干,从此再也撵不走了。
在奥斯曼人大兵压境的关口,首都建筑的拜占庭风格完成了最后的华丽转身。
柯拉修道院
1315年,一个叫Theodore Metochites的技术官僚——也是当时顶尖的学者,后成为帝国首相——出资开始修复在拉丁浩劫以后残败的柯拉修道院,进行了大幅度扩建。
Theodore Metochites将教堂捐献给基督,文官巨大的包头巾是近东的普遍风格 扩建整体非常不规则,重建的前廊有不对称且大小不一的两个穹顶,两侧增设侧廊,延伸到重建的半圆室也各安置了一个穹顶小教堂。
此外又类似利普斯修道院拓建了一个Γ型步廊,拐角处安放钟楼,南侧也设置了一个穹顶小教堂。
主半圆室则添加了一个飞扶壁平衡推力,西方的影响在最后时刻体现在了拜占庭建筑中。
修道院东北方向看去
Metochites又找到了最优秀的匠人为修道院装饰刻蚀大理石、马赛克与湿壁画,整项工作持续到了1321年。
中厅半圆室方向,装饰大多为带花纹大理石板,左为基督,右为圣母
工匠们将壁画按照核心人物耶稣与圣母玛利亚各自的圣经故事发生顺序填充在了修道院的每一个角落,主要集中在前廊与最南侧步廊,步廊两侧有多个龛室盛放骨殖。
主要使用湿壁画装饰的南侧步廊
尤其是内外前廊,琳琅满目的壁画挑战着人的头颈,而富有生活气息的场景也一扫拜占庭艺术呆板僵硬的印象,在神圣主题上带出了烟火的气息,更添静谧悠远的意境。
内前廊,壁画全在头顶
最关键的几幅马赛克壁画位置
内前廊入口的全能耶稣像
外前廊门楣的圣母与圣子
圣母向基督恳请宽恕世人的罪(鱿鱼不算人,应该不在宽恕之列)
初生的圣母与其父母,全能基督左侧
生活场景,基督神迹,水变成了酒,外前廊正中
缓缓漫步在长廊,走过的是哲人王的一生,也是马赛克艺术的绝唱。
1453年,柯拉修道院首批遭到奥斯曼人劫掠。大约在17~18世纪,金光璀璨的马赛克画像被厚厚的灰泥涂抹,在天灾人祸中默默地朽坏,直到二战以后世俗化的土耳其国家才有机会显露出一瞥惊鸿。
帝国的挽歌虽已曲终人散,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还在顽强地活下去。
正是:
千族伏惧素丹名,万里音哀野狗听。
亚诺什悲瓦尔纳,尼科堡死库西英。
归来闪电传说在,穿刺大公血魄凝。
赫勒斯滂从此渡,至今兵燹不能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