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湛江在广东的地位一度仅次于省会广州,时人称之为“广州湾”。1898年后,它成为清廷战败的牺牲品,被租借给法国,赶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了革命党人云集的地方。小小海港,熙熙攘攘,湛江就此迎来它最动荡也最热闹的时期。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曾受同盟会指派前往广州湾,以经商、行医为掩护,发展同盟会会员,壮大革命声势。广州湾是革命党人的反清根据地,他们和法国秘密谈判,希望得到法国支持,建立“华南联邦共和国”。 法国学者伯特兰·马托在其著作《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中援引1914年在巴黎出版的费尔南·法让耐撰写的《亲历中国革命》说:“在这几年,这块法国的租借地成了清廷通缉犯的避难所。孙中山的同胞兄弟在这里开了一家药店。在当时中国官员的掩护下,革命党人可以更从容地制订他们的革命计划。” ^ 1900年前后的湛江街道 广州湾成了革命之地,也诞生了许多帮会地头蛇、社会黑老大。当时广州湾有三大豪强:许爱周、陈学谈和戴朝恩。许爱周喜欢搞地产和走私生意;陈学谈号称“湛江杜月笙”,做生意是把好手,为了获得社会名声,他还兴办教育事业,湛江最有名的中学湛江一中,前身就是他和兄弟陈学森所建;另一位豪强戴朝恩军火最多,名声却最差,此人绰号“铁胆”,年少早慧,但生性顽皮,一股社会气,在学校打同学,就连老师也不放过,以致校长在盛怒之下把他开除。 “戴铁胆”从此在黑道上越走越远。坊间传闻:他与广州湾烂仔“黑眼元”陈元南结成一伙,迅速在广州湾扩张势力,走私、贩毒、开妓院、开赌场……法国人治不住他,就把他发展为民间代理人,通过设立权力机构,把“戴铁胆”邀请入局,同入者还有陈学谈、许爱周。戴“铁胆”名义上是乡绅,本质上是个黑帮老大,有枪有炮有人手,黄、赌、毒、走私无所不通,赤坎中兴街、旧菜市、米行街、克里满索街(今民主路)、港口街(今幸福路)等,条条街都有他开设的赌场、妓院,他的马仔欺负百姓,受害者敢怒不敢言。后来,他担任遂溪县县长,谄媚于国民党,大肆镇压中共地下党的粤西势力。 说起“戴铁胆”的结局,颇有意思。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戴“铁胆”最大靠山无暇顾他。同年,南路游击队60多人在大路前村设伏,暗杀戴朝恩。戴当时带了很多护卫,坐的车又是防弹车,本来应该没事。谁知游击队员大喊一句:“敌援来了,快撤!”戴信以为真,探出头看,结果被神枪手一枪击中脑门,当场毙命。 民国时期,广州湾传奇人物比比皆是,罗列起来可以写一本“岭南传奇”。其中最感天动地的是广州湾“如花”、现实版《胭脂扣》,故事的主角也姓戴,名叫戴玉珠,此人乃广州湾一代名妓。如今湛江一中所在的地方曾叫“珠岭”,就是戴玉珠的墓地所在,此地是为了纪念她而改的名。 电影《胭脂扣》里的十二少(张国荣饰),与香港石塘咀的红牌妓女如花(梅艳芳饰)相遇,一个富家公子,一个青楼女人,明知前路崎岖,偏偏跃入情网,以胭脂盒为信物,唱了一出人鬼情未了的戏。这样的故事在民国时的广州湾重现。 ^ 电影《胭脂扣》剧照 这个戴玉珠就是风月场里顶有名的一个。她出生于广东雷州(旧称海康),家境贫寒,自幼被卖到广州湾妓院。她有副好皮囊,即便颔首不语,依然艳压三千,又聪明好学,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就成了广州湾妓院的花魁,江湖人称“琵琶妹”。 戴玉珠在广州湾的红尘中遇到了自己命里的“十二少”。此人姓陈,坊间所见记载寥寥,只知道是位广州湾的有钱公子,平素怜香惜玉,对戴玉珠一见钟情。 可是,妓院里的爱情,是最不可得的爱情。电影《海上花》里,黄翠凤“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她一任君离去,绝不委屈自己。戴玉珠没有黄翠凤豁达,她决绝、激烈,追寻生命的激情,又痛恨自己的懦弱,她害怕耽误了陈公子,也怕自己将来人老珠黄,爱情做灰烬,于是染上抽鸦片、吸水烟的恶习。最终,戴玉珠服毒自杀,时年26岁。 戴玉珠死后,陈公子闻讯悲伤不已,在鸡岭脚下重金为其厚葬,墓茔旁建一座六角凉亭,命名“玉兰亭”。陈公子精心撰写挽联刻在墓碑两旁,联曰:“玉陨岂无因,断却芳魂,试问何人惜玉;珠沉难自白,怜他薄命,竟从暗处投珠。” “文革”中,戴玉珠墓被毁,点滴往事,只剩凉亭可托付。如今那凉亭,就在赤坎寸金桥公园动物园内,“玉兰亭”3个字还依稀可见,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 寸金桥公园动物园里的玉兰亭 戴玉珠的悲剧,是广州湾的一个注脚。20世纪前半叶是动荡的50年,广州湾却在这动荡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它开的一个玩笑——当太平盛世时,广州湾籍籍无名;乱世之中,广州湾却因租界、海港性质而经济腾飞,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南下同胞的避难所、国共两党转运物资的中间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广东大半沿海区域被封锁,广州湾成了国共联军联通西南和华南的短暂希望。国难当头,当地华商、士绅出手相助,广州湾这座海边小城,顷刻间与国运绑定在一起。 沦陷时期,国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涌入广州湾,或者经由广州湾流入内陆,造成广州湾人口骤增。据统计,1936年广州湾“总人口为三十万,1942年激增到六十万,其中赤坎从三万余人增到八万余人,西营从二万增到三万余人,其他圩镇乡村的人口都有很大的增长”。 1940年后,难民问题成为广州湾最大的问题。伴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如何安置人口成为政府、民间共同应对的难题。此时,民间爱国人士挺身而出,兴建、发展了一批难民救济所。比如郑坤廉女士在广州湾举办“第五保育院”,接受中共、民间人士捐赠,尽量保障其收养的难童的基本吃住。当时经费来源“一是依靠总会的下发,二是依靠社会工商界的捐助。由于经费有限,只能保证每天两餐粗茶淡饭。尽管如此,保育生所用的课本、文具盒等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还是保证供应的。另外每年还发给每人两套蓝白小方格布制的便服和一套黄色的校服”。 ^ 郑坤廉 据《郑坤廉与广东第五保育院》记载:第五保育院收养的儿童曾经流浪各方,习惯复杂,加上营养不足,水土不服,刚入院的时候,百病丛生,最常见是肠胃病、皮肤病,在保育院建立之初药物缺乏,衣被床褥也不够使用,但后来情况日渐好转,难童经过收养后,在营养上有所补充,体重、身高也趋向正常。 当时海南籍六年级学生符名渊在《战时南路》第10期发表作文习作,文中写道:“回忆二十七年(1938)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敌机炸我的故乡时,炸弹声把我的爸爸妈妈吓得手足无措,人似狂潮地跑,哭泣的惨状,令我永远不忘!第二天早晨,壮丽的海口就被日军抢夺了!……逃难的同乡,食宿没法解决,漂流;走不脱的同乡,只有终日愁苦,受气。我二百多个小同乡,现在能够在这里——第五儿童保育院读书,自然万幸极了!但只要我一想起故乡,我便会由烦闷而愤慨,握紧拳头,誓为解决三百万水深火热中的同乡,打回琼州岛,杀绝琼州岛上的鬼子,消我满腔仇恨!” 同为第五保育院学生的韩仁则写了《春天的感想》,一改悲凉情绪,发出希望在明天的呼唤。他写道:“春天的精致真值得我们来爱恋啊!在此热烈欢迎’春光降临’的呼声中,一切沉睡的小生物,都被仁爱的春光唤醒,并鼓励向着’生存之路’而前进了!我们呢?我们自然不能例外。” 广州湾的这段租借岁月起始于1898年,结束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也让法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局面。194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与法国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同年9月21日,驻雷州半岛地区的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从日军手中接收广州湾。至此,广州湾才真正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归后,国民政府以广州湾范围划设市治,因史上曾属椹川县,境内东海岛曾设椹川巡检司,古“椹川”亦有称为“湛川”,故定名“湛江”市。 1946年后,国共内战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后南渡长江,加速了国民党败退台湾的进程。1949年8月,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宣布成立,于12月19日攻陷湛江市区,宣告粤桂边区全境解放。广州湾这段由历史变局造就的激荡故事,至此也就翻页了。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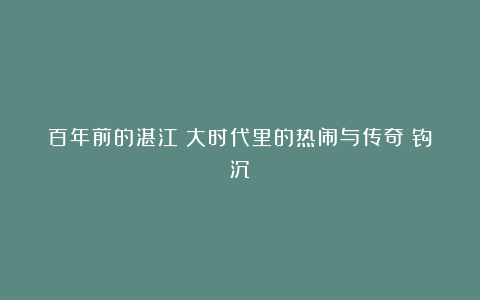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