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2025/3/16
2025年3月16日 下午 19:00
皮村同心实验小学
-新工人文学小组周六活动
创
作
谈
回
顾
|
袁
凌
Preface
好久没给大家上课了,这个正好借这本书,跟大家结合这个书聊一聊。我事先是发了几篇文章在上面,还有一些人可能自己买书读了,我看有几个人看过上面的东西? 一会请看过的人也分享一下。
NO.01
出版的历程
这个书出来的很不容易。书名最初不叫这个。大家现在看这个书名特别朴实。最初叫《亲爱的皮囊》,是书中的一篇,写植物人的。后来不让起这个名字以后,后来又想叫《亲爱的人们》。正好赶上有个作家叫马金莲,他出来一本书叫《亲爱的人们》,重名了。后来就只好改成《鸟神》,也是这里面的一篇。但是后来这个也过不了。所以最后被迫改成了一个最朴实的 《八个故事》,没有理由不让我过了,所以就过了。
现在出版环境是极其艰难的,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不是出版社能定,也不是自己能定的。但要有耐心。
NO.02
《八个故事》的梗概
这是个小说集,写的就是这五六年之间的一个积累。我前面有个小序,采用的是一个文白。我写得这么简短,是不想说很多,想把一些感受浓缩在里面。确实疫情的这几年中国人活得很艰难,大家的生活都出现了很多的变数。这些小说的虽然说不是直接写疫情的,但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一个个卑微的人生,很不容易的生活的背景。
这些小说的主题跟我的非虚构的主题其实有点像:不是高层人物,也不是商战人物,是一种底层的普通人。我所谓的普通人,不一定非要是那种力工,不一定非要是像海娟他们这样要做体力劳动或者月嫂,大部分就是辛辛苦苦用自己的能力去吃饭的人。
你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篇《大杂院子弟》写的是一个律师,算是菁英阶层了。但他是一个留守儿童出身,他的父母是那种到北京来做地摊生意的小商贩,一直住在大杂院里。他从小的生活,平时是留守儿童,过得很苦,他爷爷脾气不好,经常揍他。到了暑假,他就到北京来,在这个大院待上一段时间。那个大院是极其的脏乱破的一个环境。
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真实事件。我以前写过一个特稿,叫《北京局外人》,其实就是写他们一个家族的。我主要是想写什么呢?就是想写这种人的“撕扯”——他已经是菁英,但留守儿童的背景给他带来很多的创伤。同时他虽然已经是菁英了,但是他的父母还在大杂院里继续干着最卑微最卑微的活,不管严寒酷暑,都是弄着一个三轮车拖着很多的货到早市上去卖。
我这里面设计了一个情节,是他告诉我的,我把它特意突出了。就是他有一次约一个生意朋友在 798聊天,在咖啡馆里喝咖啡。798是一个挺时尚的艺术区,他在那正好碰到他妈妈在外面的道路上,弄一个小火钳夹烟头。原来,他妈除了出摊还兼职在798园区做清洁工。他在这碰见了他妈,非常的尴尬,就是痛感:既有一种羞耻感,同时又觉得很惭愧——就觉自己好像披着一个菁英的皮,但妈妈还在干着这么一个工作。这就是他的一种分裂。同时他跟他的妻子之间也会有这种矛盾,因为他的妻子并没有这种底层的身份。
“墨菲定理”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意思就是如果你老把事情往坏的想,那个坏事情就会变成真的。《墨菲定理》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写的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虽然上了大学甚至留学了,但是回来以后得了抑郁症,跟她的母亲的关系极其糟糕。母亲又是很底层的,做家政、物业之类。其实母亲也上过大学,但是后来落到底层去了。母女之间产生了极其尖锐的冲突,就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困境描写。同时给她们治病的心理心理咨询师又陷入了他们的感情纠葛,而这是他的职业操守不允许的,所以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突。我一会跟大家讲情节的设计。
《彩色骨灰》也是有原型的,一个西安的女的。她一辈子好像都在为别人活,后来死的时候,她为自己活了一回。她不愿意抢救、不愿意插管、不愿意打针,明明白白地告诉她的朋友:“我不打针”。最后就这样去世。那么为什么叫“彩色骨灰”?就是选取的这个故事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意向,就是这个女的去世的时候,他的骨灰是彩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去世之前,她要求把一条在西湖旅游的时的买了一条杭绸的纱巾穿上火化。火化的时候,可能是纱巾质量好吧,那上面的颜色还保留着,烧进了她的骨头里面,所以他的骨灰有一部分是彩色的。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听到这个情节,我是不会写这个小说的。我们写东西,可能都会有一个情节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你从这个动机展开去,可能可以形成一个作品。
《亲爱的皮囊》是写植物人的。我老婆罗兰有一次写稿子,去采访燕山脚下的一个植物人疗养中心。我好奇就跟她去了一趟。其实她也有点怕,所以我就跟他一块去。我去了两趟,看到的当然是皮毛。但是我后来很难忘记这个事情,我就又让她给我讲了一些,她又在采访了一周,讲了一些那的事情。而我自己加了一些想象,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它是有一个蓝本,但其实我当时看到的很有限,我就不能写非虚构。写小说,就要加一些我以前的生活经验。
《鸟神》也是一个朋友的故事。但是这里面小说成分比较大。就是要突出什么呢?这个人小时候非常爱鸟,所以他后来选择到动物园的百鸟林工作,专门去看顾鸟。但是由于生活的变故,导致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一个是来自母亲的,一个是来自妻子的。最后他的性情大变以后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弓友”,一个打鸟的大神,打了很多很多的鸟。他最后的死亡也跟打鸟有直接关系。他们有一次出去打鸟的时候,回来出了车祸。他带着两个向他拜艺的两个弓友去打鸟,回来路上出来车祸,那两个工友都没事,恰恰他死了——车祸正好让他的脖子折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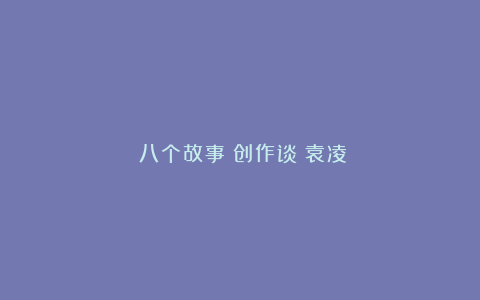
鸟被打了以后不会马上死亡,他一定会把鸟的脖子拧断——所以有人就说他得了报应。他的人生为什么会从一个小时候那么爱鸟的人,后来又把护鸟当职业,最后走到了要去打鸟?在打鸟当中寻找价值感的这么一个人生?结尾是有人建议给他做一场超度,但是朋友选择了最后仍然用弹弓给他陪葬,并没有为他办超度法事。就这是一种尊重人的态度,也许用一种话来说他可能有报应,但是我们不能这么看,因为我们需要尊重他的命运,尊重他的人生。
《此人纯属虚构》写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朋友圈有一个留言:“此人纯属虚构,如若遇见纯属见鬼。”他活着的时候写的朋友圈,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见过他几次,后来他真的就死了,死的无声无息。活着也是一个浮游一样。他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从小可能家庭有一些问题,他的父母亲没有养他,把他搁在亲戚家里,也受到一些虐待。他成长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最后导致他对人生是一个游戏的态度。他非常需要感情,但是他没有办法经营一份感情。他的人生也是这样,没有办法投入一个事业,始终是一个飘来飘去漂泊的感觉。他是现代社会造就的一个空心人。我这里想写一种社会现象,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空心人。你不能说他生活条件有多不好,不能说他有多艰苦,但是他的人生没有意义。
《山》写的是一个底层的矿工,一个家乡和外面世界的断裂。他死于一次矿难,被运回老家埋葬,最后由和他关系最好的叔叔来处理侄子的丧事。他这个叔叔也是这样,早年出来招工,在北京落户了,娶了一个北京的女人。但是他对北京没有感觉,他的心始终都在家乡。但是他又回不去。两个人有这么一种纠葛,也是一种离乡和家乡的一种断裂。其实这本书里面的人都是这样。
“物理反应”与“化学反应”——非虚构与小说
所有这些故事都存在一个由原型到小说的转变过程。为什么我要写成小说而不写成非虚构?这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比如我写皮村,我会把它写成一个非虚构?因为这个皮村本身有一定的关注性和公共的价值。有公共价值的东西其实更容易写成非虚构。
什么情况下写非虚构呢?就是这个人的故事有一定的议题性、又很完整,有标本意义。或者说,虽然一个故事本身的表现得没有那么强,但是当有一系列的故事在一个主题下面(就可以成立)。比如说《生死课》,讲得就是一个个中国人的死,“卑微的生,卑微的死”这样一个主题。像《汉水的身世》,它本身就是一个宏大题材,是一个全国的国家工程,我把它写成非虚构。
《八个故事》里都是一个个小人物故事。除了《大杂院子弟》,其他的写成特稿都很难写。把它写成非虚构,它就没那么大的价值。但是它仍然有很多地方触动我。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有一点触动了我,很多事情都是我一直忘不了,我后来就把它们写成了小说。当你没有办法写非虚构的时候,可以写小说。
那在什么情况下去写小说?一种情况是它的材料太多,生活经验、细节沉淀得比较多以后,只写非虚构有点可惜。为什么可惜?因为非虚构只能写出它的一面来。就像《大杂院子弟》就是这种情况。开始我写了一篇《北京局外人》以后,经过了很多年我又写成一个小说。特稿可以写出在大杂院那些小商贩在北京扎堆的那种集体生活的状况,但是我没有办法写出主人公在身份与境遇之间的一种严重的,有某种普遍性的分裂。
第二种情况就是像《墨菲定理》还有《鸟神》这种,材料不够写一个非虚构,但是它里边有一些东西很触动我,我忘不了,始终难以放下,那么我最后把它写成一个小说。
对一个故事,第一种情况还好说。你的细节、经验是够的,缺少的是一个“韵味”。非虚构的韵味没有小说那么多。小说要有一个讲究,小说里有特别的一种“化学反应”的东西,而非虚构更多的是“物理反应”。
非虚构,你编织就行,一些叙事线,一些内在东西,一个揭示就行了。但是小说需要“化学反应”,需要把现有的材料化合起来形成一个“韵味儿”。你要增添的是一个韵味儿,这个韵味说到底是它是一个对人性的理解,对生活经验的再度熔铸,不光是编织。编织只是表面部分。编织是必要的,平移情节,交叉,还有真实的和想象的,真实的和虚构的互相交织在一起。但是它后面还是那个韵味的东西——那才叫小说。就是超越了生活平面的,但是跟生活有关的那一种让你回味的,让你无法把握、无法定义的那个东西。那个叫“韵味”也叫“小说味”。
好多人说的“小说味”其实不是我说的这个“小说味”。好多人说的“小说味”是一种调调,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调子”。一旦你读进一个小时,你发现它的生活不是你日常生活,是完全陌生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容易变成一种套路,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品。我喜欢的是另一种“小说味”,它有日常生活感化合成的一种特别的韵味。这个韵味是很难消失的。就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全是日常的事件,但是你看到那个书之后你会觉得很有味道。你会觉得就这么两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好像生活在永恒的时空一样。他写出了人类永恒的境遇,让人难忘。它比《战争与和平》,《安纳·卡列林娜》这样作品还有韵味,这就是真正的“小说味”。
当原型素材较多时,用细节创造小说味
在《大杂院子弟》里面,在现有材料已经有余的情况下,怎么做到这个“小说味”?有一些细节你需要去把握,叙事的当中哪怕是一闪而过的东西,你需要有一个情境的刻画。就像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买了一个房,但是他不是富豪,买房是很吃力的,而且是在南四环的边上。你看他买了房,是很不错的了。但是走进那个房的时候,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像牛皮癣,贴得满楼道都是。这立刻就表现出一个双重境遇:一方面算是成功人士了,算是菁英;但另一方面,菁英的身上仍然贴着牛皮癣的那种感觉。
当原型的材料少时——用平移经验
那么材料少的时候怎么办?就像《彩色骨灰》《墨菲定理》尤其是《鸟神》,材料都没有那么多,但是给我一种很强的感觉。比如《彩色骨灰》,她对朋友说的那句话“轮回开始了”。她本来病恹恹了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忽然回过头来跟他朋友说“轮回开始了”。我把它放在小说的第一句话,立刻就把人吸引到情境里面,被带入进去看他以后的人生到底怎么样。
由于材料没有那么多,我就把一些其他人的经验移到了她身上。比如增加她丈夫的生活的经历。她的婚姻就是一个悲剧。她遇到这个男的以后,找到了一份工作,生活就要步入正轨,却在入职体检的时候查出了癌症。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她不想死在医院里。当她觉得自己的病已到晚期,提出让那个男的接他到家里去住,希望住在那个男的家里迎接死亡的时候,那个男的想了想,拒绝了。
这里面有些东西就是我需要去补充的。比如说她跟她男友的关系,比如说一些医疗方面的尝试,怎么抢救的。比如说她以往经历,比如说我对她男人的一些设计——他曾是一个厂里面的宣传员,很有风采,后来怎么样一步步没落……这些都来自生活中的经验,平移到了这个男人身上。
平移经验在《亲爱的皮囊》里特别突出。这个阿姨跟她老公之间那种相爱相杀的关系,其实来自我一位堂姐和堂姐夫。他们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在一起时经常这个要冲突,我姐夫就出走,回来以后两人又和好相处。我就把这个平移到故事情节里面去了。
从一个触动出发,阐释人性
《亲爱的皮囊里》有个伦理和人性的尖锐矛盾:人只剩下一个皮囊,还要不要活?到底是你放弃它好,还是你不放弃好?这里面有一个伦理的尖锐的冲突。我希望就是把人放在这个生死极限的边缘上对他的人性有一个考验。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拷问出善下面的恶,又拷问出恶下面的善。”我就是把这个阿姨拷问出他爱下面的恨。因为她看起来很爱他,甚至都搬到那里天天照顾他。但是爱下面其实有恨——当他真正面临救不救醒他的时候,她犹豫了,最后她选择了不救。虽然干细胞催醒针可能就是商家的一个欺骗宣传,但对她来说是真实的。老公去世之后她又陷入深深自责——恨下面又有爱,那爱的后果甚至是让两人冥冥之中走了同一条路。这种真相只有在人性面临极限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极限的环境里,才能把它拷问出来。那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的原因。
基本上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让我不能忘怀的东西。我不太想写一个纯情感的东西。都是他们在某一点上触及了我对人性的理解,对我们生活的未显明的本质的触及,我才会去写它。我并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一般来说,当没有达到么深切的一个触动的时候,我不太写。但是我写的时候一定不是无病呻吟地写,我其实想要探讨、揭示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当我真的去写的时候,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写小说很慢。一个小说从开始写到写好,要修改很久,一年,有时候要放几年才能想到哪一点可补充,或者修改。有些关键的动机我总是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去把它编好。不光是编,要在小说世界里面,有一个跟现实世界一样既有真实感,可靠,又有韵味的东西生长出来——这个是很难的。在我来说也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有些时候做得真实感很强,但是韵味不足,有的时候可能你又没那么多的真实感。可能真实是容易做到的,但是韵味相对难一些。
做的比较好的还是前面这几篇。当然别人看了以后也是这样一种态度。《大杂院子弟》和《墨菲定理》都被选入了年度的小说选。《彩色骨灰》我其实也挺喜欢的,我就把一个人生的况味把它写出来,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你像《大杂院子弟》这个小说写得好久好久,怎么样把它写得能够有那个味道,涉及到很多的知识。比如说一个律师在那些官司里面涉及到哪些知识?比如说《彩色骨灰》里面抢救。尤其《墨菲定理》里面有大量的心理学知识,我以前并没有这些心理学知识。我就需要去查大量的心理学背景知识,包括“墨菲定理”这个名词,心理学的一些伦理,心理学的一些生存现状,这样把它最后弄得像个样子,成为一个小说。
所以大家如果说习惯了写非虚构再写小说的话,其实你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块空白点,你是要补上的,其实挺难的。我希望我这个对大家有点帮助。
2014年成立,致力于促进工友与文化志愿者的文学交流。通过定期的讲座、《劳动者诗与歌》晚会和“劳动者文学奖”征文活动、《新工人文学》电子双月刊等,我们鼓励工友进行文学创作,丰富劳动者的精神世界。
支持我们,共同推动文学的力量,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